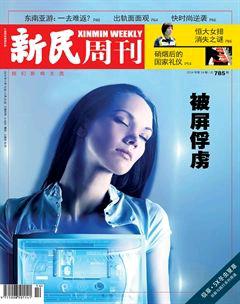互聯網+公益:無限可能
王煜 李玉



“站在風口,豬也能飛。”在近日“免費午餐三周年”發布活動中,互聯網人士雷軍的這句話被公益人士鄧飛引用,恰到好處地說明了網絡與公益的關系。2011年以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爆炸式發展,人人參與公益、人人監督公益成為可能,而把這樣的可能變成現實的,是以“免費午餐”為代表的一批運用“互聯網思維”的公益項目。在執行團隊和眾多網友的努力下,“免午”們已經創造了中國公益界的奇跡;而實現愛心的更多可能,就把握在每一個普通人手中。
互聯網成就“免費午餐”
2011年初,當鄧飛在南海的一艘郵輪上萌生“免費午餐”的想法時,他對“互聯網思維”這個他之后賴以成功的關鍵要素還沒有清晰的概念。實際上,這個詞匯在國內最早出現,也只是在2011年李彥宏的一些演講中;2012年,小米創始人雷軍開始頻繁提及一個相關詞匯——“互聯網思想”;2013年,隨著雷軍曝光度的不斷提高,一些自媒體人士如羅振宇等開始頻繁提及“互聯網思維”,這個概念才開始迅速躥紅。
但這并沒有阻礙鄧飛用互聯網思維推動“免費午餐”的前進。“去中心化、創造連接、爭取信任、快速更迭”……投身公益前,作為資深媒體人的鄧飛已懂得用這樣的方式來生產新聞、贏得受眾;當他開始把眼光聚焦于貧困山區孩子的吃飯問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成熟媒體人的操作方式帶了過來。
2011年4月2日,免費午餐基金在廣州創立時,就聯合了國內500名記者、數十家主流媒體作為發起方,向所有人發出倡議:每天捐贈3元,就能為貧困學童提供一份免費午餐,讓他們免于饑餓,健康成長。免費午餐所到的每一所鄉村小學都開通了微博,把每天有多少孩子吃飯,每天做飯花了多少錢,一分一厘地向全世界公開。免費午餐基金掛靠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為全國性專項公募基金。
自3年前正式啟動至2013年12月31日,免費午餐總募集善款7678萬元,年均增長率34%;累計支出3991萬元,年均增長率174%。這些善款,大多數都來自個體捐助者。正是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讓中國的慈善公益遭受巨大信任危機,誕生于該年的免費午餐是如何挺過來的?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繆力回憶說:“那時,網友們真的是一分錢、兩分錢地捐給免費午餐,當他們連這些捐款也能在網上清楚地看到走向和用途時,就開始捐3元、30元、300元……”信任和愛心就是這樣點滴匯集。
3年來,免費午餐運用社會化媒體動員社會參與,用“群”的方式組織人財物,用微博、公益網店、月捐等網絡籌款的方式,把普通人參與公益的成本降到最低,被視為中國公益界的創新典范。把所有該公開的都放到網絡上“曬”,讓全民來監督,這使得免費午餐至今沒有發現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和資金安全事故。
2013年,免費午餐新增項目學校154所,累計學校總數達到359所,同比增長75%。截至2013年12月底,項目總涉及19個省區,2013年受益人數91190人。以“免費午餐”為核心和樣板,鄧飛公益團隊又創立了“暖流計劃”、“大病醫保”、“女童保護”、“點亮心燈”等一系列旨在造福鄉村兒童的公益項目。快速更迭的特點也明顯展現。 從最初一名記者的一個理念,到中國最受歡迎的公益活動之一、獲得中國政府慈善最高獎“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免費午餐借互聯網之力,創造了奇跡。
學會與政府合作
“直接影響了國務院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出爐”,這是免費午餐宣傳資料中不可或缺的一句。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健剛評價免費午餐時說:除了創造性地運用互聯網思維實現人人公益,免費午餐的另一大功績就是以民間之力推動社會政策的轉變。
實際上已成為全職公益人的鄧飛,一直在不同場合提到自己將來要重新做回記者。“免費午餐的發起者都是媒體記者,我們應該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整合資源和輿論監督。我們應該是輕騎兵,創立和摸索一種行之有效的公益模式后,把它交給社會,交給政府。”
在《免費午餐:柔軟改變中國》一書中,鄧飛提到,在免費午餐開始嘗試與政府合作時,曾受到強烈質疑,反對者在微博上與他“論戰”:有人認為這意味著項目被政府“收編”,有人認為這必將使免費午餐沾上官僚機構的貪腐和低效。但鄧飛認為,在關愛鄉村兒童這件事上,免費午餐和政府的宗旨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行為方式不同;免費午餐是一個建設者,應該想辦法匯聚一切可以匯聚的愛心力量,為什么不可以找到雙方聯合的模式呢?
抱著這樣的想法,免費午餐開始與各地的教育、民政等部門接觸,了解官員們的想法,與他們探討合作的可能。在湖南新晃和湖北鶴峰等地,實現了“政府出1元,免費午餐出2元”,在全縣推廣免費午餐的模式;有些地方合作了一段時間,最后因為政府政策的變動,免費午餐不得不退出。在這個過程中,免費午餐依然保持依靠網絡公開的全面透明,以事實擊倒了質疑。鄧飛透露,最近,在江西九江的武寧縣,“免費午餐出1元,政府出1元,家長出1元”的新模式將開始試點。
鄧飛曾表示,政府出錢向免費午餐這樣的公益組織購買社會服務,是他心目中民間公益組織與政府合作的理想模式。公益組織可以因地因時制宜地為政府提供優秀的模式,讓民生工程真正落到實處。
免費午餐近日在上海發起的一場公益分享會上,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學院合作發展總監張利談到,盡管互聯網思維提倡“去中心化”,但好的公益組織不能自我隔離,而是需要和企業、政府等主流的組織做好銜接,不能把公益組織做成純粹的“道德選擇”。有人擔憂“和企業、政府合作會降低公益組織的公信力”,張利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公益組織要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實現品牌的增值,這樣才能獲得公眾的信任,這需要充分借鑒企業的商業操作模式;而對于一個新生的公益組織而言,它的公信力其實是小于政府的,不存在與之合作會降低公信力,實際的情況是相反的。”
讓公益變得更“輕”
互聯網思維下的公益組織如何發動公眾參與?網絡與公益的結合還有什么可行的創新方式?在上述分享會上,AHA社會創新學院創始人顧遠說,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民的公益參與方式以及內容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依托網絡平臺,公眾可以更多地參與公益活動的信息提供、信息發掘以及建言獻策,而這種形式的參與有時可以直接推動決策的實施。endprint
他舉例說,2011年12月,PM2.5剛剛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時,官方發布的空氣質量數據即使在人們感覺明顯是污染十分嚴重時也是“輕度污染”。于是,國內著名的環保NGO“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發起了一場“我為祖國測空氣”活動,號召環保NGO和市民自發拿起空氣檢測儀器,走上街頭,開始自測PM2.5,并通過網絡發布信息,為人們提供普通人在各個地點測得的數據。活動不僅為上海、廣州、溫州、武漢等城市的環保組織和市民募集了便攜式PM2.5檢測儀,讓這些地方的民眾親身參與進來,對空氣質量愈發重視,而且直接推動了當地PM2.5監測及發布的進程。
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韓國首爾地鐵4號線的“高低把手”。首爾不少市民在長期乘坐地鐵過程中感到,懸掛高度一致的地鐵把手設計得并不合理,對個子矮的人來說,夠不到頭頂上的把手是一件很尷尬和不便的事。于是市民們通過網絡平臺將意見提交給地鐵方,后者予以采納,于是4號線上就出現了高矮不一、更加人性化的地鐵把手。又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通過網絡向全世界征求破解城市建設難題的良策。
公益如何有趣?“一個雞蛋的暴走”越來越廣為人知,而活動的發起方上海市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聯勸)秘書長王志云說,面向公眾籌款有時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既要贏得信任,又要讓公眾覺得參加進來有意思。2011年,聯勸的“雞蛋暴走”公益平臺上線,通過親友間“打賭”完成50公里徒步行走的方式,讓募捐變得更有動力,參與者更有成就感。“你可能不相信我們這個組織,但你總相信你的朋友。而且跑步、‘暴走,本來也是當下流行的生活方式。”
王志云說,目前的統計數據顯示,平均每一個人“暴走”,就能帶動7.6個人捐款,數額平均在230元左右,相對于民政部公布的2012年全國人均慈善捐款額的60.4元,是不錯的效果。
同樣是走路,愛盟公益推出了“行善”手機App,為用戶的運動計步,用戶每走1000步,加入愛盟平臺的企業就為公益捐出1元錢。創始人郭鵬說,將來用戶可選擇的“行善”任務還會增加聽音樂、做美食等方式,讓用戶參與公益更輕松、更開心。
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學院合作發展總監張利表示:“公益沒那么沉重,它是一種好的生活表達方式;而公益創新也并不必須是顛覆性的,它常常是嵌入原生活的。”王志云提出,美國民眾平均每年將收入的2%用于公益捐款,而在中國這個比例只有0.2%。互聯網思維下,公益組織在籌款方式上的創新上仍有無限可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