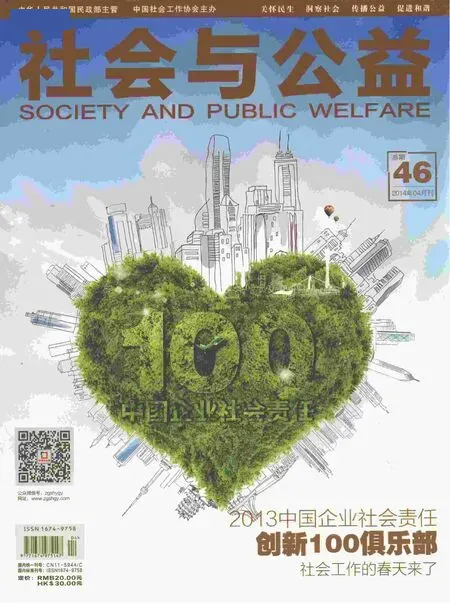探索“醫務社工”發展之路
文/本刊記者 陳紅
在中國,“社會工作者”成為國家職業新工種的時間并不太長。2004年,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國家職業標準里,“社會工作者”被首次載入。至此,這個曾經在中國有實無名、“聽上去很美”的行業,終于獲得政府層面的支持和認可。
那么在公眾眼中,“醫務社工”的概念并不足夠普及也就不足為奇。然而醫患關系緊張、醫務糾紛事件頻出的當下,已經不容許有太多的時間讓這一群體慢慢被適應和接受,醫務社工的發展模式也在磕磕絆絆中未停止過探索。
“醫務社工”搭建醫患橋梁
不久前,上海某家醫院內發生這樣一幕。
道路交通出車禍后,傷者中一小女孩被緊急送到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由于傷情尚未確診,小女孩全身被安全帶固定在擔架上。聞訊趕來的媽媽,見女兒猶如“五花大綁”,頓時嚇得臉色慘白。問醫生,醫生十萬火急忙著救人,只能說句“不清楚”,就要推孩子去檢查。母親瞬間失控。
這時,另一位白大褂來了。她不去病房,卻在媽媽身邊坐下,用專業詞匯向醫生詢問病情,轉而向這位媽媽耐心解釋,媽媽的情緒漸漸穩定了。這位白大褂又專門要了她的聯系方式,以便追蹤溝通安撫。臨別,話語溫暖:“別著急。我是醫院社工,有什么事,盡管來找我。”
作為全國最早開展醫務社工工作的城市之一,上海醫院中的社工,正漸漸被越來越多人知道。
“上海模式”成功鋪開
在上海,醫務社工的角色與醫生護士一樣,以科室或部門的形式被納入醫院體系之內,也被賦予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自2000年起,上海東方醫院、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等醫院就陸續出現了醫務社工,也成為了國內引入職業醫務社工的先行者。
“但是那時候醫院還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部門的價值和作用,而我們也沒有太多的相關經驗。”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副院長季慶英對記者說。彼時內地的醫務社工寥寥無幾,人才隊伍發展緩慢,僅本醫院內部的服務缺口就很大,兒童醫學中心500個床位,其中不少是重癥監護室和白血病病人,但是醫院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3個社工。陳玉婷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師范大學社工專業的陳玉婷畢業后,便在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社工部開始了她的醫務社工生涯,她說自己與部門共成長。一方面是通過科室輪轉、跟隨查房等方式進行臨床實踐,開展個案和小組活動,引入外界資源等等,另一方面進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部門建章立制,課題研究等工作。“沒有經驗可循,我們所做的就是一直向前嘗試。”陳玉婷如是說。
十幾年過去了,已經有較完備的知識技術和高校人才支撐的上海看到了發展醫務社工的契機和模式——醫院設立社工部,將社工納入整個醫院體系內,使之成為醫院內部員工。
這一點,陳玉婷的切身體會是,社工被派駐到醫院當中的話,在醫院內的整體融入度不好。“內部員工之間的溝通肯定會比外面的人來突兀地做溝通順暢許多,每天和病患接觸也會更方便,醫學知識掌握得也更快。”
這樣的醫院聘用方式令她有一種“身份認同感”,就是“自己看自己不一樣,同事和病人看自己也不一樣”,在薪酬保障方面也沒有不公平之感和職業發展的后顧之憂。
2012年2月,上海市衛生局出臺了《關于推進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試行)》,要求在“十二五”期間,各家醫院初步形成醫務社工管理機制和工作格局,建設一支能夠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熟練開展醫務社會工作的專業隊伍。明確規定“在醫務社工配置上,綜合性醫院按照每300-50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醫務社工,兒科、精神衛生、腫瘤、康復等專科醫院每100-30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醫務社工。”預計到2015年,全市在崗醫務社工總量力求達到400-500名。
“在醫院的評價體系指標里面,有沒有醫務社工和社工部已經被納入,成為了一項考核標準了,這在全國只有上海這么做了。”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副院長季慶英的話里透露出欣喜。
醫務社工能做些什么?
“從醫院的起源看,它除了治病,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人精神的撫慰。”攻讀了醫院管理博士學位的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績效辦主任任益炯開宗直言。
像本文開頭提到的事,你覺得應該由誰來做?時間就是生命。危急關頭醫生難以對患者家屬慢慢講明情況,護士難以明晰詳細病情,還要照顧更多患者。那么,誰來安撫家屬?
還有,比如這樣的時刻:一位得了厭食癥的孩子,嚴重營養不良,卻不肯配合護士喂藥吃飯;醫生打針,他也不理。直到社工趕來,與孩子聊天溝通,才知道他覺得父母一直沒來探望,不要他了;而在病房,他又沒一個朋友。這時的治療,不僅需要與家長溝通,還需要與醫護溝通,改變治療方法。那么,這種兩方面的溝通,該由誰來承擔?
再如,就在兒童醫學中心,醫院血液科80%的病人來自外地,心臟科90%的病人來自外地。舉家來到上海,對這座城市的不適應,對人的不熟悉,甚至去哪買火車票,哪里能找到便宜住宿都不知道。這時,誰第一時間伸出援手?
這些,正是如今上海醫務社工在做的事。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副院長兼社會工作部主任季慶英說:“社工是現代醫院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季慶英畢業于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兒科系,后進入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醫院設立初期,就成立了醫院發展部,承擔活動策劃、宣傳、慈善捐助等,尋找更多社會資源幫助患者。其實,這些就已含有社工的職責。”工作中,季慶英愈發感受到社工對醫院發展的重要作用,赴香港學習后,2004年碩士畢業回來,醫院即成立了社會工作部。
與季慶英稍有不同,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醫生宓軼群,是從臨床醫生逐漸轉向醫務社工的。這源自她對醫生職業的反思。“我一直在做臨床。久了也困惑,為什么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會到如此地步。”宓軼群說了這樣一件事:一位30多歲的病患,被車撞成粉碎性骨折,肇事者付了第一筆醫療費后,撒手不管,患者便將怨氣撒向醫院,他說,為什么我好著進來,不能好著出去?他來醫院消費,醫院憑什么不能提供等值產品……他不相信所有醫生護士。這時若有社工在,會不會好些?
“醫務社工,就像醫生與患者之間的橋梁,醫生、患者與社會關注之間的橋梁。”季慶英說,“以促進人的健康為核心,不僅達到沒有疾病,而且達到身心平衡、人與環境的協調,這就是醫務社會工作的核心。目前,我們醫務社會工作的基本任務,集中在預防和減少醫療糾紛,緩解病患矛盾,包括在治療過程中,給病人和家屬心理援助,引導他們進行良好的情緒處理,努力解決病人與家庭和社會的交往障礙,幫助病人獲取社會資源等。”
正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像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一樣,如今上海一些醫院有了住院部兒童游戲室、陽光小屋等場所,會組織兒童健康節、病員學校,組織ICU家長小組等多種學習服務交流平臺,并開展對新員工“愛的教育”、“醫患溝通技巧”等專題講座,為醫患關系、為患者身心提供全面的服務……“全球現代醫療技術不斷追求深入與專業化,應該強調要全面顧及患者精神。社工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醫院本身內涵的恢復。”任益炯說。
特殊的“白大褂”對誰負責?
既然社工是“舶來品”,很多人習慣性地將中國與國外比較。幾年前,徐女士在紐約一家診所做孕前檢查時,醫生發現她沒有工作和收入來源,建議聯系社區婦幼保健機構,并給了一個電話號碼。她將信將疑打電話后,第二天下午便來了一位能說普通話的華人社工,拿來一堆申請表格,還給一張信息卡。憑這張卡,徐女士可在申請沒批復前,去社區婦幼保健所免費診查。后來每次去醫院,這位社工都陪同,并翻譯醫生建議,跑來跑去服務。徐女士漸漸了解到,這位社工并非醫院雇員,而隸屬于民間社工機構,專為華裔孕產婦服務。前后3個多月,社工盡心盡責。徐女士是剖腹產,臨產前社工還專門為她預約麻醉師。徐女士生下孩子后,社工又為新生兒辦理各種證明材料……
現在徐女士已回到上海,有時去醫院,也能看到社工的身影。有點不一樣的是,“這些社工都穿著醫生一樣的白大褂,是醫院的職工,不像美國社工來自于第三方機構。而且國內人數也太少,分工不細,要像美國那樣全程陪還根本做不到。”
不過,在徐女士看來,中國國情不同,社工制度剛剛起步,沒有必要吹毛求疵,“有社工服務已經是很大進步了,相信將來醫院里社工會越來越多。”
對這一點,同樣穿著白大褂的兒童醫學中心一線社工陳玉婷,也挺有感觸:“讓病人分清社工與醫生,開始的確有點難,像我國臺灣的醫院社工,同樣穿著白大褂,不過領子是粉色的,一目了然。這些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鑒?”
由此還產生一個問題:社工由醫院雇傭,在醫患之間能否做到不偏不倚?“你說的是工作倫理問題。雖然受雇于醫院,但作為社工,工作的核心始終在于患者。當然,最終結果都是對患者好,也對醫院有好處。對于我們的工作,是有專業督導與團隊支持,核心價值觀相當明確。”身處一線的陳玉婷認為:我們的差距主要還是在于分工不夠細致,資源鏈接不夠有效。
“現在內地的模式,更像我國臺灣地區,社工主要還是由醫院聘請。”季慶英說,“好處也相對明確。比如讓社工有歸屬感,與醫院內部交流比較多,更容易掌握內部資源,做好協調工作。醫院可以對社工像員工一般進行培養,讓其到臨床、藥劑等部門實習,積累專業醫務經驗,提高服務水平。醫院也可將社工作為發展的一部分,促進社工實務發展。西方在實踐中存在的組織機構協調問題,在我國就不會出現。”
目前,上海設有社會工作部門或開展專業社會工作的三級、二級醫療機構逐漸在增加。不過,由于缺乏專業委員會的指導和繼續教育,各機構發展很不平衡,“別的不說,名稱就五花八門,開展的內容也相對集中在貧困救助、志愿活動組織上。”宓軼群介紹六院社會工作發展的概況,主要職責也是募捐,“不過,我們現在嘗試做的慈善醫療基金,能夠明確告知對方,你的捐獻救了誰,現在到了哪一步,比過去有了很大進步。當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新兵’,需開拓的工作還有很多。”


篩查現場
醫務社工有特色亦有難題
最主要的是社工編制與財政問題。季慶英所在的兒童醫學中心社工部,包括她只有兩人。“社工工作千頭萬緒,按我們的計算,要有10位社工就理想了。有人專職做行政,策劃宣傳;有人集中精力為患者包括家屬服務;有人跑社區爭取資源,并與社區社工對接;還有社工開展‘臨終關懷’服務,滿足病危兒童最后希望……”
這當然與醫療體制的特點分不開,衛生系統還沒有專為醫院社工設編立崗,如一線社工陳玉婷,目前也只歸于醫院行政管理崗位。“隨著社會發展,社工在維護穩定、創造和諧方面的獨特作用會日益顯現,政府部門和醫院一定會越來越重視。”
不過,也要防止對社工的過度“神化”。“大家要清楚的是,社工能做很多,但社工并不是萬能的。”陳玉婷舉例說,社工能夠緩解醫患矛盾,但當醫患糾紛進入法律程序后,社工就必須退出,交由專業部門處理。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馬進認為,現代社會構成越來越復雜,一些非醫療但與之密切相關的事務和關系,需要相應的專業人士承擔,而醫務社工正由此應運而生。醫療領域特別需要社工,因為醫患之間存在一定的信息天然不對稱,患者常會懷疑醫院行為是否恰當,即使是醫院作為醫療服務的供方主動解釋,患者也會有不信任感。此時,醫務社工以第三方立場出現,能協調供需方利益,及早化解矛盾,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醫療領域的各種糾紛,絕大多數屬民事糾紛,社工作為中間人進行調解也很適合。
對于目前社工大多由醫院自己培養的方式,馬進覺得這不但將會受限于醫院的人力資源,而且也難以真正發揮社工第三方作用。他建議,政府一方面可舉辦社工機構,一方面可鼓勵民間非營利組織發展社工事業,然后以購買服務方式派遣社工到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