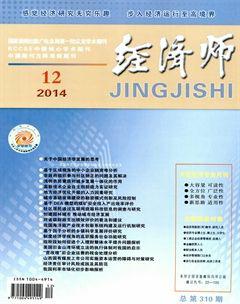生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價格激勵機制分析
●何楊平
生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價格激勵機制分析
●何楊平
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的合理定價是構建生態產業鏈的關鍵問題。文章通過對完全信息情況下和不完全信息情況下的價格激勵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結論:當上下游企業信息對稱時,下游企業可提供固定價格合同,以誘使上游企業采取有效率的努力水平;當上下游企業信息不對稱時,下游企業可對低成本參數型上游企業提供固定價格合同,對高成本參數型上游企業提供成本分攤合同,盡管此合同菜單使高成本參數型上游企業的努力水平向下扭曲了,但它避免了低成本參數型上游企業模仿高成本參數型上游企業。
生態產業鏈 完全信息 不完全信息 價格激勵合同
一、引言
1989年9月,Frosch和Gallopoulos提出了生態產業鏈的思想。所謂生態產業鏈,是指企業間通過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食物鏈,將上游企業的副產品作為下游企業的原料,形成的具有產業銜接關系的企業聯盟。生態產業鏈既可將上游企業的副產品進行充分利用,同時也可消除由它帶來的環境污染。因此,它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學者、政界、企業界的廣泛關注。
對于生態產業鏈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從宏觀、整體的角度進行研究,即探討生態工業園區或生態工業區域的形成條件和方法、穩定性以及演化規律。而從微觀角度(上下游企業之間)研究生態產業鏈形成條件的文獻極少。王秀麗和李春發、任海英和孫明、唐曉華等運用博弈論對上下游企業進行分析,探討了生態產業鏈形成的條件。朱耿先和王秀麗認為生態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之間是委托代理關系,簡單探討了其中的道德風險問題。筆者認為生態產業鏈歸根結底是一條商業鏈,必須符合雙方的經濟利益才能形成。一般而言,上游企業的副產品不可能自然成為下游企業的原材料,必須按照下游企業的要求進行改造后才能成為下游企業的原料。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需要付出成本,它愿不愿意按照下游企業的要求做取決于下游企業對改造副產品的定價。筆者正是探究下游企業如何定價才能有效激勵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從而形成生態產業鏈。
二、問題描述和模型假設
我們考慮兩企業,一企業(在此為上游企業)的副產品經過改造后能成為另一企業(在此為下游企業)的原材料。上游企業愿不愿按照下游企業的要求改造自己的副產品(即能不能形成生態產業鏈)取決于下游企業對改造副產品的定價。它們之間的博弈順序如下:下游企業根據對上游企業改造成本的觀察提出價格合同和改造要求,上游企業根據自身的成本結構決定是否接受合同,如果接受合同,按要求改造后交給下游企業,下游企業完成支付。上游企業的改造成本是公共信息(可以從會計賬戶中觀察到),但成本結構(即組成各部分的具體值)卻是上游企業的私有信息。下游企業和上游企業之間的目標是沖突的,下游企業希望少付出,而上游企業希望多獲得。由此可見,上下游企業之間形成典型的委托代理關系,下游企業為委托人,上游企業為代理人。
為了簡化,我們假定上游企業的副產品產出固定(標準化為1),并假定一件副產品可改造為下游企業的一件原料產品,下游企業接收上游企業改造后的所有副產品。假定上下游企業都為風險中性。

三、模型構建與解析
1.完全信息下的最優合同。首先我們假定,下游企業可以觀察到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發生的成本c及成本參數η。由于存在關系:c=η-a,由此可以推斷出努力水平a。可見,上下游企業之間滿足完全信息假定。
在此情況下,下游企業的支付價格為:P=w+c=w+η-a

對于上游企業而言,接受合同得到的收益至少與它處在這種關系之外一樣多。我們將上游企業外部機會的保留效用標準化為0。相應地,上游企業的理性參與約束是:U≥0。對于下游企業而言,它希望自己的支付最小化。
于是,下游企業設計的激勵合同可表示為:

其中,(1)式是下游企業支付最小化目標函數,(2)式是上游企業的理性參與約束。由于上游企業參與約束并不產生激勵,在最優的情況下下游企業沒有必要支付上游企業更多,參與約束為緊,即等式成立。
求解上述的最優化問題得:

命題1:完全信息下的最優激勵合同特征如下: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提供固定價格合同,上游企業成為所節約的成本的剩余索取者,因此,上游企業采取有效率的努力水平(a*=1),信息租金為零。
2.不完全信息下的最優合同。現在,我們假設下游企業能夠觀察到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發生的成本c,但是不知道η的真實值,因此就不能監督努力水平a。在此情形下,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同時存在。為了簡化,我們假定η存在兩種情況{ηL,ηH},且ηL<ηH,令△η=ηH-ηL。下游企業對η值有一個先驗信念:Pr(η=ηL)=γ,即Pr(η=ηH)=1-γ。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合同可以建立在雙方都可觀察的w和c之上,下游企業觀察到上游企業發生的成本c并給上游企業轉移支付w。即下游企業向每一種類型的上游企業提供一個價格合同{w(η),c(η)},也就是說,對ηL型上游企業(付出a(ηL)=ηL-c(ηL)的努力)提供合同{w(ηL),c(ηL)};對ηH型上游企業(a(ηH)=ηH-c(ηH))提供合同{w(ηH),c(ηH)}。博弈時序如下:下游企業針對不同類型上游企業提供價格合同菜單{w(η),c(η)},如果上游企業接受這個合同菜單,那么它首先要宣布它的參數,然后下游企業要求上游企業以生產成本c()進行生產,并且接受轉移支付w()。
在此情形下,下游企業的期望支付為γ(w(ηL)+c(ηL))+(1+γ)(w(ηH)+c(ηH))。我們用U(η)=w(η)-φ(η-c(η))來表示當η型的上游企業選擇設計好的價格合同時它的收益。也就是說,對ηL型上游企業,它的收益為U(ηL)=w(ηL)-φ(ηL-c(ηL));對ηH型上游企業,它的收益為U(ηH)=w(ηH)-φ(ηH-c(ηH))。為了表述的簡化,令wL=w(ηL),cL=c(ηL),aL=a(ηL),UL=U(ηL),等等。
對上游企業來說,激勵相容約束滿足ηL型(ηH)企業選擇對應的合同獲得的收益不低于它模仿ηH型(ηL)企業選擇相應的合同獲得的收益。因此有:

每一類型上游企業的理性參與約束是:UL≥0;UH≥0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最優激勵合同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4)式是下游企業支付最小化目標函數,(5)(6)式是上游企業的參與約束,(7)(8)式是上游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
經分析,起作用的激勵約束是ηL型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而起作用的參與約束是ηH型企業的理性參與約束,并且它們在最優點都是緊的。于是,最優激勵合同簡化如下:

命題2:不完全信息下的最優激勵合同特征如下:對ηL型上游企業來說,下游企業比完全信息下多支付信息租金a2H2-(aH-△η)22,努力水平同完全信息下的努力水平是相同的,并且得到正的租金;對ηH型上游企業來說,下游企業少于完全信息下的支付,努力水平比完全信息下的努力水平低而且沒有租金,并且降低努力水平aH的激勵將隨成本參數的差異和面對ηL型企業概率的提高而增加。
由此可見,ηL型上游企業可以模仿ηH型上游企業使下游企業出讓一部分信息租金給 ηL型企業,其值為 a2H2-(aH-△η)22,令T(aH)=a2H2-(aH-△η)22。可見,信息租金是對ηH型上游企業要求的努力水平的遞增函數(T、>0),它意味著企業在高強度的激勵方案(誘發較高的努力水平)下比在較低強度的激勵方案下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租金。如果下游企業堅持得到最優的努力水平,即cH=ηH-a*,那么結果將是ηL型上游企業得到較高的租金。為了降低高額的租金,下游企業需要降低向低ηH型上游企業要求的努力水平。從圖1可見,從ηH型上游企業誘發努力水平a*相應于其零效用無差異曲線上的A點,而不是B點。但這就要求ηL型企業移向代表更高效用水平的無差異曲線(從C點移向D點),信息租金也就越高。因此,對于下游企業來說扭曲努力水平來抽取租金是最優的。

圖1 滿足激勵相容約束
四、結語
下游企業對上游企業改造副產品的合理定價是構建生態產業鏈的關鍵問題,筆者針對完全信息情況下和不完全信息情況下最優合同的對比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當上下游企業信息對稱情況下,下游企業能夠觀察到上游企業副產品的成本參數和努力水平,因此下游企業可以通過提供上游企業固定價格合同,以引誘上游企業最小化成本和負效用,并因此選擇有效率的努力水平。
2.當上下游企業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不對稱信息使下游企業不得不向上游企業讓出高額的租金。為了降低這些租金,資源配置就會受到扭曲,偏離了最優的配置而接近了低強度的方案。
在實踐中,下游企業可向上游企業提供一個合同菜單:對低成本參數型企業提供價格固定合同,對高成本參數型企業提供成本分攤合同(用一個較低的固定價格加上分攤的事后成本的一部分)。此合同菜單使高成本參數型企業的努力水平向下扭曲了,但它降低了低成本參數型企業獲得的信息租金,從而避免了低成本參數型企業模仿高成本參數型企業。
[1]RA Frosch,NE Gallopoulos.Strategies for manufacturing[J].Scientific American,1989
[2]Cote R,Hall J.Industrial parks as ecosystem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995
[3]Pierre D.Cities and Industria1Symbiosis: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2
[4]Jacobsen,N.B.Industrial symbiosis inKalundborg,Denmark—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6
[5]Cote P,Rosenthal E C.Designing eco-industrial parks:a synthesis of some experienc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998
[6]James S B,Keith B.Modeling Industrial Ecosystems and the Problemof Evolution[J].Progress in Industrial Ecology,2004
[7]David G,Pauline D.Reflections on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ecology through eco-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7
[8]Allenby B,Cooper W E.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ecology from a bi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J].To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4
[9]Baas,L.W.and F.A.Boons.An industrial ecology project in practice: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decision-making levels in regional industrial system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4
[10]Chertow,M.and J.Ehrenfeld.Organizing self-organizing systems: Toward a theory of industrial symbiosis.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12
[11]王秀麗,李春發.生態工業鏈構建中的博弈分析[J].系統工程,2006
[12]任海英,孫明.生態工業園中企業間合作的博弈分析[J].經濟論壇,2008(1)
[13]唐曉華,王廣鳳,馬小平.基于生態效益的生態產業鏈形成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7(11)
[14]朱耿先,王秀麗.生態產業鏈中的委托代理問題研究[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廣東廣州 510006)
(責編:呂尚)
F062.2
A
1004-4914(2014)12-06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