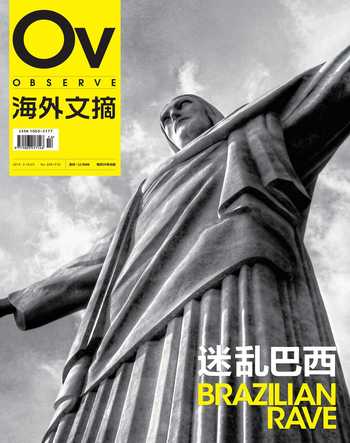巴西利亞|用50年長大成「城」
對于一座城市來說,年頭是上天的恩賜,但也有一點殘酷。具體到巴西利亞,時間最重要的意義在于,50年的變遷讓它不再是一個“愣頭青”,不再僅僅是一個坐落在偏遠熱帶地區的聯邦政府駐地。現在,巴西利亞的角色是,一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投資的中心,特別是在IT業及相關的知識經濟領域,此外,它的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包括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著名旅游城市。
自從誕生了建設巴西利亞的想法,這座城市就一直屬于未來。1891年,有人提議在巴西的陸地中點——中部高原(altiplano)開辟一片面積1.44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作為聯邦特區,如此一來,就可以帶動內陸經濟的發展,并將這個跟美國差不多大的國家在政治和地理上更好地統一起來,但該提議被巴西的第一部聯邦共和國憲法否決。此后,這個夢想被塵封了半個世紀,直到1956年,雷厲風行的新總統庫比契克(JuscelinoKubitschek)上臺執政,夢想終于開始變成現實,舊都里約熱內盧西北900公里,新首都從灌木叢林里拔地而起。1960年,巴西利亞正式開啟,盡管它尚未完工,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一片泥漿中的現代主義。
巴西利亞為世界所知,多半歸功于奧斯卡·尼邁耶設計的眾多未來主義建筑。尼邁耶善于用混凝土構筑曲線俯沖而下,逐漸變形為雅致的立柱,這些建筑常常臨水而立,頗具戲劇效果。這些建筑的現代主義形式美感冠絕20世紀,比如伊塔馬拉提宮(Itamaraty Palace,巴西外交部所在地)倒映在水池里的弧線,或者王冠狀的大教堂(MetropolitanCathedral),特別是在夜晚燈光的照射下。不過,還有一個人在巴西利亞的成長史中起過根本性的作用,從長遠來看,這種影響到底是好是壞,還很難斷定,此人就是盧西奧·科斯塔(Lúcio Costa),他以革命性的理念設計了巴西利亞。在科斯塔的理想中,巴西利亞將是一個容納50萬人的城市,各個階層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環繞在人們周圍的,是巨大的綠地公園,每一片綠地上的每一片葉子都是規劃好的。城市主干道的規劃著眼于大局,汽車在其中暢行無阻,連紅綠燈都省了,這樣就不會出現堵車的情況。
巴西利亞的確在部分按照設計師的預期運行,不過跟科斯塔夢想的理想狀態相去甚遠。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巴西利亞是個無階級差異的社會,因為住在這里的都是富人,或者至少是在經濟上相對寬裕的人。窮人住在郊區的眾多衛星城里,離市中心至少20公里,那是一些永遠不會被印到明信片上的、令人絕望的貧民窟,很多年來,生活其中的人為巴西中產階級的繁榮生活貢獻了他們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巴西的勞動力過剩),自己卻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此外,這片設計容納50萬人的聯邦特區涌入了250萬人,如果算上Goiás州邊界附近的Contorno城,這個數字將是350萬。
這種人口爆炸無可避免,雖然這么說起來有點“事后諸葛亮”。50年前,數萬農民來到巴西利亞參與它龐大的建設工程,他們中的很多人很自然地想要留下來。50年后,巴西利亞依然在吸引著巴西的窮人,特別是來自東北部的、飽受干旱困擾的農民。對于一個佃農來說,只要能進入公共部門工作,哪怕是最底層的工作,也會獲得一生的保障和難以想象(對于一個貧窮的農民來說)的各種收益。當然,很多移民從未得到過這種“涅槃重生”的機會,只有少數幸運兒(或是其后代)才有機會上大學,進入上層社會。
有趣的是,所有這些移民把首都變成了各種文化和種族的民主大熔爐,這正是巴西的眾多特質之一。在這里,政客及其幕僚來自全國各州,知識分子則大多出生在南部和東南部地區,盡管如此,從總體上看,東北部移民及其后代在這兩個階層中的人數卻占據優勢。在這一點上,巴西利亞比里約熱內盧和圣保羅更能反映“真正的”巴西。
在一項基本指標上,巴西利亞不同于任何一座巴西城市——它很富有。聯邦政府和聯邦特區政府超強的購買力,加上高工資、高津貼的政府雇員,為本地服務業(從加油站、餐廳到律師事務所和IT公司)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這方面的數據令人印象深刻。整個聯邦特區(算上巴西利亞周圍那些破破爛爛的衛星城)的人均國民收入是巴西最富有的州(圣保羅)的差不多2倍,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還多。相比任何一個州,巴西利亞有更多的電腦、寬帶連接和手機,有全國最高的高等教育質量、識字率和平均壽命。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顯示,巴西利亞的指數與德國相當,巴西各地更是被遠遠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