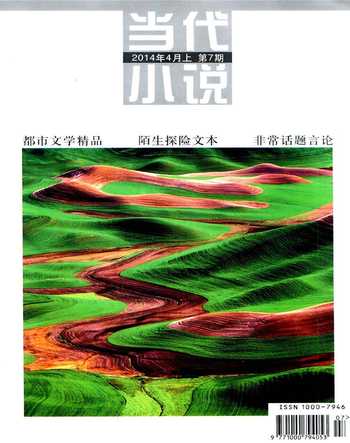溫泉蛋
樊健軍
同張戈廝混在一起后,認識尹先生就是一種必然。后來我曾疑心張戈早有預謀,但這樣的懷疑沒有了任何意義,因為事情已過去了多年,我離開了張戈,即便當時他引誘我做過什么,我也不可能責問他,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至于尹先生,之后我也沒有再見到過他。
第一次見到尹先生是在一個郁悶的下午。那些日子我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一個人呆在張戈租的房子里,除了吃飯就是睡覺,或者守著那些無聊的肥皂劇,偶爾會翻閱一下張戈帶回來的幾本美容雜志。雜志也沒有什么特別精彩的內容,宣揚的是什么樸素主義,純棉的衣衫,單調的顏色,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可它的說詞還是有點煽情,薄施脂粉,素面朝天,擁有一種樸素的美麗。用它們的說法,不穿衣服是最最樸素的美麗了。我翻了幾頁,就看不下去了,隨手將它們扔在了沙發的靠背上。可能力量過了一些,它們又順著靠背的另一面滑了下去。后來是啪的一聲響,它們掉到了沙發背后的地板上。
我懶得理會它們了。因為那時候我的手機恰好響了,肯定是張戈的電話。自從我與他同居后,他就要求我更換了手機號,你那都是些什么朋友呀,還有必要保持聯系么。并且他不讓我將號碼告訴任何人,除了家里人,打別的電話一律上公用電話亭。
青子,穿上那身白色的連衣裙,我帶你兜風去。張戈在電話里說。
聽他說到連衣裙,我的腦子里出現了短暫的空白。我壓根兒不喜歡那件裙子,除了在超市里試穿了一次,后來它就沒在我面前閃過眼。我極力在記憶里搜索,它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裙子在衣櫥底下的購物袋里,你動作快一點,我馬上到樓下了。張戈又來了一個電話。我在衣櫥的底部找到購物袋,將裙子套在了身上。就照著鏡子轉一圈,裙子很熨帖,沒有一絲皺褶,鏡子里的我真有了些樸素之美了。我敢說這不是裙子的效果,而是我的身材特別魔鬼,是我讓裙子變得更漂亮了。這是我惟一驕傲的資本,除了這個,我什么也沒有了。
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南方的小鎮,離海邊不遠,周邊還有很多的風景點,溫泉漂流避暑山莊什么的。原以為張戈會帶我去海邊兜風,誰知上了車他卻一直往北開。我一個人去送樣品,挺悶的,有了你我就不悶了。你閑著也是閑著,正好出去散散心。張戈嬉皮笑臉的,一句好話到他嘴邊絕對變了味。我繃了臉,目光全落在了窗外。等會兒見了我的客戶,淑女點。他并不在乎我一臉慍色,又拿手在我臉頰上捏了一把。我對著他的手背扇了一掌,可他的手比老鼠溜得還快,我的手掌落空了。
三個小時后,我們來到了一個鎮上,車子左繞右拐,最后在鎮子背后的一扇鐵門前停住了。張戈摁了幾聲喇叭,有人推開了鐵門,車子進去了,泊在了一片矮房前。這是一個并不怎么闊大的院子,院子中央有花有草,還有幾株三葉刺葵。左邊是一幢二層的樓房,右邊是一層的平房。有個女孩站在左邊的房檐下向我們招手,她的目光冷冷的,臉上也沒什么表情。張戈打開行李箱,從箱子里抱出一個小紙盒,扭頭眨了一下眼,示意我跟著他。我看不慣女孩的冷眼,靠在車門邊不想動,但后來張戈的背影將她擋住了,我才走了上去。
我們進去的是一間空曠的客廳,布置簡單,幾張紅木的沙發,幾個紅木的茶幾,墻角兩棵叫不上名字的植物,細碎的葉子,是一種很靜態的綠色。張戈將小紙盒放在一只茶幾上,在就近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我不想看女孩的臉色,故意沒有落座,而是朝一堵墻走了過去。那兒有一幅風景照片,黑白的,是一個平靜的山谷,霧氣繚繞,景物若隱若現。我在照片前停住了。我感覺身后有一雙眼睛,冷冷的,在偷偷打量我。我回轉身,剛好撞上了那個女孩的目光。她正彎著身子在飲水機前倒水,撞上我的目光后她趕緊低了頭,她的手跟著抖了一下,有水從杯子里溢了出來。我裝出大大方方的樣子朝她走了過去,從她手里接過一只杯子。接過杯子的時候,我朝她笑了笑,只有我自己清楚,那絕不是一種友好的笑。
尹先生呢?張戈問。
在樓上的工作室里。女孩將另一只杯子放在了張戈面前的茶幾上。
那我將樣品送上去。張戈捧起茶幾上的紙盒子,抬腿就往樓梯口走。
尹先生可不喜歡陌生人參觀他的工作室。女孩扭身阻住了張戈的去路,她揚著臉,臉上依然是那種冷冷的表情。
張戈不得不折了回來,重新回到座位上。女孩接過紙盒子,輕輕悄悄上了樓,臨近樓面的時候,她回了一下頭,她的冷眼又從我臉上掃了過去。
約摸一刻鐘后,有個男人從樓上走了下來,他的個子不很高,上身穿一件暗紅的T恤,下身是一條牛仔褲,一頭短發,嘴巴不停嚼著什么。尹先生。張戈趕緊從沙發上彈起身,迎到了樓梯口。我也直起了腰身,從遠處,向男人微笑著。不過我是浪費表情了,他并沒有看見我的微笑,他的注意力全在張戈那兒。張兄弟,請坐。他一只手摟住張戈的肩膀,另一只手做了個請的手勢。他的嗓音有些啞,是那種低沉的沙啞,聽起來很有力量。
這位是——就在我準備重新入座的時候,尹先生的臉轉了過來,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但他的問話生生斷去了一截,他的表情像是被什么凍住了,嘴巴微微張著,一雙眼睛像蚊子一樣釘在了我臉上。我向他微微笑了笑,而他好像沒有反應過來,身子僵直,眼神一動不動。那表情像是驚愕,又像是激動,似乎還有別的什么,我說不準。我記不清自己見沒見過這張臉,它不胖不瘦,眼下有鼓脹的眼袋,唇邊有一線燒焦的黑紅。我極力在腦子里搜索,但我什么也沒有找到。我有些擔心,也許我見過尹先生,說不定還陪他喝過酒,可能我忘記了。我見過太多的男人,他們看見我時就是這樣子,目光呆直,身體僵硬,甚至嘴角會流下涎水。他們留給我的印象就是這種赤裸裸的欲望,眼前的這個男人似乎也不例外。
都什么人呀,還要我淑女一點呢。我覺得真可笑,朝張戈眨巴了一下眼睛。可奇怪的是張戈正死死盯著尹先生的臉,好像要從他臉上捕捉到什么。過了大半晌,他才不急不慢走過來對尹先生說,這是我女朋友,青子。尹先生,請多關照。我再次向尹先生微微笑了笑,鞠了一躬。青子,是仙子吧。尹先生這才醒了過來,呵呵笑了兩聲,遮掩了剛才的尷尬。他很快將目光從我臉上挪開,轉向了張戈。張兄弟,你太恐怖了,找了個這么漂亮的女朋友。張戈嘿嘿笑了,一臉偽裝的得意。
認識張戈之前,我在一家娛樂城里陪男人們唱歌跳舞,打情罵俏。在南方,這種娛樂城遍地都是,像我一樣的女孩比天上的星星還多。如果客人出手大方,我還會同他一起去賓館開房,顛鸞倒鳳地過上一個夜晚。但我從不攬回頭客,我不想有人認識我這張臉。我只想從他們身上撈到一筆錢,然后離開這個鬼地方,徹底告別,去另一個地方開始新的生活。那時候,我就不需要為了錢陪男人喝酒睡覺了,我可以抱著自己喜歡的男人,抱著他過上一輩子。
而事實上我總是攢不夠這筆錢,我輾轉了好幾個地方,收獲甚微。我越想快點結束這種生活,生活卻怎么也不答應。我不停地更換地方,一方面是為了回避熟客,另一方面是想尋找一個賺錢更輕松的地方。就在那家新開的娛樂城里我遇上了張戈,準確說是他抓住并誘惑了我。一個晚上,我同眾多的女孩子在大廳列隊迎客的時候,發現一個留著長發的男人在遠處向我招手。他生怕我沒看見,一只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另一只手也是一個八字。我是八十八號,但我沒有動。那男人急了,三步兩步跳了過來,一把攥住我的手,將我從人堆里拽走了。那個男人就是張戈。
我被他帶進了一個小包廂。這個瘦小的男人用在女人身上的力量卻是不小,他的手指生生扎進了我的腰眼里,我掙了幾次都沒掙脫。掙什么,我看上的女人沒有逃得掉的。張戈一邊挾著我往里走,一邊附在我耳邊說。你弄痛我了。我說。痛了你才會記得。你怎么一點都不懂得憐香惜玉?我有些惱怒。憐香惜玉?這不就懂了。說話間,他的另一只手向我的胸前悄悄摸了過來。這一回我沒讓他得逞,而是扭身掙脫了他的懷抱。在沒有得到客人任何好處之前,我絕對不會給他們半點便宜。這是我長期遵守的原則。
后來,歌唱了,酒也喝過了,張戈將一沓鈔票卷成一個卷,塞進了我的乳溝。我坐著沒動,任由他的手在我的胸部摸索。我沒理由拒絕一個慷慨的客人,更沒理由拒絕送上門的鈔票,雖然它放得有些不是地方,但我還是忍耐著接受了。
不再罵我不懂憐香惜玉了吧?張戈嬉皮笑臉地說。
先生,你真壞。我假裝生氣了,用拳頭輕輕在他胸口捶了一下。
跟我走吧。張戈又是一臉曖昧。
……我朝他打了一下響指。我不太敢相信眼前的這個男人,他長了一張窄窄的臉,兩邊的長頭發本意是想增加臉的寬度,結果反而將臉壓得更窄了,眼睛鼻子嘴巴成了一根線。一個相貌如此猥瑣的男人,他到底能有多么慷慨。我的心里沒譜。
張戈很快豎起了一根指頭,說,月薪。
搶銀行?我笑著問。
用尹先生的話說,別說得太恐怖了,我舍得讓一個美女去冒險么。張戈拿指頭在我鼻子刮了一下說,做我的業務經理,做成功一筆業務再給你百分之十的獎金。
就那樣,我鬼使神差成了張戈所謂的業務經理,當天晚上就跟隨他一起回到了他的住處。除了陪他睡覺以外,其實我什么事情也沒有做。不過張戈并沒有因為這個而食言,另天早上他就給了我一只信封,信封里是厚厚一沓人民幣。在娛樂城里,我喝一個月的酒,賠上一個月的笑,包括偶爾陪男人上床,運氣特別順的話勉強能湊到這個數。當然,我更渴望的是能拿到那百分之十的獎金。我猜想,他也許用這種方式招聘過不知多少女孩子,但那不是我該關心的事。只要這部取款機的肚子還是鼓鼓的,我要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一件了,那就是不停地插卡,按鍵,從出鈔口拿走屬于我的鈔票。
去了一次之后,再見到尹先生的次數慢慢多了。后來每次送樣品,張戈都要求我與他一同前往。這種差使看起來很輕松,其實怪無聊的。我坐在旁邊,一句話也說不上,純粹成了一種擺設,還不如陪男人上床來得刺激。最重要的是我還得承受那個女孩的冷眼,雖然她沒有什么更過激的行為,但眼里深藏的那份戒備我還是看得出來,不過我有什么值得她戒備的呢。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她也許同我一樣,只不過是尹先生的一個所謂的業務經理。對一個漂亮女人的確要有些戒心,說不定哪天她手里的取款機被別人搶了去,而她還蒙在鼓里呢。
但我的猜想很快被尹先生打斷了。
你板房的工人也太恐怖了,你看,這邊的花紋足足短了半公分。尹先生指著茶幾上的一個紙盒子說。
尹先生,對不起,我馬上叫他們重新打樣。張戈一邊說著,一邊向我丟了一個眼色,示意我上前幫幫腔。
挪動位置的時候,我注意到那個女孩又在冷眼瞅著我。我沒有理會她的眼色,這會兒張戈是我的上帝,上帝發了話,我不敢不過去。尹先生,真不好意思,技術員的母親病了,請了假。不周到的地方還請多多關照,.我們一定依照您的意思改過來。我挪到了尹先生鄰近的一張沙發上,笑著說。尹先生仰起了目光,正巧撞著了我的笑臉,他好像很害怕在我臉上停留,很快又回到了那個紙盒子上。
我給你的樣品呢?尹先生問。
哦,在車上,我現在就拿過來。張戈趕緊跑出了客廳,轉眼抱了一只一模一樣的盒子進來。
你讓技術員好好瞅瞅我做的這個盒子,這種盒子講究的是對稱美,兩邊的花紋要對稱,少了半公分,美就全部破壞了。另外花紋的顏色也艷了一點,我需要的是一種古樸端莊的色澤,而不是花哨俗氣的艷麗。尹先生說。
看起來同樣的兩只盒子,可一旦放在了一起,它們的差距就明顯了。原來擺在茶幾上的那只盒子成了丑.八怪,盒子兩邊的花紋雖然也像兩彎半月一樣排列著,可左邊的花紋短了半公分,那感覺有點像一個明眸皓齒的女孩缺了兩顆門牙,怎么看都有些難受。而且盒子的表面是一種淺色調,有些類似木頭紋理的淡淡線條,用那樣鮮艷的花紋很不諧調。而張戈剛剛抱進來的那只盒子就不一樣了,它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美女,那兩串花紋就像兩條小辮子,一個淡妝的古典美人。
尹先生,你真的太恐怖了,做了一只這么漂亮的盒子。
我用尹先生的口吻笑著說。我的語氣聽起來有些夸張,不過我的贊美是由衷的,是發自內心的。一個看上去粗手粗腳的男人,能夠糊出一只這么漂亮的盒子,有些讓人不太敢相信。也許是張戈的那些雜志起了作用,我居然有些喜歡這只盒子了。
聽了我的話,尹先生呵呵地笑了,那模樣就像一個偶然受到大人夸獎的孩子,一臉的生動。青子小姐,這句話我是申請了專利的,說一次就得給我十萬元。尹先生說。是美元還是英鎊?我問。你讓我想想,尹先生沉思了片刻說,都是朋友么,我少收一點,就英鎊吧。可我只有秘魯幣啊。我一臉的愁眉苦臉。沒想到尹先生又一次呵呵笑了,他用手指著我,回頭對張戈說,張兄弟,你看你這個女朋友,真是一個調皮的小丫頭,你也不管教管教。尹先生,可不許你這么說,要是哪天張戈欺負了我,我找你算帳。我故意拉長了臉。唉,說漏嘴了,那十萬英鎊我就不要了,再罰我請你吃頓飯,賠償你的精神損失,愿不愿意賞臉?尹先生一臉負荊請罪似的表情。我大人不計小人過,這頓飯我吃定了。我朝尹先生做了一個鬼臉。
原以為可以山珍海味胡吃一頓,不想卻是極為簡單的一頓便餐,四菜一湯,一碟青椒肉片,一碟青菜,還有兩碟米糕,一碟是蒸的,另一碟是煎的。湯是肉片湯,上面浮了些青菜葉。尹先生,你真是太恐怖了,就這么打發我呀?我又開起了尹先生的玩笑。菜雖然不是山珍海味,可我的廚師工資高啊,沒有十萬元他是不會進廚房的。尹先生被我說得一愣,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做尹先生的廚師真幸福呀。我咂咂舌,一臉羨慕的表情。說說笑笑的,那頓飯吃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離席的時候,我們被尹先生攔住了,別急,還有一道壓軸菜。他扭頭吩咐那個冷眼的女孩,影子,去廚房將電飯煲端過來。那個叫影子的女孩很快將電飯煲端了過來,揭開鍋蓋,原來是半鍋的雞蛋,正呼呼冒著熱氣。這可不是普通的雞蛋,而是溫泉蛋,溫泉蛋,吃過沒有?尹先生用湯匙給我們每個人撈了一個雞蛋,放在碟子里。蛋有些燙手,小心去了殼,露出嫩嫩滑滑的蛋白,輕咬一口,蛋白立刻化了,滿嘴都是蛋的香味。奇怪的是它的蛋黃卻熟透了,不像蛋白一樣還是近乎液態的。我有些不解地盯著尹先生。
青子小姐,這可是商業秘密,不能隨隨便便告訴你,我還指望開間溫泉蛋專賣店呢。尹先生說。
疑惑間,尹先生一直盯著我在看,他的臉上有些調皮的得意,又有些藏掖不住的狡黠,好像還有別的什么。不過,我看不清那是什么。而且,我還發覺那個叫影子的女孩始終冷眼瞅著我,那雙大眼睛里的內容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真小氣。我朝尹先生噘起了嘴。
去過溫泉嗎?去了溫泉就知道了。后來,尹先生說。
有關尹先生的事情,張戈陸陸續續告訴了我一些。尹先生只有一間工作室,十幾個人,每年卻能做上二三個億的生意。平常他哪里也不去,就關在工作室里,不斷畫圖,裁剪,設計,出了新樣,就分散交給張戈這樣的工廠加工。張戈每年接手的新款多達上百個,而他只做了尹先生不到二十分之一的生意。尹先生真是聰明呀。張戈長嘆了一聲。
就這一些?我懷疑張戈知道的絕對不只這一些。
還不夠嗎?你想聽多少?張戈攤了攤手,說。
尹先生是哪里人?我問。
不知道。可能是南方人,也可能不是。張戈又攤了攤手。
那個叫影子的女孩是他什么人?這是我最想知道的。
你去問尹先生吧。不過肯定不像你和我。說話間,張戈又不安分了,他的手突然向我的腰部抄了過來,我扭身脫開了。我不想無緣無故讓他占便宜。
我有一樣東西送給你,不要了?張戈撲了空,反身從茶幾的抽屜里拿出一只花花綠綠的紙盒子,誘惑著我。
哼,是哪個女孩子不要了的吧?我近乎用鼻音回答了他的誘惑。但我還是接過了盒子,不管什么東西,只要不是死尸,先拿了再說。拆開一看,是一部手機,握在掌心,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還有攝像功能。我有幾分喜歡。
說吧,要我做什么?我問。
以后送樣品的事就交給你了。張戈趁機又湊近了我。
這么簡單?我有些不相信。
如果你進了尹先生的工作室,幫我拍些照片出來。張戈附在我耳邊說。
你說什么?我懷疑自己沒聽清楚。
如果你進了尹先生的工作室,幫我拍些照片出來。張戈又在我耳邊重復了一遍。
你還是收好你的手機吧,我干不了。我將手機放在了茶幾上。
如果成功了,我會重重獎賞你的。張戈拿起手機塞回我手里。
……
張戈豎起了二根指頭。
尹先生能讓我進他的工作室?我有些懷疑。
你一定進得去。張戈的語氣非常肯定。
明天去吧,影子應該不會在。他又補充說。
我有些猶豫,但還是應允了下來,張戈的二根指頭對我來說可不是個小數目。如果有機會可以避免用自己的身體賺錢,我想我不應該放過。
第二天,張戈派了一個司機,將我送到了尹先生的院落。院子里靜悄悄的,什么人也沒有。那個冷眼的女孩也不在房檐下。我有些忐忑地朝客廳走了過去,客廳也是靜悄悄的,沒有人。我在那幅照片前站住了,沒有貿然走向樓梯口,因為我擔心那個冷眼的女孩會忽然出現在背后。那幅照片應該有些年月了,邊緣有些微泛黃,不過畫面依然相當清晰,那繚繞的水霧之下有幾潭流水,緩慢的流水,甚至可以聽見它流動的聲音。我在照片前立了一會兒,并沒有什么人出現,我才放心走近了樓梯口。
尹先生。我朝樓上叫了一聲。過了好久,我沒有聽到回音。
尹先生。我加重了聲音。
這一回,樓上很快有了動靜,腳步聲近了樓梯口,一條藍色的牛仔褲進入了我的視線。喲,是青子小姐,上來吧。尹先生一臉的出乎意外。我不敢。我耍了個欲擒故縱的伎倆,聲音還是有點怯怯的。我是老虎呀?怕我吃了你?這個半老頭居然揚起雙手,做了一個張牙舞爪的動作。我猶疑地看了一下身后。影子不在。尹先生看出了我的猶疑。后來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了一掌,說,肯定是這小丫頭使了壞,別聽她的,上來吧。事實上我并不是很擔心影子的冷眼,只是我想,一個女孩走近一個男人的時候,被另一個女孩擋住去路,這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情,特別是這個女孩懷著某種目的,如果被她看破,就有可能雞飛蛋打了。
那我真上來了,到時你可別趕我出來。我說。
尹先生沒再說什么,只揮了揮手,讓我快點上去。
同樓下的客廳一樣,尹先生的工作室也布置得相當簡單,靠近入口處是一張闊大的工作臺,直尺,剪刀,紙板,各種顏色的花邊,滿桌都是。桌子的左角上放了一部固定電話,同它相對應的右角上擺著一個橢圓形的紙盒子,有可能就是今天我要拿走的樣品。這張工作臺只占了工作室很小的一部分,它的絕大部分空間被超市里那種常見的貨架占據了。貨架上擱滿了各式各樣的盒子,各種各樣的形狀,眼花繚亂的顏色,有些盒子是常見的,比如紙巾盒,月餅盒,而大部分的盒子我根本沒有見過,更不要說知曉它的用途了。
尹先生,你真的太恐怖了!我被這滿房的盒子弄暈了,我想我特別放大了我的聲音。
但尹先生似乎沒有被我的聲音打動,他抱著膀子立在工作臺前,靜靜看著我。他的嘴角有微笑翹在那里。
尹先生,我可以……我小心翼翼地問。
請吧,小丫頭。尹先生說。
在一排貨架的后面,我從手提袋里拿出手機,發出了一條早已設定的信息,張戈很快撥響了我的電話。我假裝一邊同張戈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一邊摁下了攝像鍵,然后在貨架中緩慢穿行。在快要接近貨架底部的時候,我忽然聽到了尹先生的腳步聲,他在向我走來。我以為他發覺了什么,我趕忙收起了手機,從貨架后轉了出來。
事實上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尹先生什么也沒有察覺,他端了一只杯子立在過道里,他的身后是另一個門口。從門口出去,是一個小陽臺。站在陽臺上可以看見一片更寬敞的房子,用鋼管搭建的,那種臨時的房子,足有七八間工作室的面積,里面是更多的貨架,更多的紙盒子。有幾個人影在中間忙碌著。這是我助手們的工
作室。尹先生說。陽臺有樓梯通向下面,但我沒有走下去,我想我應該向尹先生告辭了。
往后,我去過尹先生的工作室好幾次,有一回我還從陽臺前的樓梯走了下去,深入到了他助手們的工作室。我用張戈給我的手機拍攝了許多照片,張戈說話算話,又給了我一只厚厚的信封。只是我不明白,尹先生為什么單單允許我進入他的工作室,而且張戈還確信他會讓我進去。我為這事問過張戈,張戈說,男人么,哪個不喜歡漂亮的女人。他認定的理由就是這么簡單。
對于張戈的說法,我是半信半疑。后來,尹先生送過我一件小禮物,是一枚雞蛋形狀的水晶球,上面不知用什么刻了一幅圖畫,畫面就是他客廳的那幅照片,一樣的山和水,一樣繚繞的霧氣。看來尹先生是對你有意思了。我將水晶球拿給張戈看時他說。這男人哪,就是不能對女人太入迷了,特別是漂亮的女人。張戈又發出了慨嘆,但他很快話鋒一轉,又到了尹先生身上,這尹先生也太小氣了,就送了個水晶球,要是送個金蛋,那我們的青子小姐可就……張戈的話沒說完,后面是一連串的壞笑。說下去呀,究竟怎么樣?我乜斜了他一眼,張戈緘口了。
事情就這么平靜了一段時間。這期間我很少出去,也沒有見到尹先生。按照張戈的意思,每隔一個星期我就會給尹先生打個電話問候一聲,少不了說些笑話。青子小姐,有空過來玩呀,好久都沒見你了。尹先生沙啞的聲音里含著一份熱切。我還惦記著你煮的溫泉蛋呢,忙完這一陣子我一定過去。每次我都以一個相同的理由來推脫。
二個月后的一天,張戈突然對我說,青子,你約一下尹先生,這個周末我們去月牙泉玩吧。月牙泉是與鄰省交界處的一個溫泉,一彎河水流成月牙的形狀,我曾在報紙上看過有關它的廣告。太遠了,我不想去。我拒絕了他。不過這并不是我拒絕張戈的真正理由,我是擔心自己不敢面對尹先生。心虛了?女人真是沒出息。張戈一臉的鄙夷。去就去,還怕他吃了我不成?明知張戈用的是激將法,我還是答應了。因為我心理存著一份僥幸,說不定尹先生不去呢。但沒想到我的電話去得正是時候,尹先生說,我剛剛完成一份訂單,正想出去走走呢。
臨出發的時候,張戈交給我一只U盤,說,尹先生有一份客戶名單,可能藏在他的手提電腦里,你想法子幫我弄出來。張戈說得輕描淡寫的,就好像我是去逛超市,順便替他買包方便面什么的。你不要得寸進尺。我接過了U盤,塞在手提袋里。我就知道你會答應的,我的寶貝。張戈用手指在我臉上刮了一下。我可不是你的什么寶貝。這一次我沒讓他的手逃回去,一掌扇在了他的手背上。
月牙泉在北面,近三百公里的路程,有二百公里可以走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的入口處,我們見到了尹先生,他靠著一輛越野吉普,依然是那身穿著,上身是T恤,下身是牛仔褲,戴了一副墨鏡,嘴巴不停地嚼著什么。張戈響了幾聲喇叭,尹先生上了車,跟在了我們車后。上高速,再出高速,接下來是一條柏油路,靠著一條水流并不浩蕩的河流,穿過一個小鎮后就到達了一個山谷的入口,柏油路一直往山谷里延伸。臨近黃昏的時候,我們終于到了月牙泉山莊,它建在一個山旮旯里,一片紅白相間的建筑物,周圍是綠樹修竹,寂寂靜靜的。這并不是一個泡溫泉的季節,沒有多少游人。
一個晚上過后,張戈就扔下我走了。尹先生,很抱歉,公司有點急事要我回去,我處理好了就馬上趕回來。這就是他開溜的理由,還沒等尹先生回話,他又轉口對我說,青子,好好替我陪著尹先生。張戈連早飯也沒吃,就風急火燎地走了。
這小子,真不仗義。尹先生指著張戈的背影說。
他呀,就這個德性,心里只有公司。我也恨聲說。
年輕人都這樣的,青子小姐,你可別責怪張兄弟。尹先生說。聽得出他并不是真的對張戈生氣,甚至還有些許的喜歡。
尹先生,你傻了呀?他丟下我們走了,你還替他說話。我嘟起了嘴。
你這小丫頭,還讓我來勸你呀。尹先生呵呵笑了。
得了,他忙他的,我們玩我們的,回去再收拾他。聽尹先生這么一說,我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畢竟我是東道主,沒有讓客人來勸主人的道理。
早餐過后,尹先生拒絕了導游推薦的項目,沒有留在山莊內游玩,而是背了一個包,徑往山莊外走去。小丫頭,你速度快一點。他一邊走一邊回過頭來招呼我。等我追出去時,他已走出老遠的一截。我追著他,繞過山莊,拐上了靠河的一條土路,沿河而上,往山谷深處走去。河流的落差慢慢加大,道路也變得崎嶇不平。山谷卻是越發安靜了,林中有鳥在叫,一聲一聲,清脆悅耳。水流的聲音也很熱烈,汩汩響成一片。漸漸地,我和尹先生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了,他不得不停下來等我。尹先生,我們這是上哪去呀?趁著靠近他的時候我問。到了你就知道了。尹先生賣了一個關子。就這么走走停停,一個小時后,我們到了一個岔路口,河流在這里分了汊,左邊是主河道,地勢相對平坦一些,而右邊是另一個山谷的入口,河水的流量不小,路面卻是更加陡峭了。尹先生拐上了右邊的山道。一刻鐘后,我和他之間又拉開了距離,尹先生又停了下來。但這一次我沒有追上去,而是一屁股坐在了路邊的石頭上。
我走不動了。我對尹先生說。
你也太恐怖了吧?這么一點路都堅持不了。尹先生皺起了眉頭。
尹先生,你可真殘忍,沒看到人家是一個弱女子嗎?我抗議說。
對于我的耍賴,尹先生無可奈何,只得折回來,將我從地上拽了起來。但我還是不愿意往前走,鬼知道這半老頭兒要上哪里去。那你就在這里等著我吧,如果有蛇或者狼什么的,到時可別怪我呢。尹先生沒有遷就我,而是很快撒開了我的手,一個人往前走了。我只得跟了上去,這種地方不會有狼,但蛇是肯定會有的,在蛇和尹先生之間,我情愿選擇尹先生。
再往前走,是一段更為陡峭的山坡。山坡下有瀑布飛泉的聲音,響得轟轟烈烈。有些險峻的地段,我必須佝僂著身子,手腳并用,才能攀爬上去。半個小時過后,我們終于上了坡頂,眼前突然一片開朗,一個平坦的山谷一覽無遺。山谷的中央是一條紅色的河流,在陽光的映照下,就像有無數的火光在水面跳躍。特別是山谷的底部,火焰的顏色更為熾烈,似乎整座山都被燃著了。尹先生直接向那團最熱烈的火焰走了過去,不緊不慢的,走得非常從容。我的眼睛被漫天紅光傷著了,只能看見一個模糊的影子,一步一步,像是被火焰吸進心里去了。
等我追過去的時候,尹先生正蹲在一個小水潭前,他的面前是一堆白色的小紙包,用餐巾紙包裹的紙包。拆開小紙包,一枚枚雞蛋露了臉。然后將雞蛋放入一個網絲袋,再將網絲袋沉入水潭。水潭的底部積滿了紅色的淤泥,蛋袋入水攪起了紅泥,很快潭水便火紅一片。等潭水靜下來,蛋袋不見了,它完全被紅泥掩埋了。一刻鐘過后,尹先生將蛋袋從水中撈了起來,白色的雞蛋便有了淡淡的胭紅,熱氣正在裊裊散出。
吃吧,這就是溫泉蛋,正宗的溫泉蛋。尹先生說。
返回溫泉山莊是在下午,我剛掩上門就收到張戈的一條短信,短信什么內容也沒有,只有一個簡簡單單的問號。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懶得回復他。幾個小時的山路早將我折磨得痛苦不堪,腳掌上磨起了好幾個血泡,碰著地面就錐心地痛。手臂像被火烤過一樣一片炙紅,也在火辣辣地痛。這個半老頭,為了幾個破雞蛋,早知是這樣我說什么也不去。我心里不只是埋怨,還有了莫名的恨意。
我是半夜里敲開尹先生的房門的。我沒有吃晚飯,借口肚子餓了,上他的房間找吃的。正好他有白天煮好的溫泉蛋。我還帶去了一瓶紅酒,兩只玻璃杯。酒是張戈準備的,我記得他將它交給我時臉上滿是曖昧的笑。
門開的那會兒,我真疑心尹先生的房間藏了什么人。門只開了一線縫隙,縫隙里是半張臉,還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愕然。我尋思著,要不要退回去。正在我猶豫的時候,尹先生將房門拉開了,臉上的驚訝也被笑容取而代之了。你這鬼丫頭,我當是誰呢,唬了我一跳。尹先生說。我肚子餓了,你的那些寶貝溫泉蛋呢?我嚷嚷著,將酒瓶和杯子放在了小圓桌上,然后掃視了一眼他的房間,有一部手提電腦擺在靠墻的一張辦公桌上,我看見的只是一個藍色的桌面。沒有了。尹先生攤了攤手,做了個很難為情的表情。哪兒去了?我不相信。都被我吃了。尹先生說著又補充了一句,我也沒有吃晚飯。你也太恐怖了,那么多呢。我一臉的失望。呵呵,被我騙著了吧?在這呢,全給你。尹先生將網絲袋放在了我面前,臉上滿是調皮的得意。
我的確是餓了,一枚雞蛋很快下了肚。哎哎哎,你慢點吃,別噎著了。尹先生倒了一杯水,放在了我的手邊。不喝水,我們來干一杯吧。我揚了揚酒瓶。……尹先生雙手合十,做了一個拒絕的手勢。張戈說你是海量。我說。事實上張戈告訴我的是尹先生平常滴酒不沾,偶爾喝酒,半杯紅酒就會醉上大半天。我哪會喝酒呀,張兄弟可是要害我死了。尹先生苦了一張臉,像是受了莫大的冤屈。就半杯,半杯。我不管他答不答應,將兩只杯子都斟了酒。我真的不能喝。尹先生還是推辭。尹先生,我今天爬山腳板可是磨起了好多血泡,連走路都拐了,為了我腳掌上的血泡,你怎么也得喝一杯吧?我有些咄咄逼人了。我慢慢喝,可以不可以?尹先生終于端起了酒杯淺淺酌了一口。
陪人喝酒特別是陪男人喝酒,是我曾經的工作。只要他端起了酒杯,我總有辦法讓他喝下去,我怕的只是連酒杯都不愿碰一下的人。而且每個人喝酒的風格不一樣,對于尹先生,我采取的策略就是拉長時間,慢慢蠶食,穩步推進。不知不覺中,尹先生半杯酒下了肚,他的臉也成了紅酒的顏色,他的話也多了起來。來,我給你看些照片。尹先生去到電腦前回過頭來招呼我。他走過去的步態有了些微的踉蹌。
這是日本的富士山溫泉,這是印尼的火山溫泉,這是美國的西部溫泉……尹先生一邊點擊著圖片,一邊說。電腦屏幕上閃過的都是一些數碼照片,其中的風景同尹先生客廳照片上的風景大同小異。只不過客廳的照片是黑白的,電腦里的照片卻是彩色的。還有呢,這是鼓鳴泉,蛤蟆嘴噴泉,不過這些都不算什么,你看,尹先生說著又點開了另一張圖片,圖片上的畫面是一個小水潭,水潭內水花汩汩,水面熱氣騰騰。這是熱海大滾鍋,據說鍋底的溫度超過100攝氏度呢。我在鍋邊不只煮過溫泉蛋,還煮過溫泉飯呢。
再看看,這是什么?尹先生將鼠標停在又一幅照片上。照片上是一些小魚,怕有二三十條之多,搖頭擺尾的,在水里游動。我看不出這些小魚同別的魚有什么不同。這可不是普通的魚,是三亞的親親魚,溫泉里的親親魚,沒聽說過吧?說到親親魚的時候,尹先生似乎特別興奮,眼睛里也像有魚兒在游動,里面水花一片。
趁著尹先生高興的勁兒,我又給他添了半杯酒,看他那模樣,一個半杯酒恐怕解決不了問題。為了親親魚,為了你的溫泉蛋,我們干杯。我將酒杯遞給尹先生,一邊拿眼瞅著他,在一個醉酒的男人面前,我明白我該用一種怎樣的眼神。這一回,尹先生絲毫沒有推辭,而是接過杯子一飲而盡。放下酒杯的時候,他的身子歪了一下,他的一只手落在桌面上才勉強撐住了身子。我趕忙托住了他的另一只胳膊,生怕他倒了下去。不礙事。尹先生卻掙脫了我的扶持,靠著桌邊站住了。
尹先生,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我問。
什么問題?尹先生反問。
你為什么那么喜歡溫泉?這是在我心里埋了好久的一個疑問。當然,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不回答。
尹先生又歪了一下身子,但腰部被桌子頂住了,不至于傾斜得太厲害。他的臉色漸漸起了變化,紅的部分慢慢變少,而黑的部分在不斷增加,到后面黑色又被鐵青色替代了。這是一個醉酒人該有的臉色。
我再給你看張照片吧。尹先生移動了一下鼠標,電腦屏幕上突然閃出了一個女孩的照片。那是一張黑白照片,上半身的,典型的瓜子臉,又彎又細的眉,一雙大眼睛,小巧的鼻,微笑的唇。她同我是多么的相似,一眼看上去,我自己都覺得那活脫脫就是我自己,連眉心那顆黑痣的大小都一樣,位置也沒有變動。那一瞬間,我怔住了。
尹先生,你怎么會有我的照片?我的疑問脫口而出。
這不是你的照片。尹先生的回答沙啞而沉靜。
我的目光又回到照片上。照片上的女孩梳了兩只小辮子,穿的是一件很普通的白色襯衫。在我的記憶中,我一直是披肩長發,從來沒有梳過小辮子。而且我的衣服都是花花綠綠的,從來沒穿過這么老氣的襯衫。偶爾穿一回襯衫,我也不會將頸脖上的鈕扣扣死,而是任由它們敞開著,留一個V形的缺口,讓人看了多一些想象。
她是我的妻子。尹先生說。
接下來,都是他在說,我在聽。尹先生說——我倆是一個村子長大的,小時候我患有皮膚病,她每天陪我去村后的山溝里泡溫泉,后來我病好了,我們就結了婚。婚后我們辦了一個加工廠,事情慢慢多了,我沒有時間去泡溫泉了。后來就由她去溫泉,挑了水回來給我洗澡。挑水的時候,她還給我煮上幾個溫泉蛋。
我們有過一個女兒,如果她還活著,也有你這么大了。她患有心臟病,是不能生孩子的。我也沒打算要孩子。有一天她懷孕了,我堅持要做掉,但她不肯。她想要一個孩子。我依了她。但沒想到這個孩子要了她的命,孩子也沒能活下來。影子,她不是我的女兒,而是我的侄女。
后來,是一片沉默。沉默過后,尹先生說,青子,給我倒杯酒吧。尹先生,你不能喝了。我從他手上要過杯子,放回到桌子上。只管倒酒吧,我沒有醉。尹先生又端起了酒杯。我還是沒有給他倒酒。后來,他歪歪扭扭走過去,給自己倒了滿滿一杯酒。接著,他高高舉起了酒杯,對我說,青子,謝謝你陪我來看溫泉。然后他將滿杯的酒全部倒入了口中。
今天是她的忌日。放下杯子的時候尹先生說。
那天晚上的后半夜,我給張戈發了一條信息,告訴他要的東西我已經得手了。真的?張戈回了二個字,他好像有些不相信。如果你不想要,那我就扔了。別,我明天一早就到。他有些急了。記住你的承諾,咱也當一回土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記得那天離開時他在車里做的一個手勢,兩根指頭交叉疊成一個十字架,那是他答應給我的報酬。
后來,我如愿以償拿到了張戈承諾的十字架。不過我在將U盤交出去之前,將里面的資料做了一些修改,把他們換成了我在娛樂城時偶遇的客人,那些執意要將名字和聯系方式留給我的男人。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