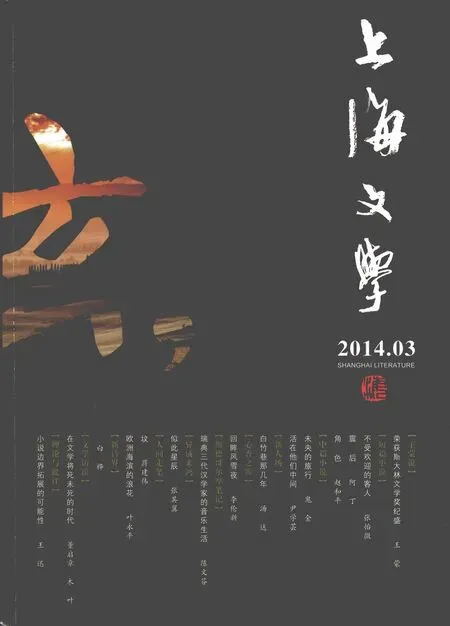似此星辰
張其翼
我是一名美國注冊臨床醫療社工,專為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病人服務。我每天花大約兩小時在路上,開車到不同的病人家做家訪。百分之九十的病人住在家中,由家屬提供日常照顧,由我們提供以止痛、緩解癥狀為原則的醫療服務。剩下的百分之十住在養老院、常規醫院或者善終醫院的病房里。我的雇主是一家善終醫院,而“我們”——是一個由醫生、護士、護工、社工,神職人員以及音樂治療師、按摩師、攝影師等組成的團隊。當然,還有管理層,被我們臨床人員稱為The Dark Side,月之暗面,負責約束我們的同情心和增加各種規程,以免遭病人起訴,使整個醫院破產。每個社工負責三十到四十名病人,職責繁多,一般而言,七成時間用來和病人或者家屬談話,俗稱心理咨詢及干預;剩下三成時間用來和政府或社會職能部門打交道,為病人申請福利或者服務。總之,社工的核心理念就是將人置于其環境中進行考量(assessment),幫助這個人成為更完善的人(empowerment)。所謂——“燃燒吧!流淌在你血管里的拉面!”——因為拉面本在血管之中,所需的只是使其燃燒。
快要下班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焦慮的陌生女人,她沒頭沒腦地說:“我弟弟想要結婚。你能不能幫幫我們?”我愣了愣,安慰了她一下,讓她從頭說起。原來,她弟弟是剛從綜合性醫院轉診來的病人,我還沒有從辦公室拿到病人的信息。轉診來的病人,預期壽命不會超過六個月。她弟弟的情況尤其糟糕,全面肝衰竭,腎衰竭,進食已經非常有限了。醫生的預計是一周到兩周。而這個焦慮的姐姐,本人也是個急診護士,她對情況的預計更加悲觀。她覺得她弟弟剩下的時間不會超過五天,可以說,隨時隨地可能撒手人寰。她弟弟有個女朋友,兩人同居四十多年,彼此忠誠,只是一直沒去辦手續。現在,他的愿望是,完成這個遲遲未走的程序。問題在于,他神志雖然清醒,卻已無法離開病榻,去婚姻登記處當面申請。除此之外,他還要再等至少三天,才能拿到婚姻證書。他等不起。如果他死在婚姻證簽發之前,那將成為他們夫妻畢生的遺憾。
于是一下子就變得像打仗一樣。我連夜寫了證明信,說明病人的病情,申請免去他的出場義務和三天的等待時間。第二天一早,我出現在病人家,讓他們將申請和證明立刻傳真給婚姻登記處。病人和我想像的有點不一樣,形銷骨立,已無力說太多的話,但思維仍然極其敏捷,還愛開自己玩笑。我問他,想不想要一個家庭婚禮。他驚訝地抬起頭,說,當然好,可是。我說,我來安排。我找了單位的牧師,為他們作見證。找了音樂治療師,為婚禮伴奏,還找了攝影師,拍攝婚禮過程,為他們制作DVD。同事們都非常支持,只是在兩天之內臨時找出時間聚在一起有點困難。不管怎樣,婚姻證明總算在次日就批了下來,一個小小的婚禮也在某個晚上整整齊齊地舉行了。病人最后還嘗了嘗烤肉。據說,他除了結婚,就是想再吃一點烤肉。
我當年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樣的:要成為一個方面的專家,最快的方法是去美國留學。因為美國據說比中國好,所以美國人也肯定死得比中國人更體面。至少,上海人大概很難死得體面(某些農村卻可以,比如湖北土家族,在人死后跳喪竟夜,名撒葉兒嗬,既神圣,又寬松)。在我父親去世的那所三甲醫院,每天都有四到八具尸體從留觀病房中拖出去。病床之間,堪堪容下一張躺椅。作為一個重癥病人,左邊的病友昨天死,右邊的病友今天死,對于自己的狀況,也就有了了解。陪床的家屬,先是痛哭,哭累了就吵,罵醫生,罵病人,直到病人在心煩意亂中離世,家屬又是一陣號啕。哭罵聲此起彼伏,晝夜不息。殘存的病人因為病痛,徹夜徹夜地睡不著,輾轉呻吟。家屬因為煩躁、憤怒和疲倦,也是徹夜難眠。醫生,護士,不是暴跳如雷,就是冷若冰霜。如此往復振蕩,信號放大,很快所有人都如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幻境中。
而對我來說,理想的目標是:病人更深刻地理解生與死,家屬在安慰中獲得新生能量,病患的痛苦得到緩解乃至消除,家庭經濟情況運轉良好,陳舊性破裂的情感關系在此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愈合,病人死時面容平靜,親人好友手挽手在牧師的帶領下為他禱告。醫護人員在此過程中得到中產階級典型的心理滿足。
現實是,一半的病人就像圣人,正直,自然,幽默,充滿了療愈的能量,堪稱人天師表,常常使我們感到,并不是我們在照顧他們,而是他們在照顧我們。另一半讓我們像消防隊一樣疲于滅火:或是病人的孫子把止痛的嗎啡偷去嗑了,賣了,一片奧施康定在黑市上可以賣到五十美元;或是暴躁的失語病人把結婚五十幾年的老婆打了,用拐杖勾住她的脖子要勒死她。這些都是社工的職責范圍,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如人猿般擺蕩在天堂和地獄之間,真是刺激。所以,在車里的時間是一個很好的過渡,到后來,我連音樂也不放,享受暫時的寧靜。
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系的凱博文教授有兩本著名的書,《疾痛的故事》和《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以病人本位的立場探討了疾病、疼痛和殘疾在精神和社會中的意義。在我們的日常各項評估中,最簡單也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疼嗎?有多疼?”病人可以打零分,也可以打十分,零分是一點不疼,十分當然是疼到極點。不管打幾分,都是病人自己說了算。有些人敏感,吃不住痛,有些人鎮定,尤其是一些經歷過大蕭條的老太太,嚴格的斯多葛主義者,對疼痛的耐受力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不管對疼痛的敏感度如何,只以病人自己的主觀反饋為準。雖然主觀,其準確性和有效性在目前的主流學術界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一般超過三,乃至于五,我們就不得不行動了,該下藥的下藥,還不行就用長效貼片劑、自助式注藥泵,直到病人感到舒適為止。
在忍痛方面,我懷疑華人是屬于斯多葛派的,都是生死場上打拚過來的,些許疼痛算得了什么。這大概和我們非常不信任嗎啡類藥物有關——在腫瘤醫院,打嗎啡等于放棄所有希望,誰想和民國時代那些形銷骨立的“大煙鬼”沆瀣一氣呢。我還是個實習生的時候,曾經造訪過一個年輕的胃癌病人。她才四十出頭,很安靜,眼睛大大,整個人瘦得盈盈一握。我低頭看了看病例,體重才八十磅,合七十二斤,而美國病人,最輕的也有她的兩倍。過輕的體重和特殊的體質(人種不同,藥物產生副作用也有差別,因體內的酶種類數量不同所致),帶來用藥上的隔閡和問題:醫生總是掌握不好止痛藥的劑量,太少了,沒有效果,太多了,又出現大量副作用,昏睡,惡心嘔吐,據說,比疼痛還要難忍。華人本就不太信任西人的止痛藥,如此一來,更是滿懷惡感。她丈夫告訴我,他們還沒有放棄治愈的希望,他們在佛羅里達有一個給開草藥的醫生,時不時會飛去接受治療。他說,她不能死,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他們是第一代移民,奮斗了半輩子,總算可以享福了,他絕對不允許她死。他常常反對她用止痛藥,認為嗎啡會讓那神奇的草藥失效,剝奪他們最后一絲治愈的可能。我心里并不以為然,我想的是,她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你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我無法忽略她二十四小時在病床上呻吟呼痛的樣子——她偷偷告訴我,她整夜整夜地無法入睡,躺在熟睡的丈夫身邊,這世上無一人她能夠求援。女人的一生,生育,哺乳,重病,瀕死,一次又一次,在極度寂靜之中的忍耐。可是我能向她那強勢的丈夫說什么呢?我送給他相關的書籍,委婉地向他進言,長期的疼痛會引發抑郁癥,就算他不愿意放棄最后的希望,讓他妻子如此忍受痛苦也只會讓她的情緒越來越消沉,徹底失去求生的意愿。我們的大多數談話都是在車里進行:我做完家訪,他主動開車送我去地鐵站,一路上,我絞盡腦汁地向他解釋疼痛對人的傷害,告訴他如何和家里的半大孩子溝通,告知他們關于母親的真正的病情。就像書里說的,汽車的車廂是專為敏感話題而設的完美環境:寧靜,與世隔絕,交談的雙方可以清晰地聽清楚彼此的談話,卻不用為目光要不要在對方臉上停留而感到尷尬。他究竟聽進去了多少,我打從心底里感到懷疑。很快,寒假來臨,被繁重的課業追趕了許久的我終于可以喘一口氣:當然,開學之前也暫時不用再去實習。我不是沒有想到過她,只覺得寒假很短,想要放縱,雖然死亡腳步匆匆,并不因為寒假而停止。開學后,我忐忑地打開病歷,發現她因為病情危重,無法攝入食物,在小年夜被送到醫院急診室,在丈夫的強烈要求下,醫院給她植入了胃造口管(G-Tube),當天夜里,她在醫院去世。我至今無法形容我看到病歷時的心情:最壞的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更糟糕的是,我有所預料,卻只是掩耳盜鈴地袖手旁觀。這個結果對我們單位來說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需要有人對此負責,至少作出解釋。但是并沒有人怪我:因為大家都覺得中國人大概是這樣的,而我也只是個實習生。但我知道,這是我職業上真正的起點,一個要永遠背負的污點。我去參加了她的葬禮,棺木中的她看上去陌生,另一個房間里,回放著她生前的照片,我在一群陌生人之間忽然淚如泉涌,無緣無故地哭了整整一個小時,那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她,極其美貌,極其溫柔,仿佛在對我說:“現在好了。”
以上是關于一個中國女人的疼痛的故事。硬幣的另一面,是許多美國病人對藥物的濫用。美國是一個藥物濫用的國度——當然,中國也是,抗生素方面。不過,美國的精神類和嗎啡類藥物濫用的問題也許更加嚴重。有些病人只是對疼痛的耐受力低,記得在綜合性醫院跟著醫生輪崗時,遇到過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胰腺癌晚期,曾經是大學的橄欖球運動員。他對疼痛的耐受力很低,所以早早就用上了自助式注藥泵,也就是說,他手里有一個按鈕,覺得疼可以按一下,額外的嗎啡溶液立即從靜脈流入,不用呼喚醫生或者護士。當然,按按鈕的頻率也有個限度,一般要等十分鐘才能按下一次。結果,他一個小時按了一百多次(好在大多數都無效,不然已經死了),所有醫務人員都嚇了一跳。我跑去問他,他笑嘻嘻地看著我說,“既然我已經得了這個病……哪怕一丁點痛,我都不想忍受。”他看上去仍然很強壯,和在酒吧里跟女孩子搭訕的大學生沒什么兩樣。作為一個社工,我理當教育他,警告他,像火燒屁股一樣開始自殺風險評估和藥物濫用評估,寫病歷,寫報告,一層一層往上報備,但我的心里有一個聲音在說:“好的,那你就不要忍受了吧。”總之,他那貌似玩世不恭的笑容,他的肌肉,他的病史……使我無法對他產生惡感。當然,還有一類病人,會拿自己的止痛藥去賣,和鄰居一起吸到迷幻,然后轉身問我們要更多、更多、更多……在佛羅里達州,對嗎啡類藥物的法規極度廢弛,許多醫生和病人沆瀣一氣,毫不負責地大開方便之門,以至于許多人在周末開車十幾個小時到南方,來一次說飛就飛的旅行。這個就扯遠了。
美國社會持槍率很高,所以,做社工的,第一要防止病人飲彈自盡,第二要防止被病人開槍殺害。好在,當醫療社工,遇到第二種病人的情況比較少。相比之下,兒童福利社工才是高危工種,常有被兒童家長槍殺的新聞。我們時不時會遇到有自殺想法的病人。不論醫療多發達,重病帶來的功能衰退終究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有些老頭極其倔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退伍之后,就一直住在自己親手造起來的磚頭房子里面,眼看著一天天衰弱下去,無法再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卻是打死也不愿意去養老院,更別提醫院,或向自己遠在外地的子女求助。而我們機構,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之外,并不提供二十四小時日常照料的服務。要雇人在家里照顧,那可貴了,每個月少則八九千美金,多則一兩萬美金,一般人都負擔不起。我們只好問老頭:“那你想怎么樣嘛?”老頭犟著脖子嚷嚷道:“把我的手槍拿來,馬上解決問題。”我只是上班,可不是拍西部片,一聽這話,只好坐下來做自殺評估和預防。畢竟,想到過自殺,和已經有了一個自殺的計劃,那是不一樣的。有了自殺的計劃,還要有自殺的手段。比如服藥死,要有藥;上吊死,要有繩子。最常見的是飲彈死,誰家沒有一兩把槍。一般而言,女性偏愛服藥,男性偏愛飲彈。白人男性的自殺率在所有群體里是最高的。老年人總體的自殺率雖然比年輕人低,自殺的成功率卻比年輕人高上幾倍。難道說這是生活積累起來的智慧?當我坐下來一本正經地和病人討論他已經到了自殺行動的哪一步時,真有種極度荒誕的感覺,似乎我在和他一起制定著自殺的計劃。有時候,我甚至不得不承認病人的想法不失其合理之處。在有著高度自尊心的病人看來,臥床不能自理的生活就像地獄一般,是對他/她人格的羞辱。有時候疾病的病程比醫生許諾的長上了好幾倍,病人等上帝等得極不耐煩,不知道這漫漫長路何時是個盡頭。沒有親屬的照料,垂死的生活的確毫無質量可言。病人如果有信仰,多少好些——想要自殺卻又不敢,怕上不了天堂,大不了拉上組里的牧師陪我一起開導病人。病人如果沒信仰,就有些麻煩。我只好鼓起三寸不爛之舌,提醒他們專注于“內觀”,而非外在機能的衰退。
還有一種,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情況。我偷偷創造了一個新詞,“可控式病理性自殺”。雖然美國的低保Medicaid可以抵付昂貴的養老院的費用,大多數老年人自由慣了,哪里受得了養老院的乏味和約束。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病人,我得不斷地勸說他們考慮搬去養老院住,因為住在家里已經變得很不安全,摔一跤就可能造成嚴重后果(骨折,乃至死亡),家人也已精疲力盡,無力再提供高強度的照顧服務。有很多次,病人迫于病情、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不得不氣鼓鼓地住進養老院。作為社工,我落著什么好了呢?每轉一個病人進養老院,起碼一周時間我要忙得腳不點地,選址,選院,申請補助,跟每個人解釋,跟養老院討論,跪舔,乃至吵架,以爭取某些特殊的要求。可往往是病人入院第二天,便送來逝世的噩耗。我聽到噩耗,又氣又恨,連續好幾天郁悶得像狗,反復思索是不是自己間接殺死了他們。我還恨他們一點面子也不給我,可能是存心以死來氣我的,仿佛狡黠地說:“我告訴過你吧,我住不了養老院。”在這行干得越久,我越覺得,也許病人并不懂得多少病理,但在預測甚至控制自己的死亡日期這件事情上,病人可比醫生要高超得多。好多都是說死就死。還有個九十多歲的老太太,病情之重,胃口之好,嗓門之大,脾氣之壞,令人嘆為觀止。她一天到晚嚷嚷“我不會死”,“我要好起來”,“給我滾出去”,轟得全體醫務人員頭暈腦脹。根據教條,她就是那種永遠處于“否認期”的壞病人。忽然有一天,她說:“到時候了。我該走了。”我差點以為自己出現了幻聽。當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第二天,她溘然長逝,面容平靜。我回想起來,覺得她真是有點搖滾精神。
去年冬天,本城大雪紛飛,路上全是冰和被撞扁的小車。我膽戰心驚,克服千難萬險開車去極偏遠的郊外探訪一個病人。他孑然一身,晚期肝癌,和一條退役的警犬相依為命。他的房子在一個小山坡上,我的后輪驅動根本開不上去,他只得開著他的紅色大卡車下來接我。讓一個走路都有些困難的重癥患者開車接我,我的人品瞬間降為負值。可他的境況更讓我覺得無解。住得最近的一個弟弟在五百英里之外的費城,偶爾來訪。妻子在二十年前去世,除此之外再無親人。齊胸高的退役警犬的攻擊性很強,經常在我們談話時撲上來,被他用電擊器擊倒,癱倒在地上。作為一個害怕所有小動物的人來說,我的命都快被嚇掉了半條。盡管如此,我還是硬著頭皮幫著解釋文件,填寫表格。這樣下去,所有的醫務人員都受不了了:做個家訪,還要冒著被撕碎的危險。護士和護工鬧得最兇,因為她們每周要去兩到三次,風險遠遠大于我。原則上,病人要是不能把寵物關好,我們就不能提供服務,可是這畢竟只在條例中成立。大家都覺得對這條狗的處理刻不容緩,可她已經太老了,又太兇,不服教化,沒有一個動物收容所有能力收容她。最好的辦法,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住進養老院,同時給她一針,讓她安樂死。這個病人也知道這是遲早的事:可是一提上具體日程,這個七十三歲的寡言的男人就開始泣不成聲。他并不太關心自己,他關心的是,如何才能盡可能長地保存這個忠誠地陪伴了他整整八年的伙伴的生命。她已是他唯一的情感依靠。所以,他絕不能去養老院。從他家出來,大雪已把我的車埋了一半。我愣愣地把車從雪里刨出來,又花了整整三個小時才從那地方有驚無險地回到高速路上。我們在會上反復討論,極其恐懼,又萬分同情,只得這樣不清不楚地拖了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和護士結伴前往,打電話沒人接,狗在院子里奔跑。我們只得打電話叫了警察,在雪里等了四十五分鐘,警察趕到,發現病人已經昏迷。狗隨即被安樂死,病人也在幾天后去世。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雪天,冷得人徹骨寒心。
我覺得自己并不是一個很好的醫療社工:我還不夠有膽量,向病人坦陳心意,或為他們爭取利益,我也不夠有奉獻精神,在雙休日里沉湎聲色,而非盡一切所能去鉆研業務。和國內的醫務工作者相比,我的工作量仍算合理。我只不過是在這條滔天的大河上隨波逐流。最近這兩天,我忽然意識到,我所熟悉的醫院的味道,其實并不是病的味道,而是消毒水的味道。就像大閘蟹的味道,實際上也不是蟹肉的味道,而是醋和姜絲的味道。不知道為什么,想通了這一點,我覺得自己好像活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