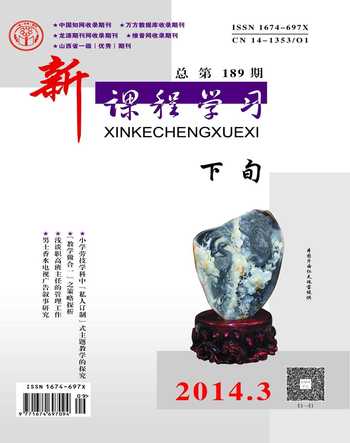論創作劇本的困難
蘇奕銘
一、當編劇是困難的,很多編劇總覺得沒有什么可寫。覺得現在的影片已經把所有的,可以寫的素材與故事情節都寫過了
經常有編劇感到沒有故事好寫,或者在一個故事上苦苦思索,最終卻發現不得要領。一個構思改不下去了,進入了死胡同,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我們這里先來談談怎樣著手構思,進入的途徑順利了,發展就會水到渠成。
在構思之前,需要先確定你準備創作一個什么模式的故事?可能很多編劇會感到棘手,故事的模式非常多樣,我怎么選擇呢?其實故事簡單來說只有兩種模式:一個人要達成某個目標或者遇到某事;兩個人形成了一種關系。你想一想,其實所有故事都可以納入這兩個模式之內。因為這兩種模式在以后的構思和創作上風格差異很大,所以首先在兩者中擇一是必要的。
在任何教材里都不會這樣來區分電影,但這是極為實用的一種方法。前一種模式是相當寬泛的,很多類型和水準差異巨大的作品都適用。
它可以這樣概括:他是誰?她要做什么?她為什么要這樣做?他遇到了什么?遇到的事情對他的目標構成了什么困難?他最終是否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作為一個基本思路,這樣可以大體勾勒出作品的情節線索。
編劇首先要會生活,很多素材都是從生活里反映出來的,有很多生活中的小事情能反映出我們內心深處的世界,只要你珍惜生活、體味生活,編劇就會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創作。
構思往往是從一個點上開始的,好的故事幾乎總能用一句話來概括。如:《一個都不能少》:一位農村小學的代課小老師千辛萬苦地尋找失學學生的故事;《保鏢》:一個白人保鏢和一個黑人女歌星的愛情經歷;《不需要愛情》:一個牛郎為了巨大的遺產接近一個富有的盲女,最后為愛死去。這三個故事的相同點,就在于故事的核心是兩個人關系的發展或者轉變,而轉變的過程決定了故事的發生地點:《一個都不能少》是發生在路上,《保鏢》和《不需要愛情》是發生在家里,如果我們有了地點(在這里其實也就是作品的敘述模式),人物就必須納入視線了。
人物的相識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會發現人物在相識之初,是構成某種對立的,這樣設計,我們就可以在以后的篇幅里用他們關系的轉變完成情節的填充。他們的關系將向哪個方向發展,決定了故事的走向和情節的設計。
中國人把戲劇概括為“起承轉合”,至此,我們實際已經得到了“起”和“合”,就是故事的開始和結局,并且我們有了地點和人物,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承”和“轉”了。我們要考慮怎樣讓整個故事轉變得合乎情理,并且具有激動人心的部分。而這些都還是故事的骨架,離層層“添肉”的工作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任何時候都不要急于付諸完成,一個良好的梗概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以下的過程完全可以變化程序,但是基本出發點我們是可以推測的:一個故事就像一個毛線球,我們只要仔細觀察,就可以找到線頭,那就是我們需要把握的位置。
我們想盡一切辦法,設計矛盾,就是為了讓故事發展下去!我們不能讓線索在某個地方不恰當地中斷,這意味著故事結束了;當然你不想讓故事在開始時就結束,你就必須讓故事延伸下去,不是跳躍著,而是勾連著、有層次地、一步步推導下去,水到渠成一樣自然,但處處滲透著編劇的匠心。
編劇在創作過程中,首先要知道寫什么,有了明確的目標,才有創作的動力。連自己要寫什么都不明確,一定寫不下去的。明確自己要寫什么以后,在心里要有創作的大概內容情節,最主要的矛盾沖突和關鍵事件要想好。因為這是牽連整個劇本創作的主干,他們是不能丟失的。之后就是要怎么將一個個故事順利地連在一起了,故事串聯過程中,情節要緊湊,內容要豐富,人物要生動。
二、每個編劇都有自己的特長,也都有自己的局限
人與人是不同的,每個人的長處也是不相同的。就像那些作家們,你是不可能期待金庸會寫出愛情小說,也不可能期待瓊瑤寫出武俠小說一樣。編劇也有自己的特長,就像“寧財神”創作喜劇,他是不會創作鄉村劇本的。創作喜劇是他的特長,也會是他的局限。
三、抓住一個好的題材,就等于抓住了一個成功的機會
好的題材是有限的,在大千世界里,值得去創作的題材有很多,就看你會不會發現。很多好的題材不是擺好了等著你去發現,也不要只限在自己的生活范圍內去開發創造,要多走多看多聽取,不是題材去找你,而是你要主動去挖掘題材。
好的題材要去創造,好的題材要去體會,好的題材要去發掘。其實在創作過程中又何嘗不是在創作成功。
現在的編劇有很多形式去改寫劇本,但是無論在改編小說、漫畫,還是自由創作,劇本中的大眾化、通俗化也有一個“度”。空洞、干癟的說教令人生厭,“寓教于樂”則可以使人們在觀賞愉悅中獲得健康、美好的教益。
盡管大眾要求通俗的劇作,但是通俗不等于媚俗,“迎合觀眾”“適應市場”往往一廂情愿,進口“大片”風風火火了一陣,人們在“大開眼界”之后便覺得那些以電影新技術賺取高票房收入的打打殺殺“不過如此”,而某些思想蒼白、內容貧乏、僅靠噱頭搞笑支撐的“泡沫劇”也已經敗壞了人們的胃口。觀眾呼喚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精神食糧,這一真誠的愿望理應得到藝術工作者的尊重和積極回應,弘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這是文藝工作者的基本職責,也是人民群眾對文藝作品這一特殊“商品”的正當要求。
(作者單位 松原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