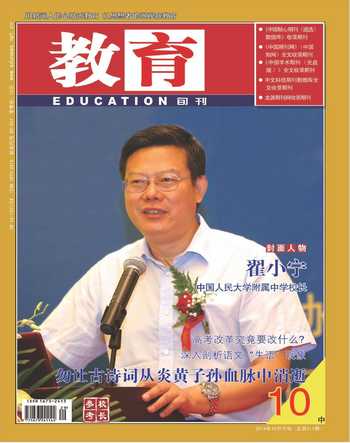《新華字典》:61年光陰,終返語文本色
自1953年初首印至今,《新華字典》發行過12個版本,這個小小的“穿著紅裙子的”字典在影響著數億中國人。教育部最新確定的國家免費提供教科書范疇,自2013年寒假開學起,我國將為全國農村地區中小學1至9年級在校生免費提供《新華字典》。
《新華字典》不能忘
時尚的帽子史無前例地戴在了“新華”姑娘頭上。人們發現,這個平常總是一臉嚴肅的女孩,居然能講出不少潮詞。她將“學歷門”的“門”解釋為“事件,多指負面的事件”。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她喜歡在電視里看“服裝秀”,偶爾會“曬工資”,也會關注“房奴”和“車奴”。
事實上,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字典,半個多世紀以來《新華字典》并不僅僅在語言上給人以指導,也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中國人。在1965年版和1971年版中,鵝被解釋為“一種家禽,比鴨子大,頸長,腳有蹼,雄的頭部有黃色突起”。后來,一名讀者寫信向編輯抱怨,由于不知道如何分辨鵝的性別,他在殺鵝前特意查了《新華字典》,于是將“頭部有黃色突起”的鵝殺掉。沒想到,這只倒霉的鵝居然腹中有卵。由此,編輯才發現,無論雌鵝、雄鵝,頭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鵝突起較大。這一錯誤在1979年版中得以修正。
一個很愛打扮的男配音演員稱:“作為一個語言工作者,你可以忘帶錢包,忘帶手機,忘帶護膚品……唯獨《新華字典》不能忘。”相似的故事也發生在已經過世的羅京身上,在26年的新聞聯播播音員生涯中,他從沒出過錯。他去世后,人們在他的辦公桌下找到一本已經被翻爛了的《新華字典》。
有媒體人發出這樣的感嘆:“無論從發行量、普及面、影響程度,還是讀者的忠誠度來看,它對中國人的意義都類似于圣經之于基督徒。”
“姑娘”芳心得不到
盡管這只是一本收錄了11000多字的小字典,可是修訂的工作卻絲毫不能馬虎。在詞典室前主任韓敬體的辦公桌上,第10版字典已經被用得卷了邊兒,由他負責修訂的那一部分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標注。這些學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斷地從“語法比較規范的報章雜志”上查找新詞,并時刻關注著最新的網絡用語。眼下,已經71歲的韓敬體像年輕人一樣熟悉“神馬”和“有木有”。但是學者們經討論后認為,這兩個詞其實都是年輕人為了“圖新鮮”而使用的錯別字,無助于增加語言的豐富性,所以眼下并不會被收入字典。
事實上,連一個字的新義項想要進入“新華”的世界里,都需要經過一段相當漫長的考察期。早在第10版出版前,程榮就注意到了“秀”作為“表演、展示”的新含義,但因為擔心這些流行詞不夠穩定,當時她并沒有貿然進行修改。直到8年后,“作秀”才算通過考察,正式進入《新華字典》。
但人們注意到,“曬”和“奴”等字的新義并沒有出現太久,卻已經登堂入室。人們甚至發現,就連常用的bye bye也真正走進了漢語世界,“拜拜”有了二聲讀音。“不管這個音譯詞合理不合理,但是它太常見了。”韓敬體笑著說,隨即又補充道,“畢竟,語言學家只是語言的記錄員和研究者,而不是語言的警察。”
扎著羊角辮、跳著忠字舞
學者們當然沒有忘記,在新中國最初的數十年里,這個名叫“新華”的姑娘曾被戴上過紅袖章,并且被賦予了“監察員”般的使命。
1953年10月,幾乎在新中國4歲生日的同時,“新華”家族的大姐在北京誕生。從這個時間節點向前推8年,“《新華字典》之父”、北京大學中文系原主任魏建功被國民政府的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派赴臺灣,推行國語。1948年他回到北京時,解放大軍包圍了北京城,魏建功找來周祖謨、金克木等語言學家,想要編纂一部字典。那時,中國還沒有一部白話字典。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圣陶找到魏建功,任命他主持編纂字典。這部字典從名字開始,就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或者也可以說是當時最美好的祝愿:“新華,新的中華啊。”
一個將近50歲的中年人,曾經使用過1953年版《新華字典》。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認為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是除中國外最強大的,因為在字典的各國首都、面積、人口一覽表中,社會主義國家高居前列,一長串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在榜單末尾無精打采地跟著。因此,當這個中年人被派到“排名倒數第三位的美帝國主義”考察時,他的腦袋亂了套。本來,根據字典,他應該看到一幅“在剝削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只有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的苦難圖景。
之所以又紅又專,與編纂方法也有一定關系。最初,魏建功等人從當時的報章雜志上勾詞,人工抄寫了30多萬張卡片,并從中選出一部分作為字典的詞條和例句,“那時候,人們就是這樣說話、寫文章,字典勾勒著一個時代”。
1971年,最新版《新華字典》出版了。據說當時的詞都要被劃分三六九等,“革命”是積極詞,“頹廢”是消極詞,而這部用紅色大字印著《毛主席語錄》的字典,必須摒棄一切消極詞。近2000條修改意見最后被匯總到周恩來總理的案頭,最終,根據周恩來“小改應急需”的指示,只有64處被改動。根據后來的媒體報道,全書引用46條《毛主席語錄》。
幾十年后,有人聽到這段故事評論說,歷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如1971年出生的“新華”——扎著羊角辮、跳著忠字舞、又紅又專。
“臉譜化”姑娘回歸人性
想要從這個“臉譜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卻沒有那么簡單了。
20世紀70年代人人都必須背誦的,為了“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經典理論,在1992年的字典上消失了。同年,“社”的詞條下出現了“社交”。當時間推移到1998年,人們在這里不再看到“仇恨”與“主義”。宗教不會被視為“虛幻的、歪曲的反映”,“利潤”也不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手段”了。
到了2004年,這個原來總有點“端著”的姑娘,已經可以大大方方地談論“性教育”和“禁毒”,她也在經歷“代溝”,關注著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2011年,新版字典中加入“和諧”一詞。一位參與修訂的人員稱,現在修訂小組中仍然有“專門負責折射條的同志”,遇到宗教、民族、政治等問題須報權威部門核準。但由于認為“和諧”只是“普通的語文意義上的詞語”,他們并沒有為此事特別呈報上級。
2011年7月8日,在社科院詞典室寬大的會議桌上,人們發現有一本第10版《新華字典》安靜地躺在那兒。在第121頁的“翻”字詞條中,“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這一例句,被用鉛筆淡淡地畫上了一道。
幾乎就在一個我們來不及注意的瞬間,在剛剛出生的小姑娘“新華”那里,這個伴隨著她整個家族的胎記,永遠地消失了。
(摘自2011年7月13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