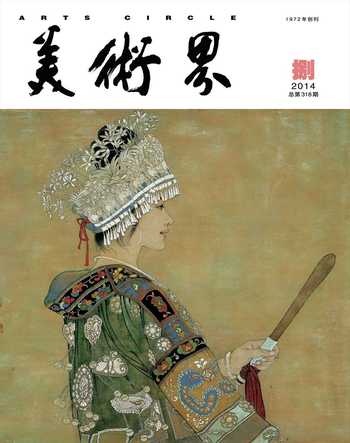唐宋繪畫視閾下的畫品與人品
【摘 要】唐朝以來繪畫多以統治者政治教化的工具而存在,繪畫創作的題材以及客體的“形”、“神”乃是畫師刻畫的重心,強調“畫品”。繼中晚唐,兩宋以來理學思想的不斷形成,仕人熱衷于修身、心性等內在品德的涵養,繪畫逐漸成為表達性情的工具,“人品”日益成為繪畫強調的重點。
【關鍵詞】人品;畫品;政治教化;性情涵養
中國畫獨特的品評方式,根植于東方獨具特色的肥沃土壤,而傳統思想的不斷衍變、成熟,也帶動著中國畫品評方式的變異。
一
唐朝雖然實行三教并融的思想政策,但是統治者(尤其是唐太宗)尤為重視利用儒學作為治國安邦一劑良藥。唐太宗曾詔令孔穎達等大儒撰寫《五經義疏》,解決了當時“儒學多門,章句繁雜”、“文字多訛謬”的弊端。永徽四年,《五經正義》頒布天下,為科舉取士劃定了教科書,也成了時人思想行為的規范。唐朝對外實行開拓疆域,所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其建功立業之豪情滿懷,社會中普遍彌漫著一種為國建功立業的英雄主義氛圍。在“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①積極入世的社會心態下,唐朝出現“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繁榮富庶局面。
在唐朝統治者有效的引導利用之下,繪畫的政教功能不斷被開拓。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講繪畫“與六籍同功”、“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綱紀”。繪畫理論家裴孝源在《貞觀公私畫錄》中講“其于忠臣孝子,賢愚美惡,莫不圖之屋壁,以訓將來。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跡,默匠儀形” 。②北宋時期的黃伯思在其《東觀余論》中記載唐朝大畫家吳道子,作畫《地獄變相圖》“視今寺剎所圖殊不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眾矣。”③可見一直以來繪畫自身的美學價值并未被認知,乃是作為一種政教工具而存在。
對于繪畫的政教要求之下,繪畫作品的成功與否更多的體現在繪畫的主題,以及繪畫客體的形象與神韻的傳達。無論是肖像寫真、歷史紀實的貴族人物畫,還是勸誡意義的佛道人物畫,都不僅要求表現對象嚴謹的寫實,還需通過“神”的傳達,以達到歌功頌德、美化現實、勸誡教化的功能。初唐畫家閻立本,其作品《步輦圖》生動地記錄了唐太宗坐步輦接見來朝使者祿東贊的情景。畫家延續著“以形寫神”的表現方式,并沒有滿足于表現每個人物在場面中的動作與服飾、反映漢藏兩組的友好情誼上。他更加注重人物的細致刻畫與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唐太宗的威嚴自若、祿東贊的敬畏之情等惟妙惟肖。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記載:郭汾陽胥趙縱侍郎令韓幹與周昉為其畫像,后問趙夫人何者為似,趙夫人云“二者皆似,后者為佳。蓋前畫者空的趙郎狀貌,后畫者兼得趙郎性情笑顏之姿爾” 。④足見,此時人們對于“形”、“神”的追求。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對于謝赫的“六法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傳移模寫,乃畫家末事”、“至于位置經營,則畫之總要”。“不再認為‘傳移模寫是評論繪畫的重要準則,而認為繪畫的構思與構圖才是關系作品全局的關鍵”。⑤繪畫臨摹與創作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之所以認為創作地位更高,無疑是因為繪畫主題的重要作用。至于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所講“以能畫定其品格,不計其冠冕賢愚”的論斷,所謂的“能畫”無疑即是作品之構思與構圖,以及“形”與“神”的傳達。畫壇對于創作主體的忽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畫師這一職業的社會地位。閻立本曾告誡兒子“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也造成了此時畫師“見用而不重”的地位。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還首次提到了“格外有不拘常法”的逸品,在崇精工、尚色彩、重格法的唐朝被列為“神、妙、能”三品之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
唐朝中晚期,在韓愈、柳宗元為首有志之士的帶動下,儒學開始向著修身、內向型的方向發生轉變,為宋代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北宋伊始,統治者采取兼容并蓄和“興文教,崇尚儒術”的國策,倡導讀經書,興辦學校,擴大了科舉取士的比例,儒學再度繁榮。“宋學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在傳統儒學的基礎之上,向著哲學思辨與探討宇宙生成的方向發展。重內省悟性,以解萬物人生。在理學中體現的典型而充分”。⑥理學強調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宋儒將《大學》的基本思想概括為“三綱領”、“八條目”。格物致知是達到修身目的的重要方式。“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⑦通過不斷地格物窮理,即可以達到心性覺悟的豁然狀態,其目的就是培養、接近圣人的人格理想。“萬物靜觀皆自得”,二程講:“人問其學,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⑧由此在注重修身的理學思想下,宋代形成了不同于唐朝注重仕功、治國、平天下的外向型進取的思維方式,把建功立業的外在追求內化為內在性情的涵養。
繪畫創作要師法造化研習、了解客體,更為關鍵的是主體內在心胸的轉化,主體在繪畫創作中的作用開始受到關注。“初,畢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見驚嘆之,異其唯用凸毫,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⑨《歷代名畫記》作為晚唐時期的繪畫理論著作,最能代表時代的美學思想。他除了將“位置經營”認為是畫之總要以外,還進一步將氣韻提到更高的位置,他講“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期間矣” 。張彥遠一改“以形寫神”為“以氣韻求其畫,形似自得于其間”,貌似簡單的一改,實則開啟了繪畫主體地位的攀升。北宋時期《林泉高致》也有相似的觀點“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飽游飫看,歷歷羅列于胸中”。《圖畫見聞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地表達了對于繪畫主體的重視“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可見繪畫創作中不再一味要求繪畫的主題,以及客體形、神的細致刻畫,主體的人品修養開始受到重視,繪畫創作發生了由重客體向重主體的轉變。
兩宋以來,隨著理學思想的不斷形成,畫家人品修養逐漸受到重視,繪畫主體的地位逐漸提高。一方面畫師為了自身地位的提高,開始熱衷于修習儒家各類經典文集;另一方面繪畫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抒發性情的工具。李成在兩宋畫壇的地位毋庸置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來自于較高的人品。《圖畫見聞志》記載李成“博通經史”、“世業儒,甚為名家所推”,李公麟是宋代的繪畫大家,同時也是畫壇巨儒,他曾講 “作畫贈人往往薄著勸戒于其間”,又有“吾為畫,如騷人賦詩,吟詠性情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側面反映了繪畫不僅不再牢牢地依附于政治教化,而開始成為個人抒發性情涵養的載體。南宋以來“比德”之風的盛行,使畫家人品成為繪畫表現的主題。理學影響下畫家將各類繪畫的題材比作成人物的尊卑貴賤的象征。《宣和畫譜》記載“繪事之妙,……與詩人相表里焉。……鶴之軒昂,鷹之擊博,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仲仁《華光梅譜》“梅有高下尊卑之別,有大小貴賤之辨”。⑩宋人喜畫竹,文同在南宋畫竹最負盛名,其筆下的竹子正是他的化身:“群居不倚,獨立不懼”;“節勁逾凡木”。畫家熱衷于通過剔發花鳥中的道德內涵,并以此反映個人的道德品格,由此出現了帶有東方特色的經典表現題材,比如大受文人喜好的“四君子”題材。
唐宋是中國繪畫發展成熟的關鍵歷史時期,同樣也是儒學成功轉型,逐漸形成在后世封建社會位居主導的理學思想。畫學思想與哲學思想的衍變雖沒有必然絕對的因果聯系,但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影響的文人士大夫對于繪畫的參與,形成了仕人亦畫亦儒的傳統。如此一來,使儒學的轉型與“人品”、“畫品”地位的轉變變得息息相關。
注釋:
①全唐文·請崇國學疏·六四五卷,載劉國忠&黃振平.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隋唐至清卷.[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②③④⑨⑩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
⑤金維諾.中國美術·魏晉至隋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⑥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⑦⑧朱熹,呂祖廉.近思錄.[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
【曹國橋 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