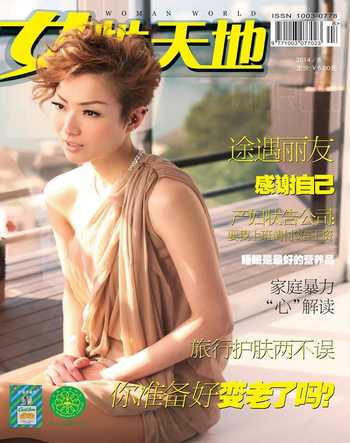美女教授顏寧:科研是最美的童話
藻靈
癌細胞一直令人聞之膽寒。多年以來,如何打敗癌細胞、挽救癌癥病人的生命一直是困擾醫學界的一個難題。而在不久前,清華大學一支研究團隊自豪地宣布了他們最新科研成果—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1的晶體結構,初步揭示了葡萄糖進入細胞內的原理及相關疾病的致病機理,并且依據這個研究成果寫成的論文還被《自然》雜志發表了,這意味著這項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與肯定。
這意味著人類有望治愈糖尿病,“餓死”癌細胞。這個成果震驚了學術界,被譽為國際學術領域評價為“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科研成就。而更讓人驚訝的是,樹立這個“里程碑”的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經驗豐富的老專家,而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輕人,帶隊的導師是一名35歲的青年教授,名叫顏寧。
“無論以哪個標準衡量,顏寧博士已位居世界最優秀的年輕結構生物學家之列。甚至可以預言:未來5年到10年,她將是杰出青年女性科學家的榜樣。”這是國際評估小組對顏寧的評價。在許多人心中對科學家的印象都是:刻板、嚴肅,但顏寧又一次顛覆了人們的印象,她天性浪漫,愛笑愛鬧,雖然已過而立之年,但依然是個愛做夢的女子,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
水木清華里的絢麗青春
顏寧1977年在山東萊蕪出生,6歲前的童年在這里度過。童年的顏寧是個十足的瘋丫頭,經常上樹摘果、下河摸蝦。那時她和鄰居家的老奶奶關系很好,時常跑到老奶奶家里去蹭吃蹭喝,她最喜歡的是老奶奶做的煎餅和灌腸。后來,顏寧隨父母搬到了北京,還時常想念老家那位慈祥的奶奶和她做的美食。當有一年她隨父母回鄉探親,這位老奶奶竟然已經患癌去世的消息。老人的兒女哭著告訴顏寧,母親被確診時已經是癌癥晚期,很快便離開了人世。走的時候肺臟上已經布滿了癌細胞,從那時起,顏寧恨透了肆虐的癌細胞。
然而上學以后,從小學到高中,顏寧卻變成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好孩子,十分自律,成績也極為優異,沒有人知道顏寧這樣的轉變是為何。不過顏寧又不是人們口中嘲諷的書呆子,在課余,顏寧又變成了一個富有浪漫情懷的女孩,喜歡唐詩宋詞,愛讀散文小說,文科成績一直在年級里霸占著第一的位子,她的目標是北大中文系。
懷著對文學的一腔單純熱情,顏寧在高中分班時選擇了文科班,但班主任老師卻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將她硬勸回了理科班。高考填志愿時,父母非常希望顏寧學醫,這又和顏寧的心愿完全相反,因為顏寧喜歡動物,不愿意解剖小動物,但又不忍拂逆父母的意思,于是便選擇了自己喜歡且較為前沿的生物科學與技術專業。她告訴父母:“21世紀是生命科學時代,而且生物學跟醫學也很相近,以后我的研究成果沒準能為醫學界提供幫助呢。”顏寧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認可。1996年,她如愿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
進入高手云集的清華后,顏寧感覺到壓力如一座大山轟然壓下,尤其是第一個學期,她幾乎每晚都會從考試不及格被勸退的噩夢中驚醒。就這樣,顏寧戰戰兢兢地過了一個學期,在期末考試的時候,她特別緊張,尤其是考高數,她腦子里一片空白,連最基本的公式都忘了。最后成績出來了,顏寧看著67分的成績,卻忽然長舒了一口氣—自己發揮得那么糟糕都能及格,看來清華沒那么恐怖。
丟掉壓力后,顏寧在學業中感到了一絲自如,在學習之余開始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大二那年,她不僅當上了學生會主席,還參與了許多校外活動,跳國標、玩乒乓、加入了學校的攝影和游泳小組,她的大學生活多姿多彩。
大三那年,顏寧被分子生物物理與結構生物學家饒子和選入了自己的實驗室。從前她一直覺得做實驗很枯燥,可是在饒子和老師的指導下,她漸漸愛上了做實驗的過程,在擺弄燒杯試管顯微鏡的過程中體驗到了無限樂趣。“一面滿懷期待地等待未知的實驗結果,一面跟實驗室的師哥師姐們侃大山其實特有趣,而且看到自己一次比一次更有進步就會特有幸福感。”顏寧這樣描述做實驗時的感受。
大四伊始,顏寧獲得了諾和諾德中國制藥公司的獎學金,同時也贏得了進入該公司做畢業設計的機會。因為表現出眾,顏寧在尚未畢業時就收到了這家公司的就業邀請函,對方開出了優厚的薪水,但顏寧卻婉拒了對方的好意,她說:“我了解自己,我喜歡做實驗時的專注,但肯定受不了公司里朝九晚五的生活。因為我喜歡自由的人生。”
普林斯頓邂逅夢想
顏寧決定赴美留學,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臨近畢業當大家都在為申請學校你爭我奪的時候,顏寧每天不是泡在實驗室就是去圖書館,遲遲沒有出手。不少同學在私下議論她的留學計劃恐怕要泡湯了。而在這時候,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助理教授施一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那天顏寧因為生病沒有參加。舍友聽了報告回來,對顏寧隨口說了這么一句:“普林斯頓是所很好的大學,施一公教授超牛。”沒想到這句話竟讓顏寧竟對普林斯頓大學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宿命感,心中突然有了一種“非他不報”的感覺。
于是顏寧便用英文給施一公教授寫了封信,在信里坦白自己的想法:“我覺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已達到貴校的要求,我希望把時間花在更有價值的地方。但申請出國太浪費時間和金錢了,如果普林斯頓大學錄取我,我就不用再花精力申請別的學校……”
這封很“拽”的來信讓施一公特別意外,他從未遇到過這么自信的學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親自面試了顏寧,而顏寧的優異在面試時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就這樣,她成了普林斯頓大學錄取的首位不按規矩出牌的學生。
2000年8月,顏寧抵達普林斯頓大學。這所大學也給了她大大的驚喜—建筑古樸,風景如畫,尤其是顏寧居住的研究生院宛如城堡,四面哥特式建筑環繞中間的天井,周圍是雪松和綠地,夜晚全是螢火蟲飛舞。顏寧就像走進魔法學校的哈利·波特一般,一下子闖入了一個如夢如幻的童話世界。
然而童話世界的學習壓力比起清華來更加巨大,顏寧絲毫不敢懈怠,尤其是在得知自己是學校招收的首屆中國學生,自己的表現將影響到該校日后對中國學生的錄取比例時,她更是緊張萬分。有一段時間她每天只睡六小時,每晚都是讀著論文入睡的。但這個過程對顏寧來說并不痛苦,因為普林斯頓的授課教師多是經驗豐富的老教授,經典論文甚至課本里的很多東西本就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像講故事那樣繪聲繪色地教給學生,這讓顏寧很快進入了狀態,覺得生物學越來越好玩。而醉心科研、簡單執著的導師施一公也帶給了顏寧許多感動,她暗暗下定決心,像導師那樣簡單而專注地對待自己的事業和手中的科研項目。
在施一公的帶領下,顏寧開始研究起腫瘤發生和細胞凋亡的分子調控機制來,她享受克服挑戰帶來的成就感,喜歡攻克課題的酸甜苦辣,沉醉在做實驗的快樂中。
回歸故土繼續追夢
2004年底,顏寧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正在她準備繼續深造的時候,她所在的實驗室決定研究膜蛋白。這是學術界一個公認的難題,多數研究者輕易不肯涉足,但這個命題卻對顏寧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她明白這項研究背后的意義—如果真的能做出成果,人類就在攻克癌癥的道路上往前跨了一大步。顏寧的腦海中突然出現了兒時鄰居的老奶奶的音容笑貌……她決定放棄讀博士后的機會,加入了新的實驗小組。
一年后,顏寧帶領師弟師妹做出了第一個膜蛋白結構模型,也為自己攢足了在美國安身立命的資本。然而,她的道路卻在一次回北京探親的時候發生了改變。顏寧回母校清華,偶然遇見了大學時的系主任。系主任詢問了顏寧的科研成就,然后感嘆說:“要是你能回來任教就好了,現在咱們國家急需你這樣有想法有創建的年輕人。” 聽了這句話,一種責任感從顏寧的心中迸發出來,忽然覺得自己應當用所學為祖國和母校做些什么。于是她做出了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決定:回國任教。她欣然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回到了祖國。
回國之后,顏寧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研究工作中,先后取得了一系列先進成果,還在世界頂級學術刊物發表了四篇論文。在通宵達旦的研究中,她偶爾覺得身體大不如前,回想起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時,常常接連四天不眠不休做實驗也感覺不到累,而回清華后,有時熬上兩天夜,身體便有吃不消的感覺。
這讓她感覺到了年齡帶來的緊迫感,也意識到自己的黃金時期也許只有幾年,因此顏寧更加專注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并開始抓緊培養帶的研究生,恨不得把一天當成兩天用。
顏寧是院系中最年輕的導師,也是最沒有架子的一位,她會在沒有任務的晚上呼朋喚友出去K歌吃飯,跟自己的學生一起玩《三國殺》,追《來自星星的你》,此外她還想盡辦法在經費允許范圍內給學生最多的補貼,為的就是他們能安心做科研。遇見學生實驗沒做好,沮喪失落的時候,顏寧又會變身知心姐姐,耐心聽學生訴苦,在顏寧的鼓勵下,學生們做起實驗來又恢復到了熱情飽滿的狀態,在學術會議上表現得極為積極,以致于與會的外國專家都好奇:“中國學生怎么這么活躍呢?”
在顏寧的帶領下,其團隊勇于進取,屢獲佳績,并于2014年6月5日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人類有望“餓死”癌細胞的研究成果,鼓舞了許多患者和研究者。而顏寧,也在“玩”科學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年輕,同事和學生們都說70后的她有著80后的外表和90后的心。而這位率性女科學家的夢想就是:一輩子扎根于生物學領域,在與科學共舞的過程中收獲更多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