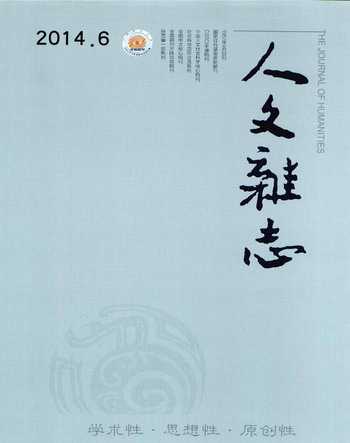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的接受
付佳
內容提要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的接受史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即產生初期詩壇主流的唱和認同,自北宋王回起至南宋范沖等人達到高潮的政治道德層面的曲解和否定,以及在南宋批判主流下部分評家仍堅持從詩學藝術角度對此二詩表示認可。接受主流從認同到否定的嬗變根由,一方面是兩宋之交尤其是南宋初年,官方出于政治目的對王安石其人及新法的政治否定和詆毀,另一方面則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理學與新學彼此消長過程中在學術、政治地位上的激烈爭斗。故宋代對《明妃曲》的接受史突出地反映了詩歌與政治、學術的緊密聯系甚至混淆對于詩歌接受過程深刻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王安石《明妃曲》宋代認同曲解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6-0065-07
王安石作為宋代文壇大家,其詩名作既多,影響亦大,流澤復遠。不過在其諸作之中,若論聚訟之多,為世人所矚目者,則莫過于《明妃曲》二首。從宋代至晚清,關于王安石《明妃曲》之欣賞與爭論、稱揚與非議,源源不絕。這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歷代詠昭君題材本身自成體系的魅力,以及王安石《明妃曲》之思想意旨、藝術特色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與王安石兼為政治家、北宋中期變法領袖等特殊身份有密切關系。綜合這些因素,今之研究者對于王安石《明妃曲》的命意造語之藝術賞析,特別是對于詩旨的辨析和澡雪,論之較多,其中的代表有鄧廣銘先生《為王安石的〈明妃曲〉辯誣》、漆俠先生《王安石的〈明妃曲〉》鄧文載于《文學遺產》1996年第3期;漆文載于《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第67-73頁。等文。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自有其本意,此固不可不查。但在這之外,歷來對此二詩之關注、唱和、批判及爭論,更使我們注意到,對王安石《明妃曲》二詩之接受,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跳脫于歧見層出的詩意辨正之外,加以整理和探討的大問題。對此,前人雖偶有涉及,然而卻一直有欠系統,更少專門而細致的研究。事實上,如能以客觀的視角,對王安石《明妃曲》的接受史加以探討,可以從中解讀出更多饒有深意的與文學、政治、學術、文化等相互關聯的問題。在整理和分析中,我們也發現,后代對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探究和爭議,其源頭實在二詩所產生的宋代,元明以降對二詩之主要評價和辨析,大體上不出宋人范疇。故而我們將探討的范圍限定于宋代,將后世爭論不休的關于《明妃曲》的問題,回歸其源頭加以集中討論。
一、唱和之盛與翻案出新:《明妃曲》
最初的接受從晉代石崇作《王昭君》詩開始,王昭君這個歷史人物便作為突出的詠史懷古題材為歷代詩人爭相取用,其中不乏名作。時至宋代,詠昭君詩更多不勝記。但在所有該題材的詩中,卻無一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那樣備受關注,且毀譽參半、飽受爭議。關于此二首詩的創作年代,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將之系于北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2頁。基本得到了普遍認可。王安石時任三司度支判官,自慶歷二年(1042年)登第入仕起,已有近二十年的各地仕宦經歷,政績顯達,下距宋神宗熙寧年間推行新法,尚有十來年,其時他與司馬光等人尚是好友。從這些背景來看,《明妃曲》二首在當時不過是一位政績突出且在文壇有一定影響的官員對古題標新立異的翻案之作。其特點正在于措辭立意另辟蹊徑,不落前人窠臼。茲先錄二詩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一)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于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其二)
二詩之本旨雖在翻案,但無論是詩中所闡發的人生思考的深度,深摯哀怨的情感興寄的濃度,還是側面烘托、散文化句式等技巧所達到的藝術成就的高度,均堪稱卓絕。故一經問世,便如激浪之石,震動了當時文壇,歐陽修、司馬光、梅堯臣、劉敞、曾鞏等紛紛唱和。從這種唱和之作甚眾,且參與者又都為文壇主將的情況來看,應該說《明妃曲》得到了當時主流的認同,并引發了一時詩人名士的極大共鳴,催動了他們對于這一傳統題材再作深入發掘和翻案的熱情。究其原因,則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代表了宋人以深刻思考和另出新意見長的詩歌創作理路與實踐,特別是在這種幾乎為前代寫盡的題材上,能取得明顯的創獲,無疑給當時的詩人極大的啟示:昭君一題尚有可開拓之余蘊,還可不斷發覆出新。這種藝術與思想兼具的創新,正是當時文人對于王氏《明妃曲》所關注的焦點,而主流文壇以和詩的方式所表達的肯定和認同,也成為宋代對《明妃曲》接受的起點。
2014年第6期
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的接受
總體來說,這些和作都延續了王安石《明妃曲》翻案的脈絡,將大量對歷史、政治、人生、倫理的思考融入其中。如歐陽修《再和明妃曲》即為其中的代表,此詩五七言散體句式之多樣,氣格之高妙,藝術之精工,融敘事、抒情、議論為一體的特色,亦皆出類拔萃。而詩中“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兩句立論,更值得注意。“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似與王安石《明妃曲》“當時枉殺毛延壽”機杼同出,不過王安石是從昭君之美本無法描摹之客觀狀況而言,重于表達對于個人得失的思考,而歐陽修則站在國家大局的立場上,更偏重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聯系北宋外患之背景,不可謂無所指。故就昭君題材而言,這種從政治視角做出的深刻的理性判斷,于王安石《明妃曲》之外又有創造。歐陽修對此詩頗為自得,他曾自詡《再和明妃曲》一詩為生平詩作之冠,認為“太白不能為,惟子美能之”。葉夢得:《石林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第424頁。以李白、杜甫為比照對象,甚至以為凌轢李杜,似有自矜之嫌,但若從其詩對前人尤其是唐詩的突破而言,歐陽修之自負也不無道理。唐詩以意興主情、典麗高華為勝,唐代昭君詩如李杜之作品,多借昭君之哀怨抒己之失意、悵惘和憤懣。而宋人則善于從理性的角度,從日常生活的細節,從社會人生的高度,深入事件的核心和人物的內心,從而能夠從司空見慣的現象和習以為常的定論中,發掘出新意,以見識超卓、透辟深邃的思辨精神為詩作之內核。歐陽修之《再和明妃曲》既是宋詩風格的典型代表,其自高標置也是可以理解的。
歐陽修作為文壇盟主對其和作的重視和自賞,以及和詩本身確實具有的價值,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了王安石《明妃曲》原作在當時的影響。歐陽修能作出這樣超脫俗見的優秀詩作,首先也是受到了王安石《明妃曲》的激發。朱杰人先生曾指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用其嫻熟的藝術手法與深刻的思想內容體現了宋初詩文革新理論所追求的藝術境界,在宋仁宗朝詩文革新運動中,成為宋詩獨特風格最后完成的關鍵,而它所引起的轟動效應正是宋代詩人們對經過長期斗爭、實踐、創造獲得的一種新的詩風與詩體的認同之舉。朱杰人:《宋代的昭君詩》,《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此論或可商榷,然其對于這次唱和的性質的認識,當是準確的。也就是說,王安石《明妃曲》之制,正是在適當的時機,為其時方盛的詩文革新運動提供了典范之例,自然就會引起主流詩人巨大的反響,形成同題創作的聲勢,推動宋詩風格的真正形成。這次唱和活動影響之大,以至于不僅有王安石、歐陽修這樣的宋詩大家,能夠在其詩中以宋詩特有的理性、議論見長的筆調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深入思考,就連本不以詩聞名的司馬光、曾鞏等人也在他們的昭君詩中甚有發揮。雖然各人詩作主旨之重點不同,如王安石重個人得失感受,歐陽修重政治層面的國家安危,司馬光加入了史學家對君主不辨是非的深層思考,曾鞏重讒言之可畏和人性之善妒等等。但他們以昭君為題唱和的核心,都在于跳脫歷來的傳統見解,各抒己見,力圖翻新,使原本老套的詩歌主題進一步深化。
雖然無人附和王安石的“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但也沒有對王安石這兩句后來引起極大爭議的詩句,給予任何的指責和駁斥。與后來對《明妃曲》二詩的聚訟紛紜相比,在其甫創之初,其接受基本限定在單純的文學范疇,不涉政治,不存爭議。而這其實也反映了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本意并不復雜,或有隱曲抒情,但仍以翻案出新的思想和藝術追求為主,也容易被時人所理解和認同。當然,更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王安石,還遠沒有他當政之后的復雜的政治、學術背景。
二、從王回到范沖:從夷夏之辯到政治詆毀
王安石《明妃曲》最初的接受是從主流詩壇的唱和開始的,然在諸史料文獻中并未見到參與唱和的詩人們對《明妃曲》有直接的評論。文獻記載中對《明妃曲》二首的直接評價,始自黃庭堅。南宋李壁《王荊公詩注》卷六在“人生失意無南北”句下注云:
山谷跋公此詩云:荊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并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荊公此詩,庭堅以為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檡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9頁。
這則材料體現出一種不同于主流詩壇觀點的過渡性的接受意見,值得我們留意。黃庭堅對此詩之立意主旨和藝術水準十分贊賞,這與歐陽修等人從文學角度加以肯定的態度一致,并無可議,值得的關注的重點在于王回(深父)對末句詩意的否定。他從儒家夷夏之辯的民族觀念和忠孝觀念出發,特為挑出“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加以否定性評價。并以孔子之語為據,認為華夏之“南”與夷狄之“北”不可混淆并稱。這是在《明妃曲》的接受史中,載于文獻的第一次爭議。有意思的是,王回為王安石之至交好友,于此卻因拘于細末文字、夷夏之別而誤讀詩意,反倒是尚且年少的黃庭堅為王安石之本意辯解。黃庭堅據其對儒家夷夏本旨的深刻理解,不以王詩末句為失,使得王回深為嘆服而贊曰“持論知古血脈”。王安石《明妃曲》接受史上的第一次爭議,以黃庭堅說服王回而告終。
王回雖然被說服了,然而在諸公唱和之時對王安石《明妃曲》的文學詩學本意的接受和理解,卻也因此開始出現了誤讀的陰影。黃庭堅評王回的解讀為“德言”、“極忠孝”,可謂一語中的,饒有深意。盡管作為好友的王回并無惡意中傷的意圖,然而從其中的觀念分歧看,雖未涉及政治、道德之批判,但已經有了忠孝之觀、夷夏之辯這樣的超出詩意本身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據《黃庭堅年譜新編》的考證,黃庭堅與王回關于《明妃曲》之辯,系于仁宗嘉佑四年左右。而前述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亦將《明妃曲》二首系于嘉佑四年,這也就說明,在王安石《明妃曲》問世之初,已有不同的意見出現了。
王回對王安石《明妃曲》前篇“人生失意無南北”的解讀,雖然只是詩歌接受史中不可避免的誤讀,然而他這種謹守儒家忠孝、夷夏觀念的立場,摘句批評《明妃曲》詩意的方法,卻代表了北宋主流詩壇之外接受和解讀《明妃曲》的新途徑。王回此評對之后出現的王安石《明妃曲》的進一步誤讀是否有直接影響,并無文獻可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當時非主流的解讀和接受方式,到了兩宋之交,得到了爆發性的充實和豐富,以至于這兩首曾經以思想和藝術之立新而成為宋詩代表的詩歌,在道德和政治的維度上,又一次成為了世人矚目的焦點,并直接影響了后世對此二詩的解讀和接受。這時批判和誤讀的重心,從第一首的“人生失意無南北”轉移到了第二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一句。其作為眾人口誅筆伐的對象,見諸文獻史料者甚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材料,當屬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載紹興四年(1134年)范沖與高宗論及王安石的一段對話: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入見……上又論王安石之奸,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沖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后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于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足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華書局,1956年,第1289-1290頁。
此論《王荊公詩注》“人生樂在相知心”句下亦載。《王荊文公詩李壁注》,第431-432頁。縱觀歷代對《明妃曲》的各種非議,范沖此論對王安石《明妃曲》的批判、貶低甚至攻擊,可謂最甚。范沖對《明妃曲》的解讀,是在王回的撇開詩歌本身思想藝術的解讀方式基礎上,將被政治立場所過濾的作家人格與詩作中個別語句牽強附會、斷章取義的肆意曲解。正如鄧廣銘先生指出,“漢恩自淺胡自深”一句,絕不應如范沖所解為昭君慶幸胡君對己的恩情自是遠深于漢帝,“自”字應是解作“盡管”。詩中的胡恩之深與相知之心,本是兩碼事,原意是說無論恩情深淺,胡地習俗語言之不通,無法相知相印,也是令人悲傷的,重點本在“人生樂在相知心”之嘆,其所表達的昭君對出塞入胡之悲怨,結合開篇“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與下句“可憐青家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是十分清楚的。但范沖卻摘句孤立地評鑒并一再推演,肆意臆測文外之旨,扭曲詩人之意,實屬別有用心。范沖之父范祖禹為司馬光之嫡系,王安石新黨之宿敵,在北宋政壇與王安石積怨已久。范沖既步武其父的政治主張,又耳濡目染,評價王安石及其作品時,刻意中傷,妄加曲解,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文學欣賞和詩意解析的角度看,范沖之論自是難以立足,研究者們也已通過解讀《明妃曲》詩句之本意對范沖的曲解有所辨正。但是從《明妃曲》接受史的角度看,范沖的意見又是極為重要的,以至于到了清代仍作為主流意見存有影響,如清初周容《春酒堂詩話》評《明妃曲》云:“介甫少而名世,長而結主,何所憤激而為此言?使當高宗之日,介甫其為秦太師乎?靖康之禍,釀自熙寧,王、秦兩相,實遙應焉,此詩為之讖矣。”見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1頁。實在是不可小覷。而范沖不遺余力詆毀《明妃曲》,也不能僅僅看作范沖以一人之力、純因私人政治恩怨而為,而應將其放到兩宋之交的歷史政治背景下分析,才能作更深層的理解。北宋末年,在金人戰鼓催逼、國祚動搖、疆土難保之際,宋欽宗為拯救局勢,整肅朝政,即位之初便將禍國殃民的蔡京集團作為首要處理對象,一一清除。然而,蔡京集團一向以新黨為標榜,以新法為旗號,雖其與王安石之人格與政治追求相去甚遠,但在時人看來,王安石與其新法亦難逃干系,故往往將禍國之責追究上溯至王安石。如右正言崔鶠上疏論蔡京誤國,就將責任亦歸咎于王安石,曰:“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 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1216頁。南渡之后,面對山河破碎,黎民流散,又屢受金人南侵的嚴重危機,匡扶社稷、重拾民心成為最為緊要的政治問題,這就必然要求檢討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高宗趙構基于政治需求,以靖康以來士大夫輿論為基礎,將王安石作為誤國的罪魁禍首來承擔歷史和現實的罪責,既維護了北宋諸帝的形象,又將在變亂之苦、國破之痛中尋找亡國之源的輿論,導向一個易為歷史信服的奸佞之臣。高宗為此,甚至不惜改修《神宗實錄》為定讞。最終使得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罪魁成為官方定論,不僅為《宋史》及之后的史家采納,也被社會普遍接受。
由此可知,范沖對王安石人格的攻擊和對《明妃曲》的曲解,并不僅是他的私人見解,更是循高宗之意而言,代表的是南宋初年時局未定的特殊歷史語境下,出于官方政治因素考慮的思維方式介入文學作品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官方對歷史輿論的導向及對主流意識的建構,不僅影響到了對王安石其人的評價,在“文如其人”、“知人論世”的中國古代傳統文學批評思維體系下,又自然會左右后世對其詩的解讀和評論。這也是范沖之論能夠在后世擁有如此悠遠的回音的原因之一。
三、“壞天下心術”的深層背景:荊公新學
與程門理學之爭南宋以來,官方對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評價上的貶損和否定,固然是造成對《明妃曲》曲解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對于在《明妃曲》接受史上源遠流長的這一誤讀,僅從官方政治需要的角度去看待,仍有欠全面完整。就上文所提及的范沖對王安石及其《明妃曲》所持之兩大主要觀點而言,王安石在政治上被定為誤國奸臣,仍然只是其否定和曲解《明妃曲》的間接原因,即因人廢詩。而更直接和根本的原因,在于此詩說明了王安石“以胡虜之恩而背君父”、心術不正,而王安石之心術不正,壞了天下心術,將不可變,此與新法相比流毒更巨、為害更大。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將王安石之心術不正與壞天下心術相聯系,并非范沖的觀點,而是出自程頤。而程頤的身份,首先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這就又牽涉了宋代學術史上一個重大且復雜的問題——新學與理學之爭。
簡而言之,之所以批判王安石之心術不正而能壞天下人心術,是因為王安石創立的新學一派,自北宋中期以來便被立為官學,地位顯赫,流布廣泛。相對而言,同樣誕生于北宋中葉的二程理學,其學術思想與荊公新學相異,在政治上又與反對變法的舊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產生之初,便已是相互對立的兩個學派。理學要擴大自己的影響,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也就勢必要標榜己之正確,而斥新學為非。在學術發展史上,一個學派為追求自身價值和地位,用種種否定、抨擊的方法,來達到排擠其他學派的目的,本是一種常見的歷史現象。但是,程頤斥王安石心術不正而壞天下人心術之語為理學傳人范沖引用,來曲解《明妃曲》之詩意,以致造成對《明妃曲》本意影響深遠的誤讀,其所表現出來的,卻已經不是單純的學術思想差異所造成的矛盾,而更應看作是兩宋之際新學與理學力量消長的一種特殊表現,帶有在政治巨變的背景下,兩個學術流派之間激烈爭斗的痕跡。
理學與新學從純粹學術流派思想之爭,發展為此消彼長、爭斗不休的兩個帶有政治性的學術流派,發端于宋徽宗之時。徽宗以王安石變法為旗號,大行黨禁和學禁,新學從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尊地位。在蔡京的提倡下,新學著作《三經新義》、《尚書?洪范傳》乃至一度被禁的《字說》等皆頒行天下,為士林所宗。同時王安石本人的政治、學術地位也空前提高,如崇寧三年(1104年),“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政和三年(1113年),朝廷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其子王雱為臨川伯,配饗文宣王廟”,《宋史》,第369、390頁。正式確認了王安石為孔子的正統傳人,新學取得儒家道統學統傳承中的正統地位。相對于新學而言,元祐時期盛行的其他學術流派在徽宗時卻遭到了嚴酷的打擊甚至禁毀,不僅厲禁傳習于公立學校,而且把“不許教授條禁”遍行曉喻,就連私下聚眾講學也被禁止。 程門理學亦在禁毀之列。崇寧二年(1103年),“詔: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34頁。可以說,新學在當時的獨尊地位,主要是徽宗和蔡京集團利用政治強權打壓、封禁包括理學在內的諸多學術流派的前提下確立的,故而隨著政局的劇變,其地位的喪失和遭到理學等學派報復性的打擊,也自是在所難免。
理學對新學之弊不遺余力地批判、攻擊甚至詆毀,從宋欽宗時就已經開始了,首先公開對新學提出嚴詞批判的,正是程頤嫡傳弟子楊時。他上疏痛陳蔡京禍國本于新學,猛烈抨擊新學一派“著為邪說”、“敗壞心術”、“以身圖利”,楊時:《龜山集》,《宋集珍本叢刊》本,線裝書局,2004年,第290頁。其論辭與范沖從《明妃曲》引發出的王安石“壞天下人心術”、“順其利欲之心”、“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如出一轍。可見范沖之評,又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否定和批判,同時帶有著濃重的程門理學打擊荊公新學的印痕。作為理學代表的楊時批判王安石及其新學的言論一出,就掀起了一場有關新學的激烈論爭,《宋史?楊時傳》載:“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見《宋史》,第12742頁。加上宋欽宗對元祐學術的翻案、獎掖和推崇,對王安石新法和新學的貶抑打擊,徽宗朝所確立的新學在政治學術上獨尊地位已經嚴重動搖,并開始受到批判、詆毀、丑化。這種傾向,在南宋高宗紹興初年達到了高潮。高宗出于政治上安撫人心、穩定局面的目的將亡國之責降于王安石一人,此前文已述。而相應的,高宗在學術流派上的政策,也發展為尊理學而黜王學。理學在南宋初政局轉變之際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一時勃爾復興。理學地位的上升,與之相對便是新學所受的極大沖擊。理學家們對新學的各種批判和攻擊,自然也得到了統治者的采納和支持。紹興六年(1136年),高宗在御制中明確指出:“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余六十年,邪說橫興,正涂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于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楊、墨之害甚于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為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閑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于天下之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1605頁。范沖所引程頤“壞天下心術”之說,經由皇帝御口作了蓋棺論定。這無疑也為南宋思想學術的主流劃定了方向,更進一步加劇了朝野尤其程門理學后進對王安石及其學術的批判,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整個社會對王安石及其新學的普遍認識。
在新學與理學復雜的政治學術斗爭和消長的背景下,范沖以詩為證,說明王安石心術不正,其根本亦在順應高宗旨意以及二程理學為代表的主流觀念,徹底否定荊公新學作為曾經的官學和儒學正統的價值。但本屬新學和理學的政治、學派之爭,卻因為范沖列舉了“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一句,并將其曲解為“壞天下心術”之實證,把《明妃曲》樹為負面典型,以至于《明妃曲》其詩,成為了與王安石心術不正、悖理傷道相表里的標志,其作為詩歌的本質和本意,反而被遺忘了。自此之后,南宋之人在論及《明妃曲》一詩時,便多與范沖一脈相承。如羅大經《鶴林玉露》“荊公議論”一則云:“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茍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羅大經:《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第186頁。朱弁《風月堂詩話》中亦記錄有太學生批判《明妃曲》曰:“若如此詩用意,則李陵偷生異域不為犯名教,漢武誅其家為濫刑矣。當介甫賦詩時,溫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為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不取而讀之乎?”朱弁:《風月堂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91年,第15頁。可見,在理學思想逐漸成為主流、影響日益加深的情勢下,對《明妃曲》的誤讀已經十分普遍且深入人心了。相比南宋一朝的政治否定,學術思想觀念的傳承具有更強大更持久的影響力,對《明妃曲》的誤解危害愈重。
四、務一時新奇,求前人未道:南宋曲解
主潮下的另類盡管自兩宋之交以來,從政治和理學的角度對《明妃曲》的曲解成為了宋代接受史的主流,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對《明妃曲》的詩美旨趣表示認同,并學習其精警議論,這也是需要提及的。
其中有直接加以評論的,如南宋李壁《王荊公詩注》引范沖之論后下按語曰:“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王荊文公詩李壁注》,第432頁。李壁之論,雖然在道德層面上仍承接南宋以來對《明妃曲》的大體判斷,認為“語意故非”、“其言之失”,然而他卻同時認識到了詩作“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的旨意。可以說,這是與王安石《明妃曲》及其唱和之作的詩旨本意是相符的,即以翻案為宗,從立意、議論和藝術表現上都力圖出新。這樣的判斷,已經有了重回詩歌文學解讀范疇的傾向。同時,他也認為范沖“傅致亦深矣”,可見他對于過分地從政治學術的層面批判王安石并延及其詩的解讀和接受方式,也是存有異議的。這或許與李壁生活在南宋晚期,與王安石并無個人恩怨和政見抵牾,且南宋初年那種官方和理學派一起極力否定和抵嗤王安石及其新學的氛圍也有所緩解的狀況有關。但能在理學為主流、王安石及其新學為批判對象的南宋,努力回歸到詩歌本身,以藝術審美的眼光加以欣賞,而不是過分地索隱詩句的政治道德內涵加以否定,這種態度本身已可謂持平了。上文我們將王回與黃庭堅關于《明妃曲》之辯,視為《明妃曲》接受史上由唱和認同向誤讀曲解過渡的表現,那么李壁的評價,也未嘗不可視為從誤讀曲解向詩歌藝術本旨回歸的一種過渡,雖然相比前者,在理學思想的長期控制和影響下,后者的過渡時間和過程都要漫長和艱難許多。
除了在評價上表現出的轉向,也有詩人用同題詩作的方式,通過學習和效法王安石《明妃曲》作詩,來表達其對原作思想藝術之創新的認同。如呂本中作《明妃》詩,其中“人生在相合,不論越與秦”一句,強調人心的相知相合,議論精辟,亦與傳統昭君詩的主題和議論傾向相異,表現出自覺的翻新創作意識。尤其是“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兩句議論,亦是警策之語出人意表:只要心靈相通相知,相處得融洽,就不應計較地域民族的差異。嫁給一個薄情寡義的漢人與去語言習俗不通的胡地受苦,并沒有區別。呂本中這樣的判斷,對封建時代的夷夏有別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挑戰,也對人性人心的相知相合的情感表達了熱切的呼喚。他在道學意識尤為濃厚的南宋,能夠這樣平等通脫地看待人性、人情和民族問題,尤顯難能可貴。故《苕溪漁隱叢話》評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30頁。然而呂本中“獨不蹈襲”,與王安石《明妃曲》的影響是直接相關的。前人亦已指出:“‘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周密:《浩然齋雅談》,中華書局,2010年,第35-36頁。故而呂本中此詩,在王安石《明妃曲》的接受史上,其實質同于《明妃曲》產生之初的唱和諸作,且是在南宋誤讀曲解《明妃曲》的主流下,正面接受和認同的少數表現之一。而從更寬泛的層面講,南宋一同呂本中學習《明妃曲》翻新之意的,還可舉出如高似孫《琵琶引》“長城不戰四夷平,臣妾一死鴻毛輕”,趙汝鐩《昭君曲》“年年兩軍苦爭戰,殺人如麻盈邊城。若藉此行贖萬骨,甘忍吾恥縻一身”等等,他們均以民族之間和平與和解為本,而不以夷夏觀念為宗,也表現出了一種通脫的觀念和創新的意識。
結語
文學作品自其創作完成之時,便自然進入了接受的軌道。文學接受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影響研究,其中不僅涉及作品本身的理解問題,還蘊含了隨著時代變遷,政治、文化、思想、心態等領域產生的復雜變化與作品之間的雙向互動,從而可以解析出與作品相關及作品之外的極為豐富的信息。《明妃曲》由于其作者王安石本身的特殊性,及其與整個宋代政治、學術、思想、文化的交疊性影響,其接受史尤為復雜曲折,也尤其值得仔細梳理和全面看待。宋代對《明妃曲》的接受史,本身所反映的,就是隨著時代和政局變化,詩歌與政治、學術、思想、文化的緊密聯系以及混淆,對于詩歌接受過程深刻的負面影響。從這種接受史的探討中,我們已解讀出許多歷史、政治、學術、文化的復雜背景和豐富信息。但同時,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上看,從追求本意的初衷出發,就詩歌閱讀和欣賞而言,則仍然需要回歸文本,將詩文作為文學創作來解讀和評賞,而不是作為政治學術紛爭的工具惡意曲解、過度闡釋。后者會對詩歌本意的正確理解造成多么嚴重的影響,在宋代《明妃曲》的接受史中,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責任編輯:張靜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