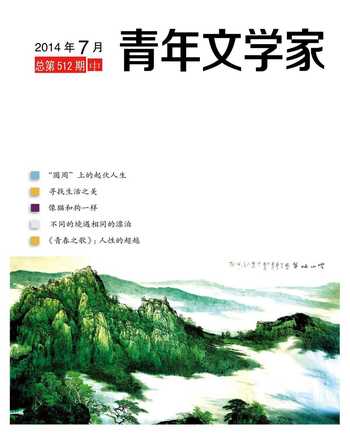小議《沉淪》中的“沉淪”精神
摘 要:郁達夫是一位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作家,他筆下的主人公主人有著感傷、飽郁的性格, 其形象飽滿而富有深刻的含義。本文分析了主人公的性格形象,并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揭示其身上的“沉淪”精神亦是當時民族的一種精神狀態。
關鍵詞:《沉淪》 ;“沉淪”精神;主體意識;民族精神
作者簡介:陳英,女,1992年生,山西省晉中市人,本科(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0-0-02
《沉淪》作為郁達夫的代表作,其主人公身上所體現的“沉淪”精神體現了作為五四青年后的一代知識分子,對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的深深的憂慮及以大膽暴露的方式表達對殘酷現實的控訴。
可以說,在《沉淪》主人公身上體現的“沉淪”精神,不只是一個個體青年的表現,而是在當時國內危機重重之下的整個民族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狀態。得出這一看法,是通過對文本中郁達夫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得出的。有人曾說:“我們可以申言:不存在對某文本的難以更改和絕對性閱讀,也不存在獨一無二的意義。我們也不認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對某文本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因為不存在某一定歷史時期內唯一有效的解釋。”1所以對于主人公身上的“沉淪”精神的含義,我們可以多角度分析:
從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角度分析:在《沉淪》這部作品中,作者對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的構建是這部作品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能體現作者寫作意圖的途徑。在對主人公的描寫過程中,首先表現在對主人公性格的細致入微而又充滿感傷的描述與刻畫上。《沉淪》中20歲上下的主人公無疑正處于人格塑定階段, 主人公在中國傳統文化格局中的“小小的書齋里度過了十幾年春秋”,這決定了他人格塑造的基礎,儒家傳統文化的修齊治平觀念與倫理道德的約束, 使其個體意識有弱化傾向, 這使他不敢在自己愛慕的異性面前公開自己情感的社會習慣心理和采用用放情山水來回避消解性本能的傳統意義上的移情模式。主人公所受到的文化也是我們民族一直以來接受的,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讓我們對打開國門后突如其來的變化應接不暇,我們一方面用自己幾千年來的正統文化看似執著的抵擋著外部世界的腐朽思想的誘惑,但另一方面身體及心理的本能卻想去接受、去學習,這種種沖突,在我們從近代以來對待外國來的一切包括器物、思想都可以看出,這也是我們民族所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所表現的出的,曾經不斷地反抗,在失敗后變為了無奈的掙扎。
其次是在塑造主人公的過程中,郁達夫有意的要突出主人公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產生了對生命意識的危機感。《沉淪》引起人們對覺醒了的自我的關注, 而對其賴以存在的生命本體予以重新審視的同時,主人公在試圖塑造與完善自己人格過程所深受的痛苦與悲劇性結局,也促使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在肯定與張揚自我意識的努力中產生一種巨大的生命意識的危機感。當面對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和錯綜復雜的政治動亂時,青年知識分子一時找不到出路,看不清方向,在前進中陷入迷惘,在反抗中淪入消沉,思想上處于苦悶、感傷、憂郁、頹廢之中。事實上,這是當時的社會通病,是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緒。這種苦悶,是一種時代的苦悶,這種頹廢同時也打印著深沉的時代烙印。2
最后作者的對主人公的描寫中,表達了作者本人及主人公的雙重悲哀與失望。通過對比主人公與郁達夫本人,我們會發現兩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正直,有才華的青年,懂得詩文和幾國外語,以賣文和教書為生。他孤僻內向,多愁善感,有點神經質,憂郁病時時襲來,經常迷戀于秀麗的山水。面對祖國遭受的苦難,自己身在異邦的屈辱,生活上的種種艱辛,使他宛如失群的孤雁。主人公的出生、經歷和教養與郁達夫都很相像,甚至外表衣著、音容笑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郁達夫是在表現自我,而表現自我,則是郁達夫創作的動力。他說:“藝術本來就是表現,而藝術品的表現,實際上不是事實本來的現象,卻是經過藝術家的氣稟的再現。”3因此在相同經歷的留日經歷中,當他們都發現了中日文化的差異及在兩種文化的交流與對比中所看到的差距, 看到民族積貧積弱對于青年一代身心的戕害,這不僅是主人公感到了無限的悲哀與失望,同樣也是作者郁達夫的深切體會及想通過文章表達的。
作者在對《沉淪》的創作過程, 不難看出這是作者自我心態的一種坦露,從文本中我們了解到:一個涉洋留學的青年, 一旦經歷了最初的外域文化與觀念帶來的新鮮感和內心亢奮后, 兩種文化、觀念在心靈中的碰撞便發生了。
這里我們看到了“他”的保守意識正無情地鞭撻著“他”天真的本能沖動, 壓抑、閉鎖的后果不僅令其陷于焦慮苦悶之境,還進一步使其人格結構嚴重失調,導致人格“沉淪”的悲劇結局。這一幅心理軌跡圖正對應著弗氏理論中關于“人格結構”的解釋。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理論中形象地敘述過“人格結構”中“自我”和“超我”各自所處的心理位置及其協調作用,“……自我的每個動作都受到嚴厲的超我的監視,超我堅持行為的一定準則,不顧來自外在世界和伊德的任何困難;如果這些準則沒有得到遵守, 超我就采用以自卑感和犯罪感表現出來的緊張感來懲罰自我……”4我們看到,《沉淪》中的“他”,一當原欲激情騰起之時,便受其保守意識的自斥自責,而對柔情嬌美異性不敢正視, 酗酒自殘無法擺脫原欲,他的“自我”始終沒有一次越軌行為,而“超我”連“他”難耐痛苦而采取的自我變態宣泄方式也未能放過。這個重負之下可憐的“自我”便為三種焦慮所折磨: 面臨外部環境的現實焦慮;面臨“超我”的心理常態焦慮;面臨原欲強力的神經變態焦慮。如此沉重的“人格結構”失調后的焦慮,其極限的超越必導致悲劇的結局。可以說《沉淪》的人物心理細節正是弗氏理論的一個個心理圖例。
從上文關于對主人公形象、性格分析以及此處從心理學角度的分析,那種“沉淪”精神不僅是主人公所特有的,而是暗指了當時整個國民身上所體現的“沉淪”精神。當時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來講,大膽地講“性”是不合禮法的,如果能壓制這種本能的欲望反會被稱道,文中的主人公在禮法與自身訴求滿足的選擇中掙扎而逐漸“沉淪”,他身上所經歷的也正是我們的民族在新舊思想、文明的沖突中不斷沉淪的寫照。追求自由,尋求自身的解放是五四時期的目標和口號,但在五四過去一段時間后,當時的社會現狀并沒有如作家、革命家所想的那樣,那根深蒂固的陳腐舊文化仍然在腐蝕著國民性,在影響著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外國先進文化與中國本土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不斷地沖突和激蕩,深刻地影響著一些青年知識分子,面對這種尷尬兩難的境地,他們只能不斷地在掙扎、反抗,如文中的主人公一樣,所以用“沉淪”精神一詞可以全面而深刻的表現了那個時帶整個民族的狀態。
《沉淪》就是從這樣一個獨特而深入的角度具體地展示了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錢杏邨曾說:“達夫是很健全的時代病的表現者。”5而作者本人也曾說:“我的消沉,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6因此,把文中的“沉淪”精神看做是對當時整個民族精神狀態的一種描寫是有合理意義的。
注釋:
[1][ 意大利] 弗·梅雷加利:《論文學接受》,馮漢津譯,見《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第三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版, 第214 頁。
[2]樂齊:《精讀郁達夫》,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版,第9頁。
[3]郁達夫:《文學概說》,《郁達夫文集》第五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版,第70頁。
[4]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結構》,[美]4卡爾文-斯-霍樂等《弗洛伊德心理學與西方文學》譯本, 第 128 頁。
[5]錢杏邨:《郁達夫代表作-后序》,見鄒嘯編《郁達夫論》,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87年版,第11頁。
[6]郁達夫:《北國的微音》,見《郁達夫文集》(第三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版,第91頁。
參考文獻:
[1]王自立,陳子善:《郁達夫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郁達夫:《悲劇的出生》,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