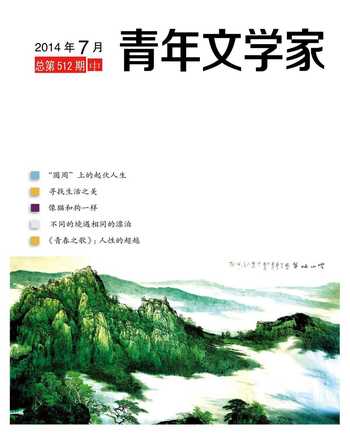略論陸機(jī)的個(gè)性理想與生命憂患意識(shí)
摘 要:陸機(jī)出身東吳世族大家,卻不幸在出仕之前遭遇亡國(guó)的慘痛經(jīng)歷,從小深受家族環(huán)境影響的他懷揣建功立業(yè)的遠(yuǎn)大理想,忍辱負(fù)重出仕晉朝,卻由于孤傲剛烈的個(gè)性在出仕之后屢屢不得志,再加上晉朝內(nèi)部數(shù)十年的權(quán)力紛爭(zhēng)與政治動(dòng)蕩而更是讓其在仕途之路上如履薄冰,內(nèi)心的憂慮與恐懼與日俱增,本文試圖通過(guò)陸機(jī)的家庭與政治等外部環(huán)境入手,通過(guò)分析其個(gè)性特點(diǎn)與理想追求,從而進(jìn)一步解讀其豐富纖細(xì)的內(nèi)心世界。
關(guān)鍵詞:陸機(jī);個(gè)性;理想;憂患意識(shí)
作者簡(jiǎn)介:張瑜(1986-),女,現(xiàn)為寶雞文理學(xué)院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教師,研究方向?yàn)橹袊?guó)古代文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 I20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4)-20--02
陸機(jī)出身于江東大族吳郡四姓之一的陸氏,其父祖皆有令名。《三國(guó)志·吳書(shū)·陸遜傳》注引《陸氏世頌》曰:“遜族紆,字叔盤(pán),敏淑有思學(xué),守城門(mén)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1]”孫吳時(shí)期,陸氏一門(mén)聲名顯著,功勛卓著,《世說(shuō)新語(yǔ)·規(guī)箴》載:“皓問(wèn)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余人。皓曰:‘盛哉![2]”受家族環(huán)境的影響,陸機(jī)從小便抱有偉大的志向,那就是希望將來(lái)能夠建功立業(yè),光耀門(mén)楣。然而正當(dāng)自己意氣風(fēng)發(fā)想要有一番作為之時(shí),卻遭遇東吳覆滅亡國(guó)的沉重打擊,他的兩個(gè)哥哥也戰(zhàn)死沙場(chǎng),那一年的陸機(jī)僅僅才二十歲,作為戰(zhàn)俘的陸機(jī)及其兄弟二人不幸被俘至洛陽(yáng),這場(chǎng)亡國(guó)的浩劫幾乎摧毀了陸機(jī)的所有夢(mèng)想和驕傲。雖然盡管晉朝對(duì)陸氏頗有賞識(shí)之意,但生性高傲不愿屈從為晉朝效力的陸機(jī),于次年便同其弟陸云重回華亭故居閉門(mén)讀書(shū),這一讀不想竟是整整十年。這十年的閉門(mén)苦讀也漸漸沖散了陸機(jī)內(nèi)心的恐懼與迷茫,讓他在冷靜之余思慮良多,吳國(guó)覆滅的根本原因究其根本還是在于那早已腐朽不堪的統(tǒng)治階級(jí)內(nèi)部,晉朝的統(tǒng)治者也只是壓垮駱駝背的最后一枝稻草,改朝換代是早晚的事,十年的光陰匆匆而逝,他唯一教會(huì)陸家兄弟的事情就是看開(kāi),這也讓壯志未酬的陸機(jī)重新燃起了出仕的斗志,終于在晉武帝太康十年,陸機(jī)兄弟接受了晉朝的應(yīng)詔踏上了仕途的新征程。
自從陸機(jī)兄弟出仕晉朝之后,其本身那種出身門(mén)閥貴族的優(yōu)越感以及自負(fù)才高的優(yōu)越感便慢慢顯現(xiàn),正所謂“木秀于林,風(fēng)必摧之”,不善于人情世故的陸機(jī)在一開(kāi)始便遭到了周邊很多士人的排斥,因忍受不了當(dāng)?shù)厝说呐磐馑枷耄愿窆掳恋乃38苓吶苏归_(kāi)唇槍舌劍,如他由于跟同為士族大家出身的潘岳相互看不順眼,這二人常常在大家面前上演相互譏諷的戲碼,博采眾長(zhǎng)的陸機(jī)甚至不惜與他人為敵經(jīng)常妙語(yǔ)連珠地炮轟在座的一干人等,因此,陸機(jī)的行為給眾人留下了剛烈、清厲的印象。在《世說(shuō)新語(yǔ)·賞譽(yù)》一篇就有如下記載述:“士衡長(zhǎng)七尺余。聲作鐘聲,言多慷慨。[3]”劉孝標(biāo)在為此作注時(shí)引《士人傳》曰:“機(jī)清厲有風(fēng)格,為鄉(xiāng)黨所憚。[4]”從很多史料的記載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求證,陸機(jī)的清厲以及他的剛烈個(gè)性讓他與周邊人的關(guān)系緊張,易產(chǎn)生矛盾,這其實(shí)對(duì)他的仕途之路并無(wú)任何好處,甚至還成為了他在未來(lái)仕途上面的一大障礙。正是這樣一個(gè)性格剛烈之人對(duì)其人生理想竟有著超越常人的執(zhí)著與狂熱,在前面我們已經(jīng)簡(jiǎn)要介紹到了他的家族及其成長(zhǎng)的環(huán)境,從小受此環(huán)境教育并耳濡目染的小孩無(wú)一不懷有建功立業(yè)的遠(yuǎn)大抱負(fù),陸機(jī)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就有用大量的筆墨論述、描述其家族成員卓越功勛的傳記、文章,如《吳丞相陸遜銘》、《述先頌》、《吳大司馬陸公誄》、《祖德頌》等,從這些文章的題目中我們便能清楚地看到他對(duì)其祖父和父親的崇拜尤甚,他在論述自己祖父陸抗的功績(jī)時(shí)極盡贊美之辭,甚至還將祖父的偉大形象以更加理想化的形象塑造出來(lái),這滲入骨髓的驕傲與崇拜之情已經(jīng)深深地影響到了陸機(jī)的人生觀、價(jià)值觀和世界觀,他對(duì)官場(chǎng)的狂熱與追求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chǔ)之上,通過(guò)不完全統(tǒng)計(jì),陸機(jī)在詩(shī)文中顯露的功名之嘆可以說(shuō)在西晉詩(shī)人中是最多的。如他在應(yīng)詔赴洛途中所做的《赴洛》二首,詩(shī)中的內(nèi)容便難掩作者對(duì)于自己即將展開(kāi)的宏圖偉業(yè)之藍(lán)圖的喜悅之情同時(shí)做好了不準(zhǔn)備回家的長(zhǎng)遠(yuǎn)打算。無(wú)論順境逆境,他都會(huì)借助詩(shī)歌傳達(dá)自己的強(qiáng)烈的決心和抱負(fù),如他在入晉之后屢遭仕途挫折之時(shí),便有做《長(zhǎng)歌行》、《遨游出西城》、《秋胡行》、《日重光行》、《月重輪行》等詩(shī)來(lái)激勵(lì)自己迎難而上、勇于奮進(jìn),又比如他在自己彌留之際所作的《百年歌》十首,詩(shī)中寫(xiě)了自己從十歲到百年的人生變化,不僅是身體上還有對(duì)世間萬(wàn)物認(rèn)知的心理變化,正是因?yàn)榭赐噶巳松鸁o(wú)償?shù)淖兓哺荏w會(huì)到人生樂(lè)趣所在,反反復(fù)復(fù)的“清酒將炙奈樂(lè)何。清酒將炙奈樂(lè)何”二句讓詩(shī)人也學(xué)會(huì)了苦中作樂(lè)。《晉書(shū)·陸機(jī)傳》:“時(shí)中國(guó)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jī)還吳,機(jī)負(fù)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5]”正是因?yàn)樗麑?duì)功名的那份執(zhí)著與熱情,才讓他在西晉政局最混亂險(xiǎn)惡的時(shí)候始終不肯抽身而退。
接下來(lái)我們?cè)賮?lái)說(shuō)一下陸機(jī)的憂患意識(shí),在前文中我們也提到過(guò)還未真正出仕的陸機(jī)便遭遇了亡國(guó)之痛的坎坷經(jīng)歷,這對(duì)于陸機(jī)人生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便是一次徹底的蛻變,亡國(guó)之前還意氣風(fēng)發(fā)、壯志滿懷,亡國(guó)之后的陸機(jī)便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里面都無(wú)法走出亡國(guó)的陰影,身心俱疲。在其隱居讀書(shū)的那十年里面,常常感慨世事的無(wú)常與生命的短暫。那種痛徹心扉的打擊曾經(jīng)一度讓陸機(jī)對(duì)前途感到迷茫甚至是絕望。經(jīng)過(guò)十年認(rèn)真反思的陸機(jī)在入仕晉朝后本以為能夠重圓兒時(shí)的夢(mèng)想,然而在其遭遇了楊駿、賈謐爭(zhēng)權(quán)以及八王之亂的政治動(dòng)亂后,在政治夾縫中茍延殘喘的陸機(jī)也倍感仕途的兇險(xiǎn)。他在《述思賦》中就寫(xiě)道:“情易感于已攬,思難戢于未忘……嗟余情之屢傷,負(fù)大悲之無(wú)力。敬彼途之信險(xiǎn),恐此日之行昃。”詩(shī)文上下無(wú)不流露出詩(shī)人對(duì)命運(yùn)的無(wú)奈,與對(duì)仕途之路多艱的感傷,又如《嘆逝賦》中:“咨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凄其多念,感貌瘁而鮮歡,幽情發(fā)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wú)樂(lè),詠在昔而為言。”詩(shī)人在寫(xiě)此詩(shī)之時(shí)晉朝的政治已經(jīng)越發(fā)地兇險(xiǎn),一步錯(cuò)步步錯(cuò)的陸機(jī),也不禁為生命的短暫而悲痛。當(dāng)身陷八王之亂的之時(shí),陸機(jī)在《門(mén)有車馬客行》中寫(xiě)道:“借問(wèn)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慷慨惟平生,俯仰獨(dú)悲傷。”該詩(shī)表達(dá)出了詩(shī)人對(duì)死亡的恐懼與憂患之情。此外,在面對(duì)成都王穎對(duì)他的高官封賞時(shí),不愿在非常之時(shí)成為旁人非議和嫉恨對(duì)象的陸機(jī)是堅(jiān)辭不受,因?yàn)樵谒磥?lái):“羈旅人宦。頓居群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故辭都督。[6]”他在仕晉之后的遭遇的種種排擠與輕視后,也同樣深刻地體會(huì)到身為吳國(guó)舊臣的自己,自然會(huì)遭到當(dāng)?shù)爻甲拥呐懦猓髞?lái)每每遭遇他人的非議與不公時(shí)他便有感而發(fā)道:“道雖一致,途有萬(wàn)端。吉兇紛藹,休咎之源。”(《秋胡行》)這種“身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窘境常常讓陸機(jī)感到不安和無(wú)奈,因而內(nèi)心的憂患意識(shí)也更甚。
綜觀陸機(jī)的一生,可以說(shuō)是非常的不幸與悲哀的,他懷著心中的出仕執(zhí)念在宮廷內(nèi)部的相互斗爭(zhēng)中常常奮力突圍,為自己尋求安身立命的靠山,他在仕晉先后曾為多人效力,又多次因?yàn)樗讨鞯牡古_(tái)而險(xiǎn)些丟掉性命,這種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雖說(shuō)身不由己,但因始終無(wú)法放棄心中的執(zhí)著而最終成為了政治的殉葬品。可以說(shuō),陸機(jī)詩(shī)文中的憂患意識(shí)并非空穴來(lái)鳳,它是陸機(jī)現(xiàn)實(shí)政治生涯的真實(shí)心理寫(xiě)照。
注釋:
[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guó)志.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6.795.
[2]余嘉錫.世說(shuō)新語(yǔ)箋疏.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551.
[3] 余嘉錫.世說(shuō)新語(yǔ)箋疏.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443.
[4]余嘉錫.世說(shuō)新語(yǔ)箋疏.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443.
[5] 房玄齡.晉書(shū).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4.1256.
[6] 房玄齡.晉書(shū).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4.2376.
參考文獻(xiàn):
[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guó)志.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6
[2] [3] [4]余嘉錫.世說(shuō)新語(yǔ)箋疏.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
[5] [6]房玄齡.晉書(shū).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