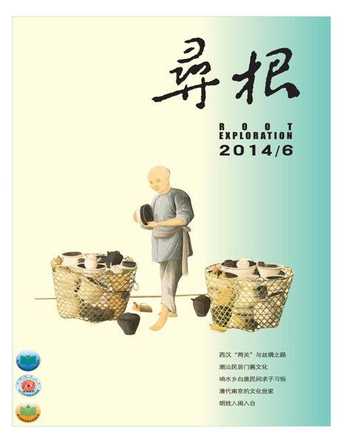福建戲神“田公”與原始崇拜
吳燕玲
福建戲神信仰概況
由于地域和聲腔劇種的不同,以致戲劇行業在尋依、塑造行業保護神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變異性,北方有供奉唐明皇、清源祖師、二郎神等為戲神的,而南方尤其是福建則祀奉田公元帥為戲神。田公元帥又稱田都元帥、相公爺、田元帥、宋江爺、雷元帥、三田元帥等。
福建各地的田公塑像形態各異,就莆仙戲班而言,其田公元帥有文身、武身之別。武身田公元帥為立式,紅臉、紅袍,頭頂有兩條辮子,嘴上畫成一只“螃蟹”,兩旁有風火二童,前有靈牙將軍。文身的田公元帥為坐式,金面金身,頭戴“金圣冠”,嘴上無“蟹”,亦無二童與武士。
據專家學者考證,田公信仰源于南宋,盛于明清。直至今日,田公信仰依然熾盛,不僅福建、潮汕一帶戲班供奉田公,而且遠播臺灣、東南亞等地。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戲神田公信仰不僅跨越了區域,而且超越行業神崇拜的范圍,成為保境安民的地方神。以泉州的田公信仰為例,泉州城區11個鋪境,郊區35個村落奉祀田都元帥為保護神,而且其神職廣大,凡演提線木偶戲,均首先請相公爺“踏棚”(請神驅邪);民間婚、壽等喜慶,凡曾發愿酬神的,由相公爺“請諸神”;凡宮廟新造神像或新造祠堂“進主”,也由相公爺“請神”。相公爺如此神通,被泉州人民奉為鋪境廟的境主也是常理之事。
田公信仰中的土地崇拜
我國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的社會狀態,農之本是田,莊稼的豐歉,取決于大自然的恩賜,人們對田祖頂禮膜拜,尤其在豐收時節,在年終歲暮或災歉季節,以擊鼓歌舞等形式祭祀田祖,以達到酬神祈報的目的,并盼來年五谷豐登、人畜興旺,許多文獻典籍都有先民祭祀田祖的記載。
福建各地的縣志也大都記載有祭祀田神祈求農業豐收的習俗,因此有戲神超越行業性質而成為各地奉祀的保護神,其所折射出來的邈遠信息正與古代的祭祀田神、土地的崇拜不謀而合。
從田公傳說隱含的信息分析來看,它一定程度上傳遞著某些原始的崇拜意象。相傳唐明皇時,浙江杭州鐵板橋頭有一蘇家小姐同女婢出門游玩,路過稻田,適值稻穗灌漿,蘇小姐信手拈了一粒稻谷,放入口中咀嚼,稻谷乳漿味甘,遂咽下,忽覺腹中奇異,數月后腹漸隆起。其父疑之,小姐乃告緣由。至期蘇小姐產下一男孩,蘇父密令女婢抱出棄之。女婢抱至原來稻田,放在田中而返。數日后,小姐不忍,復遣女婢前往探視。女婢至稻田,見毛蟹爬在嬰兒口上,吐出唾沫讓其吮吸,嬰兒活潑可愛,大異,乃抱返蘇家撫養,并以田為姓。
宋元福建戲劇主要是從戲曲興盛的浙杭一帶傳入的,因此關于福建戲神田公的身世傳說地點為杭州一說就不足為怪了。尤為重要的是,整個傳說都離不開“田”:蘇小姐路過稻田,含稻谷而孕,所生嬰孩棄之于田,而后以田為姓。閩南一帶有個風俗,從海里撈來的生物若是水母或蟹類,便會天降大雨,因此蟹沫哺育田公,隱喻雨水滋養農田、萬物。毋庸置疑,田公信仰是農耕文化的產物,與遠古田神、土地崇拜的邈遠意象是一脈相承的。
因為地域的差異,各地田公的神誕日也不一。南安坑口田都元帥的神誕日是農歷正月十六日,正符合泉南“春節民謠”中所唱念的“十四結燈棚,十五上元丸,十六相公生”。泉南一帶正月十六日為土地公的神誕日之一,揭示了田公信仰與土地信仰屬同源。大部分田公信仰區域的田公神誕日為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三日,而農歷六月、十二月正符合“春播秋收,夏種冬藏”的農業生產規律。每逢神誕日,都有祭祀田公的賽社,慶祝豐收,并盼來年風調雨順。可見田公神誕日所透露的信息離不開農耕文化的土地崇拜。
田公信仰中的動物崇拜
田都元帥像位“九天風火院”兩旁,右寫“大舍”左寫“二舍”。傳說大舍、二舍是相公門徒,兩人見相公常入宮內,乃求攜其入宮,以睹皇后豐姿。相公被纏不過,遂使大舍化為金雞,納入右袖中;二舍變作玉犬,藏在左袖中。相公入宮為娘娘舞蹈,左手上舉,右袖下垂,金雞落地,急以左手捉之,玉犬又落下,皇后見金雞玉犬甚是有趣,取金圈罩住,從此金雞玉犬不能還原人形。
傳說故事中出現的雞、犬、蟹與農業社會的生活密切相關,其中透露出某些信仰信息,這就是對動物的崇拜。
動物崇拜是由當時人們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福建是閩越族的聚居地,與中原漢族相比,閩越族的社會形態發展比較緩慢,較長時期過著刀耕火種、采集狩獵的生活。野生的動物是人類求得生存的必要條件。在極為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要把這些自然物變成“為我之物”是要歷盡千辛萬苦的,即要馴化動物是十分不易的。因此,人們對某些家禽家畜也賦予神秘色彩,加以崇拜。如雞被視為吉祥物。自古以來人們將雞為犧牲獻祭,并用以禳災祛邪。田公塑像大舍即為金雞,則帶有驅邪的濃厚意味。而二舍指玉犬反映了福建典型的對狗的崇拜。
福建居住著占全國一半的畬民。畬民長期處在游獵山耕階段,在與大自然搏斗的生存競爭中,馴化了的犬類成了人類從事狩獵生產的馴服工具和得力助手。據說畬族的圖騰崇拜對象盤瓠即是九耳犬。福建某些地方田相公神像的旁邊有為狗頭而人身的靈牙將軍像,這也反映了對狗崇拜的某些遺緒。
結語
田公信仰是一種具有民俗性、地域性與行業性等多種文化意涵的信仰心理和信仰行為,它是福建人民在與大自然斗爭中自發產生的一種精神寄托,田公信仰伴隨著人類的生產勞動和生活而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仍帶有較多的原始痕跡,始終沒有改變其低級、原始、分散、自發的狀態。從田公的塑像、傳說、神誕日等眾多信仰意象的紛繁復雜,可知田公信仰有模糊性、隨意性、變異性,但田公信仰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仍具有傳承性,透過駁雜紛繁、荒誕離奇的信仰意象去分析和考證,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包括對土地公的崇拜、對雷電雨的崇拜、對雞犬蟹等動物的崇拜,說明田公信仰與遠古人類對自然界既畏懼又依賴衍生的原始崇拜是一脈相承的。立足于田公信仰的傳承性來考證戲神雷姓與田姓實屬同源,并解釋戲神之所以超越行業性而成為地方保護神實是農耕文化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