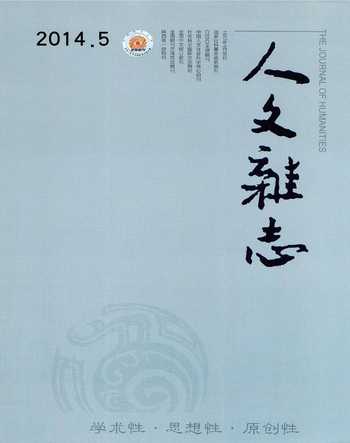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新論
杜學(xué)敏
內(nèi)容提要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概念是一種常常與喜劇相提并論的審美形態(tài),它同另兩種悲劇概念即作為日常話語的悲劇、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既相聯(lián)系又相區(qū)別。悲劇的本質(zhì)表現(xiàn)為悲劇主人公個性、人性本質(zhì)所遭受的傷害或毀滅。悲劇審美形態(tài)同時具有必不可少的四個基本要素,即悲劇主角、悲劇事件、悲劇悖論和由悲劇審美者所承當?shù)谋瘎⌒Ч@也決定了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具有四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不能被簡單地視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崇高之一種,盡管兩者存在諸多相關(guān)性。
關(guān)鍵詞悲劇概念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悲劇審美悲劇美崇高
〔中圖分類號〕I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5-0050-08
一、悲劇概念的三種基本用法及其關(guān)系
“悲劇”術(shù)語在日常生活與大眾傳媒中基本指的是一些令人感到不幸、同情乃至傷感的悲慘遭遇與苦難事件,如一次車禍、一場礦難、一樁兇殺案件等等。在更多、更專業(yè)的語境下,原本發(fā)源于古希臘酒神即狄俄尼索斯祭祀儀式的“悲劇”同“喜劇”一樣是被作為一種戲劇類型或體裁而看待,且每每與那些西方藝術(shù)史上的戲劇與文學(xué)(作為劇本)經(jīng)典之作,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等等聯(lián)系在一起。
“悲劇”術(shù)語實際并不囿限于上述日常生活傳媒話語和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范圍內(nèi)。尤其在相關(guān)的哲學(xué)性理論探討中,它同“喜劇”一樣還被擴展至人們對一些小說、影視等敘事性藝術(shù)類型的審美體驗與評價,如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的《紅樓夢》、費雯?麗和羅伯特?泰勒主演的電影《魂斷藍橋》等等,甚至被用于對諸多真實的現(xiàn)實或歷史事件的特別觀照上。末一種意義上的“悲劇”明顯不是作為戲劇類型來使用,雖不排除其中所隱含的悲慘事件、苦難遭遇等作為日常話語的悲劇內(nèi)涵,但它其實已經(jīng)進入到作為審美形態(tài)之一的美學(xué)范疇內(nèi)了。為免于和作為戲劇及文學(xué)藝術(shù)樣式的悲劇概念相混淆,美學(xué)家往往稱美學(xué)上的悲劇(tragedy)為“悲劇性”(the tragic)或“悲劇美”(the tragic beauty)。
盡管不排除不同時代、不同理論家給予悲劇概念以特殊的規(guī)定性,三種悲劇概念即作為日常話語的悲劇、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和作為美學(xué)范疇或?qū)徝佬螒B(tài)之一的悲劇則構(gòu)成了悲劇概念的基本用法。三種悲劇概念各有其使用范圍,其內(nèi)涵所指也大有不同,但也并非各不相干,毋寧說存在著十分密切而復(fù)雜的邏輯與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概念實際是日常話語中的悲劇概念與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概念產(chǎn)生的歷史根據(jù),雖然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形態(tài)只是美學(xué)研究的悲劇形態(tài)的一部分,但卻同呈現(xiàn)于其他藝術(shù)類型如小說、影視等敘事性作品中的悲劇形態(tài)一起,構(gòu)成了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
* 本文系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shè)工程”重點編寫教材《美學(xué)原理》的階段性成果,由作者獨立撰寫完成,卻與首席專家尤西林先生的相關(guān)著作與指導(dǎo)密不可分,在此謹表謝忱。
悲劇的原型與典型代表;日常話語中的悲劇即苦難、不幸和死亡等悲慘事件雖不等于作為藝術(shù)類型與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但它無疑又常常構(gòu)成了作為藝術(shù)類型悲劇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創(chuàng)作素材,也構(gòu)成了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及其研究的現(xiàn)實背景;作為審美形態(tài)范疇的悲劇明顯不能等同于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苦難、不幸和死亡,也包括但不限于戲劇及其他藝術(shù)類型中的悲劇形態(tài),但它不能脫離后兩者而存在,在一定意義上,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概念是對藝術(shù)類型中的悲劇形態(tài),歷史或現(xiàn)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事件的哲學(xué)概括與意義提升。
另外,從悲劇理論研究而言,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概念之于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概念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意義更加重大,因為作為戲劇藝術(shù)類型的悲劇概念不僅構(gòu)成了整個悲劇理論史的核心,也因此成為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討論的重要前提與基礎(chǔ)。人類始于古希臘時期的悲劇審美史源遠流長,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悲劇理論研究也已逾兩千多年,關(guān)于悲劇的審美本質(zhì)及其特征迄今卻仍莫衷一是,罕有公認定論。從邏輯上講,作為一種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同其他審美形態(tài)一樣實際是審美及美的本質(zhì)在審美形態(tài)層面的具體滲透和展開,也可以說是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矛盾運動狀態(tài)的具體表現(xiàn)。中外美學(xué)原理類著作在討論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時,普遍從介紹古今形形色色的著名悲劇理論開始或圍繞這些理論而展開的常規(guī)寫法表明,悲劇的美學(xué)本質(zhì)其實也由美學(xué)史上那些出發(fā)點迥然有別的著名觀念所規(guī)定。本文關(guān)于悲劇概念的美學(xué)內(nèi)涵、性質(zhì)與特征之探析將以學(xué)理分析為線索,同時兼顧自古希臘以來的古今中外的相關(guān)著名悲劇理論。
2014年第5期
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新論
二、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的性質(zhì)與分類
由三種悲劇概念及其關(guān)系遂牽扯出一個頗有爭議性的重要理論問題:現(xiàn)實生活中有無美學(xué)上所謂的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
大多數(shù)美學(xué)家給予否定回答。英國學(xué)者海倫?加德納(Helen Gardner)說:“嚴格說來,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悲劇,悲劇是藝術(shù)品,因而它是用來提供娛樂的。事件本身也并不具有悲劇性,它們可能是災(zāi)難性的、令人震驚的、可憐的或是恐怖的,但不經(jīng)過想象力的加工則不具有悲劇性。”[英]海倫?加德納:《宗教與文學(xué)》,江先春、沈弘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頁。朱光潛也曾明確寫道:“現(xiàn)實生活中并沒有悲劇,正如辭典里沒有詩,采石場里沒有雕塑作品一樣。悲劇是偉大詩人運用創(chuàng)造性想像創(chuàng)作出來的藝術(shù)品,它明顯是人為的和理想的。”朱光潛:《悲劇心理學(xué)》,張隆溪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3年,第243頁。還有學(xué)者更具體地從美學(xué)視角分析指出:“現(xiàn)實中存在的悲劇,經(jīng)常迫使人們采取嚴肅的倫理態(tài)度和實踐行動。……對于跟人的實踐利害直接聯(lián)系的現(xiàn)實中的悲劇,人們很難、一般也不應(yīng)直接采取審美觀照的態(tài)度。因此,只有反映形態(tài)的悲劇藝術(shù),才經(jīng)常作為審美對象,引起人們的審美愉悅。”王朝聞主編:《美學(xué)概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頁。
上述分析無疑有其道理,也符合“一般”的審美活動實際。不過,從事實上講,“很難”并不意味著一定不會存在,“一般”也就給特殊情況的出現(xiàn)留下了余地;從邏輯上講,只要承認與圍繞特定藝術(shù)品而發(fā)生的藝術(shù)審美不同且沒有一般意義上的藝術(shù)品參與的自然審美、社會審美這兩種所謂現(xiàn)實審美的存在,在一定時空距離的間隔下,歷史與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苦難與悲慘事件就未嘗不能呈現(xiàn)為美學(xué)意義上的悲劇審美形態(tài)。
換言之,現(xiàn)實生活中當下發(fā)生的苦難與悲慘事件的確首先是需要“人們采取嚴肅的倫理態(tài)度和實踐行動”的倫理事件,因而并不構(gòu)成美學(xué)意義上的悲劇形態(tài)。但這些苦難與悲慘事件一旦成為歷史,接受者一旦與之拉開一定的心理距離或給予審美觀照,那些分明不是藝術(shù)虛構(gòu)而是真實的悲慘事件就會以作為審美形態(tài)的悲劇呈現(xiàn)出來。這從我們下文列舉的實例不難得到證明。而且,在我們看來,戲劇與文學(xué)藝術(shù)史上的那些以真實的歷史或現(xiàn)實事件為題材的經(jīng)典悲劇作品的誕生,無不以此類現(xiàn)實的悲劇審美形態(tài)為前提。很難設(shè)想以真實的歷史或現(xiàn)實事件為題材的悲劇藝術(shù)作品會在未經(jīng)審美觀照的前提下創(chuàng)作出來。悲劇藝術(shù)家對歷史或現(xiàn)實中那些被視為藝術(shù)悲劇素材的真實事件,“運用創(chuàng)造性想像”(朱光潛)進行“加工”(海倫?加德納)的初始階段,或創(chuàng)作一部特定悲劇藝術(shù)品的過程,就已經(jīng)是或至少是伴隨著現(xiàn)實的悲劇審美的發(fā)生過程。
可見,現(xiàn)實悲劇審美形態(tài)的否定者,不僅對由無悲劇藝術(shù)品產(chǎn)生卻能夠?qū)φ鎸嵉谋瘧K事件予以歷史性審美觀照的觀照者或接受者所承擔(dān)的現(xiàn)實悲劇審美形態(tài)視而不見,而且也顯而易見地忽略了由悲劇藝術(shù)家自身承擔(dān)的、作為藝術(shù)審美形態(tài)悲劇基礎(chǔ)的現(xiàn)實悲劇審美形態(tài)。因此,作為美學(xué)研究對象的悲劇概念既包括圍繞各門類敘事性悲劇藝術(shù)作品而普遍存在的藝術(shù)悲劇審美形態(tài),也包括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針對具有悲劇性意義的社會生活與歷史事件而展開或存在的現(xiàn)實悲劇審美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