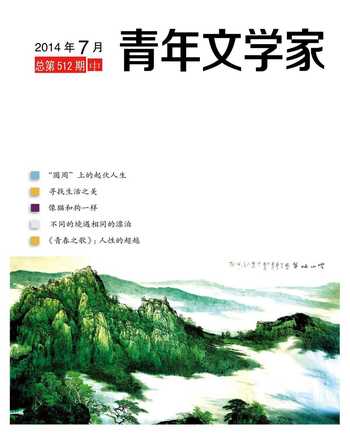黃賓虹的五筆問題
鄭海文
摘 要:二十世紀的畫家中,黃賓虹是一位站在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交叉口上的重要畫家,他的“五筆”理論——“五筆”即“平、留、圓、重、變”,將筆墨問題的闡述發展到極致。
關鍵詞:黃賓虹;五筆;意義
[中圖分類號]: J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0--01
賓虹老人的一生是坎坷波折的,家庭的變故、革命的危機,都深深影響過他的生活,但是,這一切外在的東西都不能影響他對筆墨的追求。
賓虹老人常常朗吟道:“和合乾坤春不老,平分晝夜日初長,寫將渾厚華滋意,民物欣欣見阜康。”1“渾厚華滋”是個常常被人提出來說評價黃賓虹筆墨的一個詞,“渾厚華滋”不僅僅是是一種筆墨意趣,給人帶來一種審美意味的筆墨狀態,更是賓虹老人的一種心境,對他那種博大胸懷以及學富五車文化內涵積淀的集中表達,是通過一種自然意象表達出了自己的內涵意蘊。筆者認為這是筆墨技法層次的最高境界,基于技法而又超乎技法層面,正如老人自己所說:“不求氣韻而氣韻自至,不求法備而法自備。”這是長期修煉后的境界,是信手拈來的一種從容,此時將從畫匠變成大家。
黃賓虹對于筆非常重視。“五筆”:“一曰平,如錐畫沙;二曰圓,如折釵股;三曰留,如屋漏痕;四曰重,如高山墜石;五曰變,參差離合,大小斜飛,肥瘦短長,俯仰斷續,齊而不齊,是為內美。”2
第一種筆法“平”
其中,“平”包含三層意思:一是在姿勢上說,所謂“指與腕平,腕與肘平,肘與臂平”,黃賓虹認為這樣的姿勢可以讓全身的力氣用力平均。二是“起訖分明,筆筆送到,無柔弱處”, 不讓線條和點變的虛,按照這種姿勢應該不會是側鋒,像中鋒用筆,這就是常說的的“中鋒取勁,側鋒取妍”。最后是黃賓虹強調了一下“平非板實如木削成,有波有折”,說明他要的“平”不是那種沒有變化的平,而是做到前兩步的“平”,方可產生那種千變萬化,實現最大程度的相反相成,就像是那種可以用枯筆畫出很潤的感覺。在這里有一種哲學的思辨關系。
第二種筆法“圓”
黃賓虹用了一個很貼切的比喻來說“圓”,那就是“如折釵股”,釵股一般都是金屬做的,把釵股弄折了那個彎曲的地方必定是圓的,大自然中的萬事萬物都不是圭角分明的,所以要按照自然的樣子去畫山川草木,多用“圓”。筆者對黃賓虹提出的這個說法真的是非常贊同,或許有人覺得這個不值得專門提出來說,但是,當你真的拿起毛筆去畫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都是我們不經意間容易犯的錯誤。而且,“釵股”也還給人一種內含力量的感覺,相反“平”中的“錐畫沙”用筆澀行,力量外露。
第三種筆法“留”
書法家沈尹默曾經這樣解釋過“屋漏痕”:“水滲入壁間,凝聚成滴始能徐徐流下來,其流動不是徑直落下,必微微左右動蕩著垂直流行,留其痕于壁上。”
黃賓虹在此用這個比喻來說明“留”要積點成線,上下映帶,不疾不徐,讓筆充分體現出力量和韻味。
第四種筆法“重”
黃賓虹在“重”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首先要有“弩發萬鈞”的力量,但又不能濁、不能滯。再次,要舉重若輕,雖細亦重含剛勁與婀娜,產生筆墨的最大功效。而這種筆墨的“重”是要足夠的內修外煉才能達到的境界。也可以看作是對以上三種筆法的綜合境界的提升。
第五種筆法“變”
黃賓虹在《談畫》中這樣描寫“變”:黃賓虹對于“變”主要暗含兩方面的意思:一個是自然界眾多的形象是萬變的,相互回顧的,所以在處理物象上要有“變”,不能被桎梏。二是藝術的道是不變的,雖然表面上看是千變萬化的,但是那個中心的原則是不變的。
黃賓虹很明確地表達了“五筆”之間的內在關系,它們并不是平行的,而是遞進的,最后一個 “變”字,也將整個“五筆”的理論推向了一個更廣闊的天空,它使得前面的四種筆法都充滿了活力,因著“變”是“用筆要變,不拘于法”的。黃賓虹“濃、淡、破、積(漬)、潑、焦、宿”的“七墨”法,也是于“五筆”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的。黃賓虹認為“五筆既嫻,可言墨法”。黃賓虹在《九十雜述》中詳細敘述了七墨的理論。錢學文在《黃賓虹墨法——漬與積的區別》中區別了這兩種墨法。大概是說:漬墨是先用筆蘸濃墨,再蘸清水,作畫大點行筆,中農四邊淡,水漬墨色自然溶化,有滋潤靈活之效。而寂寞,是墨上加墨,層層積疊。濃墨淡墨之間用以水分很少的枯筆,形成“干裂秋風”的表象,表面看起來很枯燥,其實確富有“潤含春雨”的意味。這水墨的最高境界,實現最大程度的相反相成。好的墨法應該是哪種就是哪種,不能不倫不類,好的墨法應該豐盈但是不臃腫,瘦勁但是不枯羸。不管用哪一種墨法,墨色不能生澀呆滯,否則成為死墨。
賓虹老人是古典傳統的集大成者,但是又不甘于僅僅是學習,更重要的是創新,按他的話就是“師古人以啟來者”,“由舊翻新”。按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要出古人頭地,還要別開生面”,他做到了,他成為從古典到現代轉折的關鍵性人物,為中國畫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
注釋:
[1]黃賓虹《黃賓虹畫語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2]蔡星儀《黃賓虹“民學國畫”的新時代意義》載于《朵云》第六十四期,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