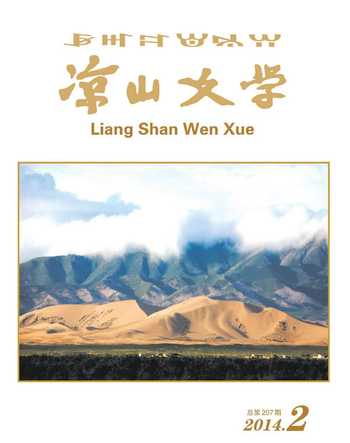念 姑
2014-04-29 17:29:17阿蕾
涼山文學
2014年2期
阿蕾
念姑是個重度羅鍋背,走路時頭與腳幾乎呈九十度的夾角,也許畸形的脊柱壓迫著肺部呼吸不暢,使她在不負重的情況下也總是埋頭走一小段路就停下來,一只手撐腰,一只手撐膝蓋,費力地挺起雞胸喘上一會兒,然后才又佝僂著身子埋頭前行。
據說念姑本是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囡囡,還在月窩里時,因為缺人手的母親總是把她系在背上干活,有一次她的母親把她系在背上給豬圈起糞時,也許糞毒侵襲得了一場重病,在耗盡錢財延請蘇尼畢摩作了很多驅邪儀式后,人救活了,但背上卻長出一個羅鍋,再也打不抻腰,乖巧的小臉也長成一副凹鼻凹臉的怪模樣,眼角上的眼屎總也揩不干凈,翹起的下巴上總是掛著長淌的涎水。家里人不屑于再叫她根據屬相歲位取的本名,而是叫她的外號“念姑”——凹臉。外人呢,也都跟著她的家人在稱呼后邊無一例外地加上外號“念姑”,全然忘了她還有一個本名。
念姑不僅身患殘疾,還有些智障,高興起來涎水滴答地又說又笑,甚至手舞足蹈地哼著當時流行的歌曲“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盡管不知歌詞唱的啥意思,還是搖頭晃腦地唱得非常投入;不高興時氣粗如牛喘,見什么拿什么出氣。這時如果有誰再招惹她,那么這人這一天就別想安寧。她的母親可能因為小時候沒把她帶好讓她落下殘疾心中愧疚,也有可能怕把她惹著了她罷工不干活不說,還有可能將背水桶滾下山去——白天出工干活外,早晚背水是念姑雷打不動的任務——所以更是處處陪著小心,不管怎樣窩火都隱忍著不敢罵她。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