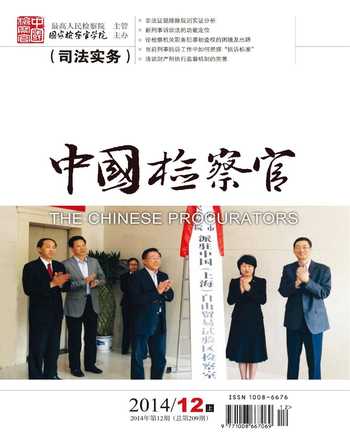“多次盜竊”的累計應包括已經受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
鄭小敏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3年解釋》)第3條將“多次盜竊”的含義由1997年司法解釋所界定的“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調整為“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加大了對盜竊犯罪的打擊力度。鑒于規定中,需要累計多次盜竊行為才構成犯罪,于是在實踐中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能否作為構成盜竊犯罪的某次盜竊予以累計。筆者認為,“多次盜竊”中的盜竊行為既包括未受行政處理、處罰的行為,也包括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
一是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從主觀惡性對比來看,一種情況是行為人之前的兩次盜竊行為都沒有受到行政處罰,抱著“查不到我”的僥幸心理繼續實施盜竊,主觀惡性相對較輕;另一種情況則是之前兩次以上的盜竊行為已經受到了行政處罰,在明知實施盜竊可能再次遭受國家法律懲處的情況下,依然不思悔改,繼續實施盜竊。顯然,后一種行為具有藐視國家法律、挑戰國家執法權威的性質,主觀惡性較大。從處罰的平衡性來看,同樣是實施了三次盜竊行為,在前兩次盜竊未被發現、未被處罰的情況下再次盜竊的,因為可以累計評價,符合“多次盜竊”的要件,依法應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而在行為人實施的前兩次盜竊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情況下,如果前兩次盜竊行為不納入可累計的范疇,行為人受到的至多是三次行政處罰。這將推導出“同樣是多次盜竊行為,法律對主觀惡性大的行為的懲處反而輕于主觀惡性小的行為”這一荒謬的結論。因此,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從罪行相適應的角度出發,應將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納入累計評價的范疇。
二是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將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納入累計評價的范疇,所涉及的是對這種“多次盜竊”行為究竟是違法還是犯罪的法律評價。因此,在評價時,更應結合犯罪構成理論從行為的主觀惡性、危害程度、造成損失等多方面進行考量,至于先前的行為是否應納入累計評價范疇,則不應作為主要考量因素。因為,這完全可以在量刑中作出適當處理,避免重復評價。在多次盜竊案件中,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3條的規定,若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是被處以行政拘留15日并罰款200元。如果根據該行為人后續的盜竊行為,累計計算,已達三次,構成盜竊罪的,在實踐操作中,完全可以通過科以刑罰后,對之前已經受到的行政拘留進行折抵,拘留一日折抵一日,對之前的罰款進行等值減除,通過該種方式,避免重復評價。
三是具有類似的法律規定可作法理依據。《刑法》第153條第1款規定:“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較大或者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后又走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從上述條文看出,普通走私要求數額達到較大標準才夠罪,但如果一年內走私兩次且已經被行政處罰,之后第三次又有走私行為的,雖然第三次走私單獨來看并不構成犯罪(不達數額較大標準),但結合之前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兩次違法行為,依然將該種行為入罪科以刑罰。因此,筆者認為,雖然《刑法》并沒有在盜竊罪的規定中作出類似的規定,但上述規定所反映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完全可以適用于盜竊罪的規定中。
四是避免實際操作中的諸多執法尷尬。如果將已經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排除出“多次盜竊”,則可能會導致不合理的現象:對于每次盜竊(非特殊盜竊)均未達數額較大標準的慣犯而言,司法機關無法以“多次盜竊”追究其刑事責任;如公安機關欲追究其刑事責任,避免“抓了放、放了抓”的惡性循環,則只能在發現其兩次盜竊后均不予任何處罰并直接釋放,之后長期監控,等待其第三次實施盜竊;對于盜竊者而言,甚至可通過主動到案尋求行政處罰的方式,避免被科以刑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