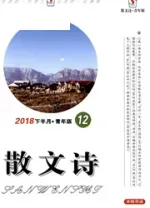關于散文詩
高博涵
一,“影響的焦慮”——如何為散文詩正名
散文詩由西方波德萊爾等詩人初探,到傳人中國融入漢語文學,其間已有上百年的歷程。但作為一個由詩歌和散文嫁接而生的文體,其獨特的抒情方式依然得不到正名,許多人仍重復著古老的論題:散文詩到底是散文還是詩?或許用“散文詩”這個組合型詞語來命名這一文體。本身就攜帶著揮不去的“影響的焦慮”,散文詩仿佛即是散文與詩歌結合的產物。的確,散文詩不分行的抒寫格式形同散文,而其文字呈現的情感化、心靈化,又分明是詩歌擅長的領域。夾在早已成熟的兩種文體之間,散文詩的處境看起來相當尷尬,它不僅需要再出生之后摸索性的成長,還要時刻注意排除散文與詩歌帶給其的焦慮感——它必須不斷地證偽,擺脫散文和詩歌自娘胎里帶給它的影響。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因為剛剛成長起來的散文詩看起來與相當成熟的散文、詩歌并不能抗衡。
雖然散文詩與散文、詩歌之間有著剪不斷的血緣關系,但一味投身于證偽的過程又分明是一種買櫝還珠的行為。一個新文體的誕生必然有其誕生的理由和獨特性,與其不斷辯駁于散文詩不是詩或是散文詩不是散文的泥淖中,不如還其本源,發掘屬于散文詩的獨特性到底在哪里——至少試著減少其他文體的參照,或是在參照對比中逐漸發覺散文詩自身的特性,而使其以自已獨立的屬性存在。即便散文詩吸收了散文與詩歌的特征,它也絕非散文+詩歌的物理量化,而必然是一場改變文體性質的化學革命。
散文詩的獨特性是什么?我以為,是以情緒之流貫穿全文的抒寫性靈之作。散文詩不是散文,紀實性的文字并不包含其中,敘述性話語更不必存在。它所記載的是高度純粹化的心靈體悟、思想的波浪,所倚存的描寫背景也僅是一個鋪墊或是一種象征,并不具備實際意義。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魯迅的《野草》便是例證,魯迅所勾勒的許多場景都縣有虛幻色彩,或是在無物之陣中上下求索,或是在夢境之中體瞇甘苦,即便貌似寫實之作,也具有高度象征色彩(例如《風箏》實際上是魯迅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相悖逆時刻靈魂的寫照,當然這里僅就象征意義而言,其行又模式并不屬于真正的散文詩)。散文詩必須是一種玄幻之思,否則它與散文的邊界則變得模糊——那些真實可感的日常生活寫照完全可以讓位于散文,不同的文體各司其職。試想在散文詩出現之前,有許多心靈式體悟僅能附著于紀實性散文之末,隨著現代人個體意識的逐漸加重,必然會出現專一性心靈言說的文體,這一文體即成為散文詩。
同時。散文詩具有一股強大的情緒之流,這種流向統貫全文,使得整篇史章具有一股流動的血脈,清晰可辨。我以為這即是它與傳統詩歌的區別,詩歌的分行預示著詩歌文體的跳躍性。如果喪失了這種跳躍。詩歌的興味便全無,讀者需要做的便是將這種跳躍系連起來,完成一場閱讀。但散文詩則恰恰相反。所渴求的是文章整體的貫通,一種鱗次櫛比紛紛墜墜又銜接自然的文句表達模式。激情式文字適合這樣的義體,作者的情緒可一貫而下,毫無阻障;玄思式文字也同樣適合這樣的文體。抽絲剝繭的恩路一點一點延展。似一種理性的推導,又到底深情款款,絕無生硬之嫌。
散文詩的出現是現代文體發展的必然,使得文體的界域愈發分明,也增加了各類文體的純凈度。有了散文詩,心靈化的文字找到了柄止的理想場所,強烈情緒之流的作品,也不必在注重跳躍性的詩歌之間苦苦尋找自己的位置。隨著文學現代化的不斷增進,人類情感思維的廣度將不斷延伸,新增的文體即能承載下更新的思維與表達模式,使得每一種向度的文字能各安其位,有所成就。
二、作為舶來品的散文詩
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即是散文詩這一文體并非自然生發于中國文學之中,而是西方的舶來品。當然,每一件事物能在當地生根發芽,其土壤必然是渴求這一種子的。散文詩走進中國文學亦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需要——隨著文學革命的號召響起,白話文成為中國文學發展不可阻擋的趨勢,人們急切期待著心中所想與文中所寫完全契臺、多年壓抑的情緒之流也待于文字之中傾然噴薄——那么。散文詩這一文體恰恰滿足了當時作家的需要。散文詩自然是以自話口語承載情感,同時又具備鮮明的情緒流向,自然極受當時作家的歡迎。當時的作家渚如劉延陵、冰心、郭沫若等無不多有這樣的嘗試,就連詩歌創作其實也是散文詩化韻,胡適、周作人等人初期嘗試的詩歌,冰心、宗白華等人所寫小詩,某種程度上僅只是分了行的散文詩而已,并不真正具備詩歌的特征,與其說五四時期的詩歌創作偏重散文化,不如說是偏重散文詩化,因白話文學初被嘗試,激情式或玄思式的情緒之流最多見,最適合產生散文詩這樣的文體。
但激情式的破壞僅只是一時之快。文學的建設仍要在漫長的時光中不斷摸索前行。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仍然深重地影響著現代文學的創作,不能不提起我們高度的重視。中國文學自來便以詩為中心,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詩歌注重抒情性而相對忽略敘述性,這就導致了中國詩歌雖自古發源但卻缺乏強于敘述之流的民族史詩,而多是一種吟詠喟嘆,或是詩意的生活場景寫照。中西詩歌走向的不同或許取決子中西文字狀態的不同,有關這一問題可參考林庚先生的相關論述。在林庚看來,中國方塊字的特征使得文字創作之初十分困難,于是很難跟上敘述思維的發展進程,于是只能以一種意象的狀態來呈現、暗示。所以多出抒情性作品而較少敘述類文學。日后中國文字雖在緩慢發展過程中得以壯大成熟,但其文學表達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再難轉變,這便造就了中國詩學以意象、象征、星現為中心的詩文化傳統。這種傳統顯然是與西方文學相對立的。西方文學因其字母拼寫的便利,自古便可與思維發展同步進行,文字也就更多敘述特征,民族史詩也自然是其必然的發展結果。
這里產生了一個問題——西方詩歌強太的敘述特征使得玄思式詩歌得以有效發展,而當這一情緒之流過于噴薄。打破分行的模式走人散文詩的自由場域也似乎是順其自然的行為了。但對于中國詩歌來講,其強大的呈現性仍然揮之不去,詩行的斷續性特征也格外明顯,即便受到白話文的沖擊,詩文逐漸西化,其連續性的情緒之流恐怕還不曾達到需要沖破分行的模式轉向散文詩的強度。于是,我們現今所看到的散文詩,可能更多的仍是一種詩歌跳躍性思維,注重平行意象的呈現、注重情景交融的意境。而近乎缺失連貫的情緒之流,或是又完全走向對立面,告別“詩”的空間成為平庸的散文紀實。也許,在五四時期情緒之流的噴薄過后,我們尚需要較為冷靜地思考——作為舶來品的散文詩,我們如何將之真正載入中圄文學的土壤,使其特性閃光,而不是飽受“影響的焦慮”。
三、當今散文詩所應注意的問題
我認為散文詩在發展過程中所應注意的問題有三。
其一,應避免紀實性語句人散文詩。在我看來,散文的敘述特征是散文詩強大的宿敵,甚過詩歌跳躍性對散文詩的干擾。因為紀實容易作詩難。散文詩篇幅長于詩歌,大量敘述性話語涌入散文詩文本,造成散文詩純度的降低。散文詩閱讀一本是給予人們心靈的美感體驗,流于瑣碎的記錄只能使得散文詩這一寶貴的特征被泯滅。
其二,應多些智性思考空間。散文詩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感性的情緒之流,一種是理性的思索。但理性的思索絕非哲學語句的直接表達,而是借助思緒之流帶動契合思索的活語呈現。并且該話語還應具有優美的特征。觀今的散文詩更多是感情的抒發,而較少思緒的流轉,若能發掘這一方面的作品,使得溫潤柔軟的文字能加以剛性的成分,剛柔并濟的味道一定更美。
其三,辭藻應為情緒之流服務。我并不認為堆疊意象的散文詩流于空浮,只要文本內容契含情緒流動。毫無不必要的炫技,這些辭藻的使用便也具有錦上添花的妙處。但單純羅列辭藻,使意象脫離于情緒之流,無一以貫之的思緒帶動。這些辭藻便只能顯得華而不實,甚至有過于繁瑣之感了。
如何把握得恰到好處——我感覺散文詩創作仍是要以情緒之流為基本依憑,情緒流向哪里,便相應帶動起哪些辭藻——它們自會恰到好處地貼合作者剎那的情感體悟而又不會旁逸。一句話,散文詩的情緒之流是最為重要的東西,把握好它,就可把握好整章散文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