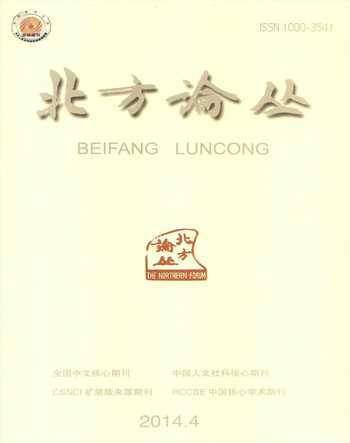明代關中曲家的雄峻之氣與復古格調
汪超
[摘要]嘉靖文壇逐漸彌漫復古格調,戲曲領域則呈現出承前啟后的特性,康海、王九思等關中文士,伴隨南北取士的時代背景,身兼復古流派的前七子成員和曲家的雙重身份,立足文統體系展開曲論探究,折射出北方文人的典型戲曲觀念,既浸染關中地區的雄峻之氣,又流露出其時盛行的復古痕跡,無論文壇和曲壇都皆有別樣風格,是解讀嘉隆曲壇不可或缺的關鍵內容。
[關鍵詞]明代;關中曲家;康海;王九思
[中圖分類號]I207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4-0074-05
嘉靖時期的文壇逐漸彌漫復古格調,對于古學的復興與呼喚,成為諸多文士尤其是前七子的重要聲音,同時渴求當下真詩的創作,倡言“真詩在民間”的論調,體現出此時文統體系復古觀念的特質。在此文壇復古思潮的籠罩下,戲曲領域則呈現出承前啟后的特性,身居關中地區的康海、王九思,作為復古流派前七子的主要成員,同時又積極參與戲曲領域的活動,介乎文統背景展開曲論探究,折射出北方文人的典型戲曲觀念。
一、南北之別:康海等關中曲家介入曲壇的時代背景
康海、王九思等關中士子涉足曲壇領域,時值科舉功名天下之際,介入戲曲或多或少帶有業余的意味,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決定其戲曲觀念的闡發,難免受到詩文正統思維的波及影響,康海、王九思等人努力詩文復古思潮的倡舉,同時也折射出戲曲觀念的演繹。審視康海、王九思的戲曲觀念,不得不先正視梳理他們的復古思想,并回歸至他們介入文壇的背景探尋,其中南北科考導致南北士子觀念的差異,是為其間考察審視的重要關節:其一,康海等北方士子復古觀念的闡發,將目光溯源至引以為豪的漢唐時代,凝聚成較為濃郁的地域情結;其二,康海等北方士子所稟賦的關中習氣,試圖以剛勁質樸之氣改變當時文壇的柔弱文風,扭轉彌補臺閣體,以及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的不足之處。此外,康海針對南北曲差異的詳細論述,身居其間所感受的獨特時代背景,也是促成理論闡述的關鍵因素。
明初朱元璋建立漢族政權,為文人提供更多實現價值的機會。此時的文人群體一方面努力運籌于政治權利之間;另一方面,又活躍于文壇領域。其間,雙重身份的交叉互動,影響文學思想的闡發,換言之,他們文學思想觀念的表態,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如較為突出的南北之爭問題,滲透當時的詩文理論批評,也波及文人戲曲觀念的演繹。
文人群體無論是躋身國家的權力機關,還是步入文壇的中心領域,科考都是較為關鍵的環節,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進入朝廷,進入翰林院,甚至內閣而為朝廷重臣,身份的變化直接導致影響力的大小,文學思想的闡發才能得到認同,并且受到文學才俊的追隨效仿,終而成就當時一定影響力的文人群體,如明初的“臺閣體”領袖人物的楊士奇等,都是先后官至大學士,特殊的身份直接導致當時朝廷文人官僚的追捧,形成明代前期雍容華貴的突出風氣。考察明代前中期的科舉考試及其所帶來文壇風氣的多樣現象,是探索考察此時曲壇現象的關鍵視角。
討論明代的科舉考試,就無法回避最為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又稱“春夏榜案”。針對這次科舉考案,朱元璋采取較為極端的處理方式,犧牲南方士子的集體利益,主要從政治平衡的角度出發,籠絡北方士子的支持和擁護,以便更快消滅前元的殘余勢力,實現南北經濟文化的均衡,從而穩固朝廷的統治。南北取士科舉的地域名額分配,不僅只是文化層面的問題,而且涉及政治統治的需要,同時也為后來南北士人的爭議埋下伏筆:“明代科舉分卷制度的實行,客觀上起到了穩定政局的作用,體現了協調、優待和兼顧邊疆與經濟文化落后地區的政策性支持,有利于調動和激發落后地區讀書向學風氣的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提升,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協調發展”[1](p.165)。
南北榜科舉對于明代政治文化的推動,促進明代士子群體呈現出地域性特征,同時轉變為政治性群體,再變而為文學性群體。科舉考試即已成形的南北地域因素,導致朝廷政權的具體運作,在所難免出現南北分歧,也即究竟任命何方文人進入館閣的現象。如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年)的會試:“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2](p.4683)。明英宗朱祁鎮交代李賢盡量挑選北方文人,南方文人如果能有像彭時那樣風度的方可錄用,結果當年所取15名庶吉士當中,北人共有9個名額,占據上風并得以機會進入館閣,從而把握政治文化的權柄,如李賢的河南老鄉劉健也在其列,他在弘治年間官至內閣首輔,其時前七子的凸顯就與他密切關聯。而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也都是依據核心人物的地域牽連,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文學性群體,由此可見,南北科考所推動的連環效應及政治對文化領域的影響。
總之,明初確立分南北取士的政策,直接關系明代南北文人地位的變化,不僅體現于政治權利的爭奪,而且波及文學思想的論辯,審視明代文人文學思想的闡發,南北科考凝聚成的地緣情結,推動文人群體的逐漸形成,并由地域性群體轉變為政治性群體,再變而為文學性群體,康海、王九思文學觀念的闡發,就附著濃郁的北方士子的關中色彩,對于秦漢文學繁榮的推崇,對于勁健質樸風氣的植入,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西北雄峻之氣”:康海等曲家振弊文壇的內在情結
以上論述明代科考的地域色彩,或明或暗地推動影響明代文壇的分布格局,胡應麟《詩藪》也有較為客觀的論述: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子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后,復自北而南矣。[3](p.341)
胡應麟細數明代文人地域歸屬的演變,大致呈現出南—北—南的轉變情況。弘治之后,由于南北科榜的推動,北方文人逐漸進入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時成為引領文化大旗的重要力量,并推動復古格調的倡舉興盛,只是分歧于究竟復何時之古,其間不論是復秦漢文化、唐宋文化、南朝文化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倡舉者地域身份因素的影響。究弘治、正德年間的前七子中,李夢陽為甘肅慶城縣人,康海為陜西武功縣人,王九思為陜西鄠縣人,他們三人都屬關中地區,可謂漢唐興盛之地。其余何景明為河南信陽人,王廷相為山西潞州人,邊貢為山東歷城人,他們復古論調中恢復漢唐盛世,多少包含有弘揚地域文化的意味。弘治十五年(1502年)康海、何景明、王廷相三人得中進士,尤其是康海的策論為孝宗皇帝賞識,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為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睹焉。[4](p.341)
孝宗皇帝等給予康海最高的稱賞,也促成他們強烈的自豪感,并轉為內心的使命感,而源出他們成長的地域文化血緣,逐漸內化為文化政策的血液,重舉漢族文化的中興旗幟,恢復漢唐時期的恢宏氣象,便成為自上而下認可的方向,也是轉化為復古格調的動力所在,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曰:
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于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峻之氣,當時文體為之一變。[5](p.208)
何良俊將康海、李夢陽二人相提并論,指出二人改變文氣的重要作用,康海作為關中地區的青年才俊,順利通過科舉考試,并且得到皇帝權臣的賞識,以其浩然蓬勃之氣進入較為凝重雍容的館閣,與李夢陽等人一拍即合,試圖改變其所認為的靡弱之氣,康海為王九思所作《渼陂先生集序》云:
明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景明、戶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榖、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于諸公之間。
康海認為,明初直至弘治時期的文章方至興盛,并不滿之前文章的“古俗”與“流靡”者,故而直取自身稟賦與高揚蹈舉的“關中習氣”,《隋書·文學傳序》:“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6](p.1730)康海等明代文人亦云:“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有古之道焉。”[7]李開先在《涇野先生傳》中評價呂柟:“鐘以關中風氣,渾厚雄偉,剛毅奮強,而直氣將塞乎天地,富貴焉得以淫之,貧賤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8](p.739)北方文士都有對關中風氣的清晰認識。
同時,康海等關中曲家“西北雄峻之氣”的高調抒嘆,極具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康海步入文壇之時的文風之陋,大約所指臺閣體和性氣詩而言,當時文章風氣偏于柔弱的現狀,正是他們所要直面振起的難題,復古格調的形成不僅源于內在的血緣精神,還有外在文壇發展現狀的現實針對,康海倡舉司馬遷的文章,李夢陽宗法杜甫的詩歌,打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旗幟,以及剛健質樸的秦漢文風,無疑是一方救弊的良藥,有著極強的地域色彩和文壇針對性。康海文章創作理論的闡發,針對文壇現實的弱弊,將古今之文進行比照參議,為當時文壇注入新鮮血液,其《文說》云:
古之文也充之而后然,故其師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后思,故其敝也渙而晦焉。充之有道,窮理博文而已。理不窮則無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博則無以盡其法度之所宜。故窮理博文而約之于禮,然后可以言其文也。
康海認為,古文的突出價值在于內容形式的充實,所謂為文之道就在“理窮”、“文博”,追求內在的旨趣與外在法度,都能實現較為完滿的詮釋,而這些恰是“今之文”的不足之處。不僅如此,康海還認為,文章需要有益,張治道評述康海時說:“對山論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出于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人國,乃為可貴。”[9]在文章旨趣方面進行明確強化,為文需要回歸于“道”,這與此時文人普遍推崇的歐陽修論述一致,將“道”具體到關心國家百姓,這樣的文章才能充沛厚重,不至于流連于臺閣宮廷,過于關注局部生活的描寫,從而將文章推向更寬闊的境地。
正如張治道所評議的,康海致力于糾正當時文風之弊,在強調“理”的同時,重視“氣”,依據西北質樸淳厚的地域秉性,同時還建立于秦漢時期的傳統習氣,無疑都是用來糾正柔弱文氣的一劑良藥。所以,在康海等西北文人那里,無論是理論主張,還是創作實踐,都立足于陽剛之氣的重振,而從實際所體現的效應來看,也得到當時文人的認可,對于當時文壇風氣的扭轉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王世懋《康對山集序》云:“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文靡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10]王世懋也指出李東陽主盟文壇時的不足,認為康海秉承秦漢風氣,以此扭轉文壇的靡弱文風,這也可以說是當時復古風氣之下,康海等西北之士從兩個層面的展開,不僅致力從內容的“理”,而且還立足于風格的“氣”,從兩方面改變扭轉當時文壇的創作傾向。
康海這樣的復古思路同樣體現在詩歌方面,致力于詩歌復古思想的闡發,也大約從“理”與“氣”兩個角度,體現出如出一轍的復古基調,康海對于古今詩人的評價來看,認為“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略停畜于內,滂沛洋溢郁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模仿剽奪遠于事實者萬萬不同也”[11]。歷數古今詩人當中,唯獨稱許曹植、杜甫、李白,無論是在“經濟之略”的理,還是在“滂沛洋溢”之氣,可謂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這是當時文壇的所謂模仿者所未能比附的,是對此前復古思路的某種否定。
康海振古格調的闡發與豪邁的“雄峻之氣”的抒嘆,同樣踐履于他們的戲曲創作,如康海的《中山狼》《沜東樂府》,王九思的《碧山樂府》都可尋見。康海戲曲創作風格被何良俊評為“跌宕”,王驥德則評為“粗豪”,近代學者任訥《沜東樂府補遺跋》曰:“明初散曲,大抵為端謹一派,元氣漸離。至康氏始一意豪放,較之元人,雖終覺氣度偏急,然要非昆腔以后之南曲可比者矣。”[12](p.56)諸家評議都聚焦曲風的音情頓挫和抑揚豪邁,提攝符合他們的西北雄峻之氣,有抒發英雄激越的豪情,如“流年算來三十七,折盡英雄氣。難收張禹頭,為就朱云義。死林侵醉模糊因甚的。”([清江引]《九日》之二)另外,《中山狼》描寫趙簡子獵狼的場景:“塵埃滾地,金鼓連天……紛紛車馬,對對旌旗,飛鷹走狗,千群萬隊。”又“[那咤令]只見那忽騰騰的進發,似風馳電刮。急嚷嚷的鬧喳,似雷轟炮打。撲剌剌的喊殺,似天崩地塌。須不是斗昆侖觸著天柱折,那里是戰蚩尤擺列著軒轅法,卻怎的走石飛沙?”通過一系列的疊詞渲染氣氛,一氣呵成,氣格豪邁。
康海評價王九思《題紫閣山人〈子美游春傳奇〉序》曰:“予讀之每終篇或潸然涕焉,曰:‘嗟乎,士守德抱業,謂可久遠于世以成名亮節也,如此乃不能當其才,故托而鳴焉,其激昂之氣若滲乎其毋已也,此其所感且何如哉,且何如哉。”明確表示出對于王九思曲作“激昂之氣”的欣賞:“夫抉精抽思,盡理極情者,激之所使也;從容徐舒,不迫不露者,安之所應也。故杞妻善哀,阮生善嘯,非異物也。情有所激,則聲隨而遷;事有所感,則性隨而決,其分然也”。王九思《杜甫游春》借助杜甫之口,澆筑自我胸中的塊壘,描寫游春經過既沒有元代雜劇情節關目的緊湊設計,也沒有明代初期雜劇重視熱鬧場景的渲染,而是突出杜甫游春之時的萬千感慨,完全借助唱詞來抒發杜甫內心世界的情感,同時也是王九思自我對當下的情志抒發。
三、詩曲同源:康、王戲曲觀念的復古痕跡
關中曲家康海、王九思復古旗幟的樹立,復古觀念的倡舉,有著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因素,精神與現實的互相刺激,導致前七子復古主張的呼喊,這又波及映射于他們戲曲觀念的闡發。康海戲曲活動的展開,除了表面的娛賞宴樂之外,其戲曲觀念的闡發則立足文統視角的切入,將戲曲納入文統體系,確認戲曲的正統地位和詩文品性,同樣折射出鮮明的復古論調。
康海作為正統文人的身份自居,經歷科舉與京城時期的輝煌,使其內心流露出較強的文人優越感,肯定戲曲與古詩一體的同時,也表達出與民間藝人的區別,有意識強化戲曲的文人化色彩,他在自題所作《沜東樂府》曰:
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余者,輒以酒淆聲妓隨之,往往因其聲以稽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甚少”。蓋沿襲之久,調以傳訛,而其辭又多出于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謬,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童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沜東樂府》。
康海對于當時樂府作品頗多不滿,其一,在于“調以傳訛”、“音節既乖”的現象;其二,在于文辭出于樂工市人之手,造成當時樂府作品水平不高,促使康海親自操刀捉刃,并將作品輯錄成《沜東樂府》,顯然康海的作為與朱權較為相似,有意識地區分文人作家與民間藝人,在某種程度上強化戲曲的文人化傾向,從另一個角度將戲曲納入正統詩文體系。同時,康海戲曲辨體觀念的闡發,基本圍繞“樂府”概念為核心展開,并延續至古詩體系進行論析,體現出戲曲思想的復古論調。這既要溯源至元末時期楊維楨等人的戲曲觀念影響,又要聯系當時文壇西北之士復古論調的倡舉,從而揭示康海等前七子戲曲觀念的階段性和時代性特征。
檢閱這一時期的文人戲曲總集,就可以發現所用的“樂府”稱名較為多見,如朱有燉《誠齋樂府》、夏文范《蓮湖樂府》、王九思《碧山樂府》、王磐《王西樓樂府》、康海《沜東樂府》、陳鐸《秋碧樂府》、楊慎《陶情樂府》等,其間收集的戲曲文體卻是多樣化,朱有燉《誠齋樂府》收錄的多是雜劇,而康海《沜東樂府》等則又是小令套曲皆有,可見僅從概念稱名而言,康海等文人還未形成較為清晰的共識。
元代文人關乎“曲”的指稱概念,“樂府”只是眾多概念的其一,就曲體的外在形態而言,大致傾向于小令的范疇,與“俚歌”相對應而言,“樂府”所指為文人雅士所作的小令,而“俚歌”則是對于民間流傳作品的鄙稱。不過,元代文人對于“樂府”有較為明晰的認識,鐘嗣成《錄鬼簿》有“有樂府”和“有所編傳奇”的界分,“方今”兼有“傳奇”、“樂府”的諸公也是明確交代。楊維楨針對“樂府”的認識,也同樣基于詩曲同源的基調。
士大夫以今樂成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王霄;蘊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余韻在焉。[13]
楊維楨針對當時曲家的批評,依據詞曲本源的核心觀點,將樂府文體納入古詩體系,在詩學體系下展開戲曲思想的闡述,并實踐風雅精神切入戲曲,從而也為康海等人將詩文理論的復古格調,納入戲曲文體的討論,提供可資借鑒的標本,正好與他們的復古思想不謀而合。所以,辨體命題的討論首先從曲詞范疇入手,以傳奇文體的文學性為突破口,將詞曲與古詩接續一統溯源正名,肯定他們風雅傳統的一致性,以及傳奇作品的文學性:“世恒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詩與曲始歧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14](p.44)康海認為,古曲與古詩同根同源,通過與古詩同源的溯流,將曲最終納入文體內部,確立獨立的文體價值和地位。基于文人審美趣味的立場,肯定曲與詩詞的共有因素——文學性和抒情性,辨體意識通常基于曲詞本位進行探索,但這一結果卻忽視戲曲與詩詞之間的文體界限,模糊忽略各文體之間的其他特性,從而導致戲曲的辨體意識存在片面性,這一點充分體現在當時曲壇的傳奇創作。
基于詩統體系之下的討論,詩歌作品常見的題材內容,如忠臣烈士、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都在樂府作品有所反映,起到感化人心的社會作用。康海為王九思作《碧山樂府》序:
“其才情之妙,可以超絕斯世矣……其聲雖托之近體,而其意則悠然與上下同流,宕而弗激,迫而弗怒,即古名言之士或已鮮也。詩人之詞以比興是優,故西方美人,托誦顯王。江蘺薜芷,喻言君子。讀其曲想其意,比之聲和之譜,可以逆知其所懷矣。”
同樣為曲正名,與詩詞具有同樣的諷喻功能,高度肯定“詩曲一體”的命題,同時還需注意的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潛意識當中,又與李夢陽“真詩在民間”的文學思想如出一轍,又體現出前七子復古觀念在戲曲文體的折射并所體現出的一致性。
康海針對南北曲風格的分析,同時滲透南北地域因素的影響,這一方面由于當時曲壇出現的客觀現狀,另一方面,源自康海獨特敏感的地域情結,才導致他能夠對此問題能夠透徹論析,其為自己所作《沜東樂府》序曰:
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為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為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
針對南北曲的討論并非康海獨家之論,這在后面何良俊等人也有涉及,南北文風的差異,以及曲風的不同,雖然一直以來客觀存在,但詩文復古思想所努力貫徹的地域情結,直接導致同樣能夠清晰認知南北曲風的特色,這是我們看待康海這一觀點不可忽視之處。
關中另一曲家王九思不僅與康海交往過密,而且也致力詞曲之道,他在正德六年(1511年)罷官次年歸鄉后,便常與康海往來潛心制曲并以唱和:“每相聚沜東、鄠杜間,挾聲伎酣飲……自比俳優,以寄其拂郁。”[2](p.7349)借助詞曲來排憂解悶,二人相與曲戲的情形,顧起倫進行較為細致的描述:
公嘗與余游關西形勢,不但山川,而人物尤偉。康王作社于鄠里,既工新詞,復擅音律,酷嗜聲伎。王每倡一詞,康自操琵琶度之,字不折嗓,音落檀槽,清嘯相答,為秦中士林風流之豪。[15](pp.1115-1116)
康、王二人將京城詩文唱和的風氣,轉折而至關中地區的詞曲和鳴,雖然他們在詩文方面闡述相近的復古主張,但在戲曲領域又有些微差異,康海是以狀元之才,以治國報君為己任,難免視詞曲為小道,文學作品為言志的載體,故其較為粗放;而王九思以才子名天下,寄情詞曲而能當行出之,更近于本色的專業曲家,對于戲曲的認識較為詳細。
王九思的曲論主要體現在為李開先所作《寶劍記后序》《碧山樂府·碧山續稿序》《碧山樂府自敘》等,以及散曲作品的只言片語,大致梳理發現其依舊未能擺脫文統體系的范疇,無法避免詩人的身份立場切入詞曲。王九思基于正統士大夫的立場,涉足戲曲文體的領域還是心存余悸,不免對于戲曲地位正名吶喊,努力推崇戲曲的地位,為此將目光聚焦先前的詩人文豪:“風情逸調,雖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謫仙、少陵之詩往往有艷曲焉”[16](p.996)。以李白、杜甫的事例,來消解旁人的疑惑,同時也是獲得自我的心安。晚年所作《〈碧山新稿〉自敘》云:“奉教以來,每有述作,輒加警惕,語雖未工,情則反諸正矣。”[16](p.997)與陸游晚年對于自己作詞行為的悔意不同,王九思則是強調符合傳統的雅正標準,將詞曲之道回歸正統,避免時人以為艷曲的誤解。從這個角度而言,此時的王九思等關中文人,受制于正統觀念的影響束縛,試圖將詞曲納入文統體系,提高確立文統內部的地位,并且從文體風格、內容題材、表現功能等多角度出發,賦予詞曲同樣的文體特質,充分體現強化內在的文學性。
王九思不僅創作散曲,而且填制傳奇戲曲,他的戲曲觀念傾向于戲曲的自身特性,重視戲曲的娛樂功能和抒情功能,其自作《碧山樂府·碧山續稿序》云:
“予為碧山樂府,沜東先生既序而刻諸木矣。四三年來,乃復有作,興之所至,或以片紙書之,已即棄去。一日,客有過予者,善為秦聲,乃取而歌焉。酒酣,予亦從而和之,其樂洋洋然,手舞足蹈,忘其身之貧而老且朽矣。于是復加詮次,繕寫成帙,用佐樽俎。”[16](p.996)
詳細描述與康海填曲娛樂的情狀,充分發揮出戲曲藝術的本色,體現出戲曲文體的抒情特性。
王九思還重視“托物以寄意”的關鍵內容,強調文學創作飽含的內蘊,對復古思想的闡述,指出不僅只是模仿杜甫詩歌的格律法度,而是領悟杜甫詩歌“情真”的精神,才能復古人文學的精髓。所以,王九思也將此賦予詞曲創作,肯定戲曲創作的興寄精神,其《與王德征書》云:“擬為傳奇,所以紓情暢志,終老而自樂之術也。”又《碧山樂府·碧山續稿序》云:“或興激而語謔,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順乎情性而已。”可見,王九思將戲曲納入文統范疇視為抒情性的文體,從《寶劍記》《浣紗記》等作品可以發現,體現出此時戲曲創作的基本特征,也即作為文學性的文體來看待,重在抒發作者自我的情感,與詩詞等文體在表現功能方面趨向一致。
康海、王九思等關中文士,身兼復古流派的前七子成員和曲家的雙重身份,他們對戲曲思想觀念的闡發,既流露出其時盛行的復古痕跡,又浸染關中地區的雄峻之氣,無論文壇和曲壇都注入別樣的風格,是解讀嘉隆曲壇不可或缺的關鍵內容。
[參考文獻]
[1]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考論[M].沈陽:沈陽出版社,2005.
[2][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七六·列傳·第六十四·彭時[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清]黃宗羲.明文海:卷四三三[M].四庫全書本.
[5][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M].北京:中華書局,1993.
[6][唐]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7][明]康海.陜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C]//對山集卷四.四庫全書本.
[8][明]李開先.李開先全集[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9][明]康海.康對山先生集:卷一[M].續修四庫全書本.
[10][明]王世懋.康對山集序[C]//康對山先生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本.
[11][明]康海.韓汝慶集序[C]//康對山先生集:卷二七.續修四庫全書本.
[12]任訥.沜東樂府補遺[C]//散曲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31.
[13][元]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C]//東維子文集:卷一一.四部叢刊本.
[14][明]康海.沜東樂府序[C]//吳毓華.中國古代戲曲序跋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15][明]顧起倫.國雅品[C]//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16][明]王九思.碧山樂府[C]//謝伯陽.全明散曲.濟南:齊魯書社,1994.
(作者系安慶師范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