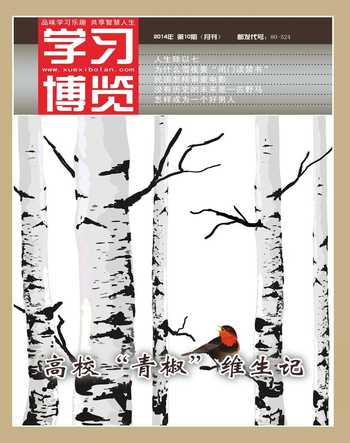直面體制有取舍
元年春
從1980年畢業至今的30多年里,他寫了36篇論文,翻譯了15本書,出版過17本著作,卻從未申請過任何課題——他就是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關于不申請課題的原因,他歸結為四點:第一,研究興趣和關注的問題與課題發布者的意圖對不上號。因為他從事的是“無用”的理論研究,但招標課題多數是要有“用處”的。第二,課題設定的時限太短。在三五年時間內,無法完成有分量的研究。第三,不符合自己的研究規律。做課題“不能跟隨靈感的即時閃現迅速轉移陣地,只能在一棵樹上吊死”。第四,不知道怎么填寫課題申請表,因為申請表要求填寫預期成果,無異于“搭建空中樓閣”。
2005年3月,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晏才宏去世,終年57歲。交大校園bbs上貼出上千篇悼文紀念他。據說,他上課已達到了這種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筆隨身,從不帶課本和教學參考書,知識早已爛熟于胸,例題信手拈來,講課條理清晰、自成體系。一道例題,他竟能接連給出20種解法。加上一手俊秀的板書,洪亮的嗓音,他的電路課被譽為“魔電”,幾乎場場爆滿,座無虛席。這樣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到死卻連副教授都沒有評上,因為他幾乎沒有發表過一篇“像樣”的學術論文。他花了大量時間為學生答疑、補習,堅持不為評職稱而拼湊論文。他說:“學生滿意我的課,比吃豬蹄還香。”
“上級考什么,下邊就干什么,行政權肆無忌憚地侵害教育權和學術權,攪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在離職演說中,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前院長徐斌如是說。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老師們非常反感。學校卻還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當天,徐斌是整個禮堂中唯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他反問:“人為什么要這樣假、這樣賤?”他從不申請任何獎項,因為“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他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分子永遠的價值追求。最終,徐斌“不和體制玩了”。他認為今后可以更加輕松愉快,就像“懷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2011年,趙躍宇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上任伊始,當著全校師生的面,他做出承諾:擔任校長期間不申報新課題、不新帶研究生。“不親自帶學生,是為了帶好全校所有的學生;不做課題,是為了全校的老師能夠做好課題。”這個“兩不”宣言讓他迅速走紅。他還要求學校里擔任管理崗位負責人的教授,不能享受學校的學術資源分配,“這樣才能保證全校學術分配的公平氛圍”。在趙躍宇心中,理想的大學是這樣的:學生能認認真真學習,教師能認認真真教書,管理人員認真為教師的“教”、學生的“學”做好服務工作。
尚春生曾以最高票當選蘭州大學首屆“我最喜愛的十大教師”。“他上課不帶片紙,四冊《古代漢語》爛熟于心,任意揮灑,絲毫無錯。”在學生眼中,他“在唐就是李白,在明就是李卓吾”。在教學初期,他曾撰寫教案,但發現教案會禁錮思想,于是放棄了照本宣科的教法。他說自己“胸中藏有一本永遠翻不壞的教案”。他不參加任何評比、評獎活動,不攜帶任何通訊工具,只是不想讓這些瑣事打亂自己的生活。他有獨特的學術見解,卻只發表過兩篇論文,因此直到退休還是一名講師。尚春生說:“我始終忘不了臨近下課時同學們那滿意的一瞥,那就是我這么多年教學的最大的動力。”做了一輩子“窮書生”,卻得到同學們的喜愛,他自認為“這輩子值了”。
2013年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諶洪果發微博宣布辭職。此前,他去香港中文大學開學術會議,在去機場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但他堅持前往。回校后,有關部門以他沒有遵守程序赴港開會為由,吊銷其港澳通行證。他多方求助無門,甚至起了“給領導下跪”的念頭。這念頭讓他感到“后怕”,害怕自己被體制化。諶洪果一直有意跟體制保持距離。2012年4月,他在網上公開自己不參評教授的決定,被網友戲稱為“終身副教授”。他擔心現行的評審體制會吞噬自己“殘存的”治學能力和獨立精神。當時,他還心存一絲樂觀,說“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里,我想我還是可以做一棵獨立挺拔的小樹的”。然而,風雨或許太猛烈,他最終只好選擇離開。
2012年5月,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副教授張江南在個人網站上發表《關于取消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的申請》。因為根據學校相關文件,由于申請的研究經費為零等原因,他被停止2012年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資格。盡管文件并未點名,但他心里清楚,文件表格上人文傳播學院一欄,“2011年無項目、無經費、無科研成果的”那個數據“1”,就是他自己。兩天后,他撰寫申請,請辭“碩導”。他承認規則面前無話可說,但否認他是個合格的老師則讓他備受羞辱。他認為,學術絕不能用項目經費做誘餌,用計件工資式的考核做羅網,把大學教師在學術和思想上應有的自由和道義擔當扼殺殆盡。有同事評價說:“學術賦予張江南力量,讓他敢于反抗。”
上海同濟大學哲學系主任柯小剛和夫人曾住在昆山鄉下的小公寓,閑來就在自家小院種菜。后來,他們搬到學校的筒子樓,沒有廚房,就吃食堂。每天早起打坐、畫畫,下午和晚上讀書、寫作。柯小剛還創辦“道里書院”,在網上做公益講座。后來書院被朋友注冊成公司,他堅持不做法人代表,也不占一分錢股份。工作十余年來,他沒有拿過一分錢的國家或省部級課題。他對所在單位不搞“唯課題論”深表感謝,“否則,我死慘了”。他會開中醫藥方,能給親友看病,但從不收錢。柯小剛不想做什么“公知”,因為太過“公共”會妨礙他思考政治和公共話題。相反,“冷靜旁觀和理性分析不是學術遠離政治的方式,而恰恰是參與政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