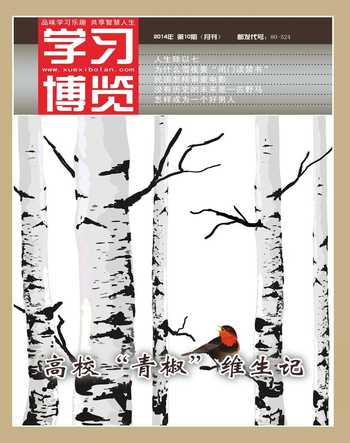揮之不去的懷鄉病
雪堂
如果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曾經是一種思潮,眼下它遠未退燒,相反,越來越多的“回鄉記”仍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之中,儼然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社會心理的流露。
《回鄉記:我們所看到的鄉土中國》一書的撰稿人群體是一批具有社會學背景的年輕人,曾經真切地在鄉村出生、成長起來,來到城市求學、生活,并且有過在故鄉之外的中國農村田野調查經歷,這些一直在觀察和思考今天“鄉土中國”問題的人,再次回到那些越來越陌生的中國鄉村,“家鄉”在一個疾馳的變革時代變成了自己的研究對象。
懷舊病人的集體鄉愁
由于是講述自己家鄉的情形,無論是對傳統還是對現狀,撰稿人復雜的情緒中往往更多的是批評和內省。當代中國的社會公眾評價有其極為特殊之處,即人們對變革并不見得有多大的真實歌頌,更多的是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疑慮;相反,他們對那些對傳統的頑強捍衛則從來不吝嗇自己的掌聲和帶有共鳴的嘆息。
書中所有撰稿人都是懷舊病人,無一例外對兒時鄉村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價值給予了高調的確認,對家鄉當下的問題和現狀則深表遺憾,提出無休止的質疑。出人意料的是,這些私人觀察和判斷,擇取的樣本容差同撰稿人本身的樣本容差同樣不足以支持其觀點的“回鄉記”,在網絡上公布后竟然獲得讀者的廣泛認同,引起了討論。最終整理結集成書,來到一個更廣闊的接受與言論環境。不能不說這反映了當代中國城鄉二元社會在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之下都郁積著某種深刻的焦慮。
天真爛漫的旁觀者
費孝通先生曾說:“任何對于中國問題的討論總難免流于空泛和偏執。空泛,因為中國具有這樣長的歷史和這樣廣的幅員,一切歸納出來的結論都有例外,但需要加以限度;偏執,因為當前的中國正在變遷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觀察都不易得到應有的分寸。”當我們用一個時間跨度提取出某個“中國問題”并最終找到答案時,你會發現那個問題早已經過一場變化,變得更復雜、更不可逆轉。當人們終于無法適應劇烈變革帶來的眩暈,“回鄉”不再僅僅是追尋記憶的物化存在,更像是一種文化尋根之旅,但就其實質來說,這種文化尋根的本能與訴諸“傳統”存在明顯的區別。
以《回鄉記》的撰稿人來說,他們顯然并非思想完全成熟的觀察者,有的甚至還比較天真爛漫,只是想回到從前。進一步說,他們回到家鄉后,更多的是成為整個鄉村原住民通過禮儀人情扼守傳統的旁觀者,是那樣一場自覺的集結在傳統之下的本能運動的訪問人。
然而,也正是從這批人之中,將來會誕生真正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運動對城鄉二元世界的改造”進行全面評價的人物,因為這是他們這代人真正的需求。而現下他們的觀察所得,不過是上一代人用傳統麻醉自己、掙扎求生存罷了。
回不去的“熟人鄉土”
在許多屬于“鄉土中國”的問題和困惑中,“鄉村公共品的困境”這個題目下的一組文章涉及農村社會轉型的細部,尤為引人注目。傳統的鄉土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微觀說是生產耕作時的互助,站遠一點說直接指向鄉村的公共生活,包括交通(修路)、灌溉(農業設施投入)、醫療(鄉村醫生)等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的供給,都要依賴內生的組織結合道德禮法來運作。一位撰稿人回顧了故鄉村莊當年引水灌溉中村民自發合作、互相提供公共服務的故事。從集體時期的公共“壟溝”,到近鄰幾家合資合作投入灌溉設施,直至私家購置的水泵、水管,灌溉作業從自發尋求鄉村公共服務到可以獨立完成的演變正是一個縮影。
今天農村的社會分化越來越大,純農戶所占比例減少,“農業生產合作幾乎無從談起。日常互動逐步減少了,社會關聯也日漸式微。”在市場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沖擊下,與鄉村衰落同時,鄉村公共服務的供給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經濟理性、私人觀念依仗著新技術的推廣,在鄉村微生態環境中完全驅逐了叫做“農業生產合作”的公共品,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憂。
一篇題為《村莊公共品供給的悖論》的文章,歸納了這種供給的悖論:村莊的基礎設施建設依賴于集體的“公共財政”能力;然而,當集體有了資金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的時候,村民小組們又期望把這些錢收入個人腰包,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村莊的平靜。
變革中的故鄉與人心
《回鄉記》文章的選錄頗具心思,對應的題目深度顯然超越原文:有日漸消散的“年味”和淡薄的鄉村人際關系,原先作為大家庭感情樞紐的長者逝去后,產生了所謂“核心家庭”和“喪家犬”情結久久揮之不去;有轉型時期農村治理與公共服務缺失的悖論;還有傳統傳宗接代觀念在時代沖擊下形成的新的代際關系,“城鄉分住”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今天城鄉關系的反映,新版的“城鎮剝奪農村”正在成為現實……都令人感受到一種賀雪峰教授所說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濃烈氣氛。
面對鄉土中國的急劇變遷,每一個有“故鄉”的人都會有自己的不適應,都會生發出自己的“鄉愁”。無論你現在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還是二者間的“擺渡客”,或者是進城不歸但內心深處仍然渴望獲得故鄉血緣和傳統安慰的新“城市人”,可能“談論”這些問題都顯得空泛,但記錄下這些一手的觀察絕對值得。這或許就是本書未來的歷史價值吧。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看出,所有圍繞著“回鄉”所不斷帶來的新的痛苦,都來自于變革。人,也確實有美化以往事物的不自覺。當下面對的這種,過去西方把它叫做“現代化的陣痛”,城市和鄉村都要經過這種必要的試煉。又或者,變的不是故鄉,而只是人心。痛苦只是源于“家”是中國人的精神圖騰。
(摘自《新京報·書評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