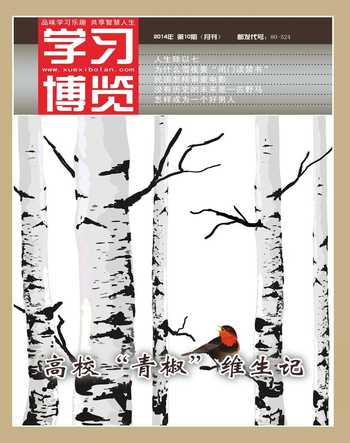直徑一米以見自然
劉華杰
“在大自然的經濟體系中,有多少強盜大亨,就有多少貿易聯盟;有多少私人企業家,就有多少團結經濟。”這并非單純來自倫理學的教導,也是來自大自然的基本事實。以自私的基因為抓手,鼓勵個體間、物種間惡斗,終究是邪說。
修習自然科學的學生以及普通人怎樣才能最好地了解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進化的精致以及掌握生態學的基本原則?
所謂最好,當然是相對的,包括較快速地、不太失真地了解。在一所不算太差的大學聽一門生態學課程,應當是高效、靠譜的事。通常,這樣做是對的,但是這未必是唯一的選項,也難能說是最好的,因為在教室里了解大自然總是缺少直觀性,聽眾無法發動自己的動物感受能力,與其他物種平等相處,切身體會大自然的復雜關聯性、整體性。
美國生物學家哈斯凱爾采取了并不特別驚人但絕對與眾不同的一種辦法。他像懷特和利奧波德等博物學先驅一樣,將目光聚焦于一個較小的區域,主要通過肉眼和身體,持續觀察、感受他的“小世界”,并把觀察、感受、思索寫成了暢銷書。他選擇的“樣方”只是一個直徑一米的圓形區域,位置在田納西州的一片老齡樹林中,他滿懷敬意地稱這塊小地方為“壇城”。
哈斯凱爾以日記體寫成了當代博物學名著《看不見的森林》,副標題為A Years Watch in Nature,即在大自然中進行一年的觀察。從1月1日寫到了12月31日。作者在“壇城”觀察并感受到鮮活的雪花、苔蘚、獐耳細辛、蝸牛、飛蛾、鳥、毒蛾毛蟲、螞蟻、蛞蝓等等,以生動的文筆和深刻的博物學、生態學、進化論的見解,闡述了生命的驚人多樣性、精致性,特別強調了大自然中各物種之間的普遍共性關系。書中幾乎每一小節,都有亮點,都令我產生共鳴。實際上,我本人也有這樣的想法:在地圖上打骰子,隨機選擇一小塊地方,對它持續觀察,寫一本自然筆記!
進化生物學是作者的思想利器和無盡的科學數據來源,但博物情懷顯得更為重要。當今,進化論武裝起來的博物學,試圖汲取現代各門分科之學的營養,以自己的原則對其加以組織運用,更精確、更自然地理解整個世界。觀察、記錄、描述,以及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思索,是當代博物學實踐的基本手法。這類工作具有悠久的歷史,技術門檻從來不高,但要求獨特的心境和肯用來“浪費”的時間。在現代性的大潮中,人心惶惶,高效地追逐名利,迫使許多人不容易保持“赤子之心”,不愿意用時間感受身邊的大自然。大自然不是伙伴,不是感受的對象,而是設法利用、壓榨、污染的對象。因此,到目前為止,真正能嘗試從事博物學的人仍然是少數,尤其是在中國。
哈斯凱爾的博物學觀察相當豐富,其解說令人振奮。讀后自然能夠感受到,我就不舉例評說了。他對經驗主義和當代科學的批評,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專門說幾句。
“我們生活在經驗主義的噩夢中:一個真實的世界,就存在于我們的知覺范圍之外。感官欺騙我們長達數千年。”(277頁)作者說,一個重要原因是尺度的差異。我們人類具有太龐大的身軀,感官過于遲鈍,而這使得我們對生命的多樣性、復雜性產生了錯誤的印象。“我們是裝點在生命表皮上的笨重飾品”,我們需要“用心”去感受、去發現動物、樹葉、雪花、塵埃、菌蓋,以及其他多得多的微小生命。“忘我”很難做到,但它是一種方法論手法,通過忘記我們的身份,拋棄我們的自大,便容易認識到生命世界的共生本性。“生命史上的重大轉變,大多是通過像植物與真菌這樣的協同合作來達成的。一切大型生物的細胞內部都棲居著共生細菌,不僅如此,就連這些生物的棲息地,也是經由共生關系促成,或是被這種關系改良的。”固然曾作為異端的連續內共生理論已經被普遍接受,甚至寫進了中學課本,但是只有像哈斯凱爾一樣,觀察一塊“壇城”,才能對共生獲得更深刻的感受。
用我們自己的感官觀察大自然,能夠更平衡地看待本來就存在的自私自利與合作共生,避免簡單地把一個還原為另一個。通常的弊病是,以為進化論科學教導我們或者向我們明白無誤地證明自私常有理。“在大自然的經濟體系中,有多少強盜大亨,就有多少貿易聯盟;有多少私人企業家,就有多少團結經濟。”(275頁)這并非單純來自倫理學的教導,也是來自大自然的基本事實。西方文化非常強調個體性,高揚個體、解放個體在一定歷史背景下固然有道理,但在自然體系中孤立個體終究不存在。以自私的基因為抓手,鼓勵個體間、物種間惡斗,終究是邪說。
博物學也強調經驗,并且鼓勵人們開發自己的新感性。狹隘的經驗論是有問題的,要時時提醒自己:經驗并非都靠得住,經驗也能誤導理性。但是,經驗不足,對世界的感受和理解便容易出問題,依據極有限經驗的模型便可能導向邪路。經驗不足在現代社會中往往以追尋客觀性為擋箭牌,這便觸及對當代自然科學局限性的批評。
“很不幸,有太多的時候,現代科學不能或者不愿去正視或體會其他動物的感受,‘客觀性的科學策略,無疑有助于我們對大自然取得部分的了解,并擺脫某些文化偏見。”“然而,分離的態度只是一種策略,目的在于打開局面,而不是要在全部活動中貫徹始終。科學的客觀性一方面推翻了某些假定,另一方面接納了另一些假定。這些假定披著學術嚴肅性的外衣,很可能促使我們在看待世界時產生自大和冷漠的心理。當我們將科學方法適用的有限范圍混同為世界的真實范圍,危險就降臨了。”(284頁)科學為了自身的目標,要化簡復雜的大自然,一瞥自然的某些側面。這樣做非常有效。但是這與世界就如科學化簡所描述的那樣運作,是完全兩回事。哈斯凱爾進一步指出,自然科學的自大精神,并非純粹學術使然,它“迎合了工業經濟的需求”。科學把世界簡化為機器,這一隱喻雖然十分有用,但它并不展示世界的全部。
“在這一年中,我極力放下科學工具,努力去傾聽,科學是何其豐富,它在范圍和精神上又是何其有限。很不幸,這類傾聽訓練,在正規的科學家培養方案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這種訓練的缺失,造就了科學中不必要的失敗。由于缺少這種訓練,我們的思想更為貧瘠,可能也蒙受了更多損失。”(285頁)神話、常識、科學都講述了若干故事,我們可以陶醉于故事中,但要分得清,不要“將故事誤當作世界明澈而妙不可言的本質”。
哈斯凱爾作為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的批評顯得更有瓦解性、可信性。當然,這不是號召放棄科學,只是提醒改進我們的科學。
(摘自《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