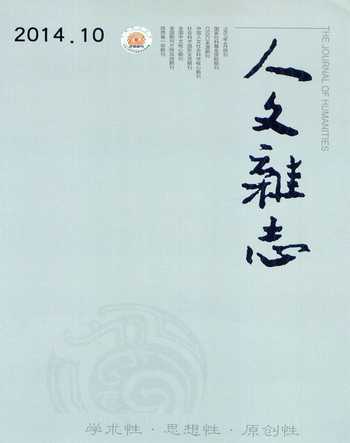論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
武道房
內容提要曾國藩是晚清理學經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學術思想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伴隨著他軍事上的成功,在清中葉漢宋之爭中一度陷于頹勢的宋學在晚清再度復興。這與他在吏治腐敗、帝國危機的背景下積極倡導宋學,以圖改良風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時,又大力主張漢宋調和,從而使漢宋學術長期對立的局面得以終結,促進漢宋調和成為晚清學術的主流。他以禮學會通漢宋,既堅守宋學的立身之道,又以禮學的經世精神吸納新知,為禮制改革以及西學的傳播創造了條件。曾國藩的學術努力,改變了既有的學術版圖,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曾國藩理學禮學歷史地位
〔中圖分類號〕K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10-0090-08
評價一個學者的歷史價值,不僅要回答他的學術是什么,還要回答他的學術為什么是這樣以及對后世的作用與影響。曾國藩的學術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在吏治腐敗、帝國危機的背景下復興宋學,試圖改良風俗,挽回道德人心,從而促成了晚清宋學的復興運動。他宗宋儒,同時又不廢漢學,主張漢宋調和,從而使漢宋學術長期對立的局面得以終結,促進漢宋調和成為晚清學術的主流。他以禮學會通漢宋,既堅守宋學的立身之道,又以禮學的經世精神吸納新知,為禮制改革以及西學的傳播創造了條件。總之,曾國藩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晚清學術的新路向,改變了既有的學術版圖,并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曾國藩學術思想促成了晚清理學的復興運動
乾嘉時期,理學在漢學的沖擊下,幾乎潰不成軍,宗宋學者廖不數人。道光時期的潘德輿曾說:
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潘德輿:《任東澗先生集序》,《養一齋集》卷18,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曾國藩的理學好友劉蓉也說:
為漢學者,阿世諧俗,漠然不知志節名義之可貴,學則吾學也,行則吾不知也。世亦遂無以行誼責之者,以謂彼特為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不當以道義相苛。泯泯棼棼,與世同濁,學術壞而人心風俗隨之。其為害有甚于良知頓悟之說猖狂而自恣者矣。劉蓉:《復郭意城舍人書》,《養晦堂集》卷8,清同治二年長沙刻本。
曾國藩于道光年間在京師與唐鑒、倭仁等人精研宋學,在當時全國熱衷漢學的學術環境中,是逆潮流而動的少數派。方宗誠指出:
嘉道間,海內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為為己之學兢兢焉。謹守程朱之正軌,體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則著之為事功,變則見之于節義,窮則發之于著述,踐之于內行。純一不雜,有守先待后之功者,聞見所及約有數人: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先生,官京師時,與師宗何文貞公、湘鄉曾文正公、羅平竇蘭泉侍御,日從善化唐確慎公講道問業,不逐時趨。其時在下位者,則有湘鄉羅羅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劉虞卿先生,俱無所師承,而砥節礪行,為窮理精義之學。方宗誠:《校刊何文貞公遺書序》,見何桂珍《何文貞公遺書》,光緒十年六安涂氏求我齋校刊本。
可見,道光末年,曾國藩以理學潛修之時,理學在全國并沒有多少市場;唐鑒等人的理學小團體也并不為人所注意。如果不是后來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成大功、暴大名,理學在晚清是否還能復興,也許是個疑問。梁啟超說:
乾、嘉以來,漢學家門戶之見極深,“宋學”二字,幾為大雅所不道,而漢學之支離破碎,實漸已惹起人心厭倦。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勵,其后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論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
熊十力也認為曾國藩的成功得益于宋學:
晚世為考據之業與托浮屠者,并狂詆宋儒,彼何所知于宋儒哉!唯宋儒于致用方面,實嫌欠缺。當時賢儒甚眾而莫救危亡,非無故也。乃至明季,船山亭林諸公崛起,皆紹述程朱而力求實用。諸公俱有民治思想,又深達治本。有立政之規模與條理,且皆出萬死一生以圖光復大業,志不遂而后著書。要之,皆能實行其思想者也,此足為宋儒干蠱矣。(顏習齋名為反對程朱,實則骨子里仍是程朱。所攻伐者,但是程朱派之流弊耳。)勝清道咸間,羅羅山、曾滌生、胡林翼諸氏,又皆宗主宋學,而足寧壹時之亂。……故由宋學演變觀之,浸浸上追孔氏,而求內圣外王之全體大用,不復孤窮性道矣。熊十力:《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十力語要》(1),新世紀萬有文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7~168頁。
熊十力指出,曾國藩宗宋學,但不孤窮性道,而是重視經世致用,能得內圣外王全體之大用。這說明曾國藩的理學是在宋儒基礎上有所發展的新理學。
理學是心性的學問,偏于內圣和修身。曾國藩通過理學的修養,養成了堅強的意志,勤儉的作風,血誠的性格,以及生死利害不動于心的殉道精神。世人正是通過這些,看出曾國藩之所以成功,來源于他的學術。如清末曾廉認為:
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錱、李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后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曾廉:《應詔上封事》,見楊家駱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2),臺灣鼎文書局,1973年印行,第449頁。
曾國藩的幕僚后來任湖廣總督的李翰章評價說:
曾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鑒、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禍福得喪窮通于度外。其大端則在以人事君,晉接士類,能決其人之賢否,推誠布公,不假權術,故人皆樂為之用。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見曾國藩著,李翰章編:《曾文正公全集·卷首》,民國廿一年(1932),掃印山房石印本,第25頁。
“曾門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亦認為,曾國藩之所以能立己立人,宏濟時艱,轉移一世之風俗,是因為講程朱正學之效:
曾國藩自通籍后,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鑒、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52頁。
薛福成的評價大體客觀。曾國藩在理學方面,不輕立說,并沒有什么多少講學文章或語錄,他只是一個對理學實有心得的實踐家。他為人為官與做事,有理學的氣象與精神,但通而不迂,大而能容,沒有前人講學之流弊。他是有心得又能躬行實踐的真道學,不同于歷史上常見的只炫弄理學教條而并無其實的假道學。
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打出“衛道”的旗幟,將“血性男子”和“抱道君子”吸引到自己的門下,使其幕府成為全國最大的人才基地。據羅爾綱的《湘軍兵志》統計,湘軍重要人物共182人,內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員以上者的達104人,占可考人數中的58%,其中僅進士、舉人出身者就達19人。羅爾綱:《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第56~65頁。他以理學經世的思想教育幕僚,培育人才,由他推薦、提攜成為封疆大吏的如李鴻章、左宗棠、李翰章、郭嵩燾、劉蓉、楊岳斌、李續宜、沈葆楨、劉長佑、劉坤一等一批總督或巡撫都有理學的背景。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初,亦是靠一批理學士子為骨干。羅澤南在湖南傳授理學多年,他的弟子在咸同時期多成為湘軍名將,如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溢澧等。這些人物也多以理學義理訓誡士兵,如王錱“常教士卒作字讀書,書聲瑯瑯,如家塾然。又時以義理反復訓諭,若慈父之訓其愛子,聽者至潸然淚下”。羅正鈞:《王錱年譜》,見梅英杰等編:《湘軍人物年譜》(1),岳麓書社,1987年,第59頁。曾國藩指出,羅澤南“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弟子也”。曾國藩:《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曾國藩全集·詩文》,岳麓書社,1995年,第305~306頁。
伴隨曾國藩軍事上的成功,清廷也認識到了理學對于保大清的作用,開始重用一大批理學人物。同治初年,倭仁被任命為大學士兼帝師,李棠階入軍機,李鴻藻為帝師兼尚書,吳廷棟官刑部。理學官員無論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勢力。據史革新的研究,就全國來說,活躍在咸同時期及光緒初期二三十年間各地主要理學士人,代表人物有70人,分布全國17個省份。且這些人多是朝廷或地方大員,其中身為大學士、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者,竟達15人,占統計總數的21%強。擔任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要職的就有倭仁、曾國藩、李棠階、李鴻藻、徐桐等五人。這是自康熙朝以來從未有過的情況。⑥史革新:《程朱理學與晚清“同治中興”》,《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在理學士人的努力下,清廷開始有意提高程朱理學的政治地位。1860年,清廷發布上諭,規定學人從祀文廟,“應以闡明圣學,傳授道統為斷”,對入祀文廟的人選標準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學的修改。是年,以明初理學家曹端從祀文廟,位列東廡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從祀。1870年“恩準”將清初理學名士張履祥從祀文廟,并重刊《楊園先生全集》。1875年將清初理學家陸世儀從祀文廟。1876年清初理學名臣張伯行、理學士人王建常被奏準從祀文廟;又允準把已故理學名儒李元春事實交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對健在的理學家也進行表彰,1868年褒獎安徽理學名士夏炘。1874年,陜西、山西兩學政分別給理學名儒賀瑞麟、楊樹椿、薛于瑛請授京銜。清政府以他們傳授“正學”有績,皆賜予國子監正銜。⑥
同治元年,清廷下令整頓翰林院:“自明年癸亥科起,新進士引見分別錄用后,教習庶吉士,務當課以實學,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關閩諸儒等書,隨時赴館,與庶吉士次第講求,辨別義利,期于精研力踐,總歸為己之學,其有余力及于詩古文詞者聽之。”《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52同治元年12月,大滿洲帝國國務院發行,大日本東京大藏書出版株式會社承印,1936年,第16頁。倭仁以大學士身份掌管翰林院后,即著手制訂翰林院新規,規定翰林士子必讀《朱子語類》、《朱子大全》等理學圖書。各地督撫在地方創辦書院,如上海龍門書院、陜西味經書院、四川尊經書院、湖北經心書院、江蘇南菁書院、廣州廣雅書院、武昌兩湖書院等,這些書院多請理學家主講習,課程設置均以經史、性理為主,以詩文詞為輔,順應了清廷尊崇理學的學術傾向。
在圖書出版方面,理學書籍在沉寂了近百年無人問津之后,再次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曾國藩創辦金陵書局,各地督撫隨即仿效,所出版經史圖書,以歷朝理學家著作為出版首選。如清初張伯行的《正誼堂全書》于同治八年由福州正誼書局刊印,是書編集宋、元、明、清理學家著作以及張氏自撰著作共66種200冊。除官方刊刻之外,一些地方理學士人也籌資刊印理學圖書。如陜西理學家賀瑞麟在講學之余刻印各朝理學書籍達百種以上。其所輯圖書被其門人后人匯編為《清麓叢書》,自同治至民國時期,陸續以“傳經堂”名義刊印歷朝理學著作多達153種。理學再次成為從官方到民間都很熱衷和時髦的學問。
在理學復興的沖擊下,漢學勢力一度出現頹勢。廣東學者陳澧感嘆說:
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澧前在江南,問陳石甫江南學人,答云無有。在浙江問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語或太過,然大略可知,蓋淺嘗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粵講漢學者,老輩惟勉翁在,在近年為俗事所擾。同輩中最篤學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讀注疏、《通鑒》為正功課,《皇清經解》、《五禮通考》為余功課,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陳澧:《東塾續集·與徐子遠書》,《東塾讀書記》(外一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41頁。
總之,晚清理學的復興,是同曾國藩的努力與影響分不開的。在一定程度上,曾國藩的確實現了他以一人之力轉移一世之風俗的人生理想。
二、曾國藩學術思想終結了清代漢宋學派長期對立的局面,促使漢宋調和成為晚清學界的共識
早在嘉道時期,伴隨社會矛盾和帝國危機的加深,漢學的“護法”阮元及考證學大師段玉裁等人就已有調和漢宋的傾向。稍后,黃式三沿繼戴震、凌廷堪、阮元等人學術路向,博綜群經,專治漢學,但并非認為“凡漢皆好”,而主張對漢宋學“各用所長,以補所短”,黃式三:《漢宋學辨》,《居儆集》“經說三”,光緒十四年刊本。但漢宋對立的根本狀況并沒有改變。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學立場的方東樹著《漢學商兌》反擊漢學家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漢宋學之間的巨大鴻溝一時難以填平。雖然已有一些學者如張成孫、毛岳生等在道光初年試圖調和漢宋學的矛盾,但只有到了曾國藩登上學術的舞臺時,情況才有很大的變化。
曾國藩標榜“一宗宋儒,不廢漢學”,他對當時互相嘲諷的漢宋學派都各打五十大板,聲稱“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⑤《致劉蓉》,《曾國藩全集·書信》(1),第8、6頁。他既批評漢學家不知他們的鉤研故訓手段實與朱子“即物求理”精神相符合,也批評宋學家蔑視漢學派的稽核之長,以致有空疏之譏。他肯定兩漢經師有傳經之功,“許、鄭亦能深博”,“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于用”,⑤但“言藝則漢師為勤,言道則宋師為大”。《送唐先生南歸序》,《曾國藩全集·詩文》,第167頁。他認為宋儒究群經要旨,然后博求萬物之理,能得孔學正軌,因此持堅定的宋學立場,但他并不排斥漢學,甚至反對宋學家孫鼎臣“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的偏激之論。《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55頁。曾國藩多次強調圣人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于義理之學。”《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他主張以宋學統攝漢學、經濟、辭章等其他學問。
由于曾國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影響力,漢宋調和的觀點很快在晚清為學人所普遍接受。如曾國藩的慕僚也是著名學者的李元度指出:“學術之途有四:義理也,經濟也,考證也,辭章也,是即三不朽之所從入也。”李元度:《送黃奎垣訓道常德序》,《天岳山館文鈔》卷31,光緒六年爽溪精舍刻本。李元度的說法其實是在重復曾國藩已說過的觀點。又如羅汝懷,他也是曾國藩的朋友,其所作《湖南文征》190卷,曾氏曾經為之作序。羅氏有“《與曾侍郎書》,娓娓千言,力辟漢學宋學名義之非,于門戶之見,豁然廓清,足救孫鼎臣《芻論》之偏。”④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29、435頁。南海朱次琦,乃康有為的老師,治學也不屑為門戶之爭,其要仍以義理為主。據其年譜記載,“嘗謂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然而攻之者忽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于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古之言異學者,畔之于道外;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于道中。果其修行讀書,蘄至于古之實學,無漢學、亦無宋學也”。④馮桂芬與曾國藩亦有學術上的切磋,他曾經邀曾國藩為其《校邠廬抗議》作序跋。馮桂芬指出:
漢學善言考據,宋學善言義理,亦各有所長。且漢儒何嘗諱言義理,宋儒何嘗盡改漢儒考據,漢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漢古而宋今,漢難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難,毋忽乎易,則學者之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調而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馮桂芬:《闕里致經堂記》,《顯志堂稿》卷3,1876年校邠廬刊本。
閩縣人陳濬在夏炘《景紫堂全書》作序時也說:
圣人之道,載于六經,遭秦火后,漢之諸儒掇拾煨燼,纂輯殘缺,殫勤于文字訓詁之間,雖微言大義,有未暇及,而使后儒得所考據以求圣人之間,功亦不細矣。有宋五子興,席漢儒之業,因經求道,超然獨契《太極》、《西銘》、《定性書》、《好學論》諸作,實能發前賢所未發。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于經訓尤殫精研思,條分縷析,無不根極于理要,圣道由是大明。見夏炘:《景紫堂全書》卷首,民國十年刻本。
夏氏《景紫堂全書》初刻于同治六年(1867年),陳濬此序大致應作于此時。但他的觀點其實是曾國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作的《送唐先生南歸序》中早已表達過的。
晚清不少治漢學的學者亦開始漢宋兼采,主張折衷漢宋。如嶺南漢學大師、學海堂山長陳澧,一生泛濫群籍,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及諸經子史,無不畢究。他的《東塾讀書記》有乾嘉諸師治學精嚴之風,但無乾嘉學派門戶之見,破漢宋之門戶,立論較為持平。他反對輕詆前賢:
自非圣人,孰能無誤。朱子雖大賢,其書有誤,后學固當商訂之。然商訂古人之書,必當辭氣和平,不可囂爭,不可詬厲,若毛西河所著《四書改錯》,不知《論語》朱注,“學”訓“效”,本于《廣雅》,而曰從來“學”字無此訓,則非朱子之錯,乃西河之錯也。陳澧:《樊昆吾先生論語注商序》,《東塾集》卷3,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陳澧這些話,早已是曾國藩發揮過的剩義。曾氏在《復夏教授書》以及其他文章中多次表示反對“輕詆前賢”的做法,主張“或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茍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并斥“西河駁斥謾罵,則真說經中之洪水猛獸矣”。曾國藩:《復夏教授書》,《曾國藩全集·書信》(5),第3467頁。
陳澧《東塾讀書記》又云:
自宋以來,學術迭變,固由風氣之轉移,亦由門戶之爭競,有爭競,故有興衰。然門戶之爭,總不出孔門之四科:德行,道學傳也;言語,文苑傳也;文學,儒林傳也;政事則大而將相,小而循吏傳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無,故孔子兼收而不偏廢,尤不交爭。爭則有勝負,有勝負則必偏廢,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陳澧:《朱子書》,《東塾讀書記》(外二種),三聯書店,1998年,第312頁。
《東塾讀書記》初名《學思錄》,作者陳澧于咸豐八年開始撰寫,同治十二年改名為《東塾讀書記》。上述所引陳澧這些觀點,曾國藩早在道光年間所寫的《書學案小識后》、道光二十三年給劉蓉的信以及同治八年寫成的《勸學篇示直隸士子》等文章中都有類似的表述。
張之洞學術上偏重漢學,但他也力主漢宋兩家各有其長,不可偏廢。他說:
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余一切學術亦不可廢。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張文襄公全集》卷213,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83冊,第15291頁。
在《輶軒語》中,張之洞又說,“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即是佳士,無論真漢學未嘗不窮理,真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張之洞:《輶軒語》,《張文襄公全集》卷204,第14692頁。
由是可見,晚清調和漢宋已成為學界的主流和共識。這種局面的出現,是與已居大位的曾國藩對知識界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分不開的。
三、曾國藩的禮學思想為洋務運動和西學的傳播提供了理論的支持
錢穆先生有言:“漢學派的精神在通經致用,宋學派的精神在明體達用,兩派學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經學上去求實用,去研究修齊治平的學問”,這是漢、宋兩派學者之共同精神。錢穆講,劉大洲記:《漢學與宋學》,《磐石雜志》1934年第7期。錢先生這句話應該是平情之論。且不論清代的漢學派,即就漢唐儒與宋明儒而言,學術致思的路徑是不一致的。漢唐儒重《五經》,意在經世致用;宋明儒重《四書》,雖也意在經世,但關注更多的是明體達用,向內轉。清儒有鑒于宋明儒之虛,主張回歸漢唐經學,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求一切經世致用的學問。所以,從顧炎武到江永、秦惠田,將經世的學問都統歸之于禮學。“禮”作為體國經野之學,涉及的范圍很大,從名物典章、人倫教化、天文地理、食貨水利、算術格致,到民間習俗、個人言行、生活規范,無不與禮有關。概言之,禮是萬事萬物的規范、制度和法則。所以相對而言,漢學家比宋學家更傾向于接受新知。早在鴉片戰爭之前,漢學家就開始注意研究科學,如天文、算學、地理、水利等學科。戴震通曉算法,著有《勾股割圓記》、《考工圖記》;阮元編輯《疇人傳》,為古代天文算學等科學家作傳,其中還介紹了西方科學。阮元開辦的書院還開設科學課程,在其《學海堂策問》中,他專門策試學生關于西洋歷法的來歷。著名的數學家李善蘭,也是從治漢學轉向數學研究的。李善蘭著有《則古昔齋算學》,于數學多有發明,并大量翻譯了西方數學及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后9卷)、《代微積拾級》、《談天》等。李善蘭的老師是專治《毛傳》的漢學家陳奐,而陳奐則先后師事過段玉裁和王念孫父子,是戴震一系中的學者。道咸年間的數學家如羅士琳(著有《四元玉鑒細草》、《籌人傳續編》)、項名達(著有《下學庵算學三種》)、徐有壬(著有《務民義齋算學〉七種)、戴煦(著有《對數簡法》及《續編》)、夏鸞翔(著有《洞方術圖解》、《致曲術》)、鄒伯奇(著有《格術補》、《乘方捷術》)等人都是出自漢學家隊伍。在邊疆地理學研究方面,何秋濤、張穆、陳澧、汪士鐸、洪鈞、楊守敬等人都有不少著作,這也是漢學派的一個成果。漢學家之所以與科學為近,是因為他們對一切學問都喜歡考鏡源流并具有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
當然,漢學家考禮更側重于人倫儀節,試圖以禮來促進社會教化。乾嘉時期的學者熱衰禮學,而排斥宋明儒的理學,禮學與理學之間存在鴻溝。嘉道之際,漢宋調和的苗頭漸顯,如阮元認為“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阮元:《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后》,《揅經室集·續三集》卷3,《四部叢刊》影印清道光本。阮氏試圖以禮學溝通漢宋。稍后黃式三對清代漢學家不講理,宋學家不講禮都作出了批評:“后世君子,外禮而內德性,所尊或入于虛無;去禮而濫問學,所道或流于支離。此未知崇禮之為要也。”黃式三:《崇禮說》,《儆居集》“經說一”。其意是說宋學家只講尊德性容易流入虛無;而漢學家只講考據,而不將學問落實成禮,則容易流入破碎支離。黃式三以禮學溝通漢宋的目的是很明顯的。
至曾國藩,以禮學會通漢宋才得以大暢厥旨。曾國藩的理學朋友孫鼎臣提到漢學便痛心疾首,認為太平天國的動亂就是因為漢學家的學問與道德人心無關造成的。孫鼎臣著有《芻論》,是講經世致用的書,其中論鹽政、漕運、兵制、幣制等。在曾國藩看來,孫鼎臣顯然并不懂得什么是漢學的真精神。他在為孫鼎臣《芻論》所作的序中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稿,夭鳥盅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在曾氏看來,漢學如顧炎武、江永、秦惠田等人的學術成果都是體國經野的禮學,這與孫鼎臣的《芻論》本質并無不同,因此曾氏認為“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56頁。所以曾國藩提出,“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圣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50頁。他主張以禮學“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復夏弢甫》,《曾國藩全集·書信》(2),第1576頁。在理學與禮學的關系上,曾國藩主張以理學尊德性,以禮學經世致用。他說:“蓋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禮”;《王船山遺書序》,《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78頁。“禮之精義,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書儀禮釋官后》,《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02頁。“禮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⑦《江寧府學記》,《曾國藩全集·詩文》,第338頁。理學家喜歡說仁說義,思考微眇玄虛的本體問題;漢學家喜歡考證制度層面的禮,而不喜言玄虛抽象的本體。曾國藩認為,應該取理學的內尊德性,取漢學的外道問學,這樣理與禮的關系便統一起來。
曾國藩的治國理想是通過制禮,使“人人納于軌范之中”,“人無不出于學,學無不衷于禮”。⑦也就是說律身治國都應該有章法,有規范,這樣才使理學家的道德落實到器物的層面。不僅如此,曾國藩具有“禮,時為大”的卓見。即是說制禮要因時制宜,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他說:“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復劉蓉》《曾國藩全集·書信》(10),第7034頁。所謂“三代制禮”之意便是“仁”。師其意不師其跡,這就為近代中國禮制改革拓開了空間。應該說曾國藩的禮學思想與乾嘉學者通過考證企圖在社會上恢復三代古禮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前者代表改革,后者代表復古和倒退。
在曾國藩的影響下,團結在他身邊的一批理學經世派,都有改革禮制、以禮治國的思想。曾國藩的弟子張裕釗頗得其師以禮經世之旨。他說:“若夫禮之于道天下也,宏遠矣。蓋處人之一身,耳目形體、飲食男女之事,推及乎天下國家、朝野上下,冠昏喪祭射御食饗之經,至于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未有一事而不由乎禮者也。”張裕釗批評漢宋學末流都不知以禮經世之義同時也批評宋學末流“耳目熟于心性之空言,而不識其余”。張氏認為,漢學末流雖然考禮,但又“咸鉤析一名一物,謬讬經訓,碎詞詭辭,而忘其為修身治世之要術也”。為此,張裕釗提出:“要其終極,而一惟禮之治,馴致其道,而徐俟其成。施之于一身,而身得其安焉;施之一家,而家得其序焉;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得其理焉。其居于上,則足以尊主庇民,更化矯俗;其居于下,亦不失為經明行修、明體達用之士。”張裕釗:《經心書院記》,張裕釗著,王達敏整理《張裕釗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0~452頁。劉蓉通過讀《儀禮》,深感禮能使人“各有遵循而不逾其矩,以是知圣王綱紀天下,所以范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B11劉蓉:《繹禮堂記》,《養晦堂文集》卷1。但他對古禮的態度也只是師其意,并不泥古。他很不屑于漢學家“較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賾,嗜奇綴瑣,以資證附”,B11于是擬在江永《禮書綱目》、秦惠田《五禮通考》的基礎上著《禮經發微》,取禮制大端,如祭祀、朝聘、燕饗、冠、婚、喪、鄉射之禮,據經援傳,目的是在抉發這些古禮形式背后的含義。只有弄清這些含義才能依據變化了的時代制定新禮以規范百姓。郭嵩燾著《禮記質疑》明確指出:“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則與時違矣,故時為大。”②郭嵩燾:《禮記質疑》,岳麓書社,1992年,第272、263頁。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禮順人情”的禮制改革思想:“人之生,生于味聲色之各有其情,故禮者治人情者也,非能遠人情以為禮者也。”②他主張國家應在順應民情的基礎上,變通與改革禮制。至清末,清政府試辦新政,令大臣提出意見,孫詒讓為盛宣懷代撰變法條議,匯成《周禮政要》一書,提出廢跪拜、除忌諱、裁冗官、革宮監、革吏役、改兵制、伸民權等改革內容。就見面禮而言,西方人行握手禮,中國人跪拜、作揖,禮儀不同,但背后都有恭敬的意思。但相對而言,握手有平等之意,跪拜卻象征尊卑秩序。就“內仁外禮”而言,禮可以變革,仁的意思不能變。由此思想延伸,譚嗣同著《仁學》以沖破封建禮教以及后來的“五四”激進派反禮教都是“禮順人情”、“內仁外禮”學術邏輯深層展開。激進派認為,傳統禮教已悖離“仁義”或“人情”,他們同樣是基于仁學或人情之理試圖建立全新的禮(制度和規范)。貌似與傳統悖離,其實精神實質并沒有脫離傳統。
當然,在曾國藩的禮學視野中,禮并不僅僅是人與人交往的儀節,所謂觀象授時、體國經野等自然、人文學科都在禮學的范圍之內。禮代表自然與人文的規范與秩序,這就是他所說的“修己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修己需要自律,這是禮;治人需要章法,這也是禮;“經緯萬匯”則遍涵自然與人文,按其規律和條理做事,也是禮。曾國藩有憾于秦惠田的《五禮通考》缺了食貨內容,于是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等六卷內容。他又感慨古禮殘缺沒有軍禮,于是手訂營制、營規,在他看來,這就是“軍禮”。他認為,禮是修己、治人、經世的學問,禮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因革。他的禮學是與理學溝通的;換言之,他的禮學要為理學的三綱五常服務。在此觀念下,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手辟洋務運動,團結一批研究科技的漢學家如徐壽、李善蘭、華蘅芳、徐建寅、舒高第、李鳳苞、趙元益、王振聲等人在江南制造局設翻譯館,與西方傳教士合作大量翻譯西方科技圖書,并首創近代史上的留學生運動,以期輸入西方的科技。在他看來,科技之類的西禮自然也是他禮學的一部分,他要用這些西禮為他的理學綱常服務。清季所謂“中體西用”思想,在曾國藩這里已經成形。
受曾國藩提攜而崛起的一批湘淮系朝廷或地方大員如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廣東巡撫)、劉蓉(陜西巡撫)、曾國荃(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劉長佑(兩廣總督)、劉坤一(兩江總督)、閻敬銘(山東巡撫)、沈葆楨(福建船政大臣)等人,都信奉曾氏禮學經世的思想,后來都變成堅定的洋務派,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堅力量。相反地,一些保守的理學士人如倭仁等人,只知祭起理學天理人欲的老調子,關注世道人心,但卻沒有曾國藩的禮學觀念,成為仇洋反西學的保守力量。因此,洋務運動與西學的傳播之所以能夠展開,除了列強的逼迫與中國被動接受原因外,在中國固有的思想中,還有一個內在的發展進化理路,清代的漢學與曾國藩的禮學為中國近代化運動的展開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支點。曾國藩以理為體,以禮為用,前者固守理學家的天理綱常觀念,成為后世保皇派的思想根據;后者則為后世維新和革命拓開了空間。發展到后來,禮學最終撐破理學內核,經世學人以西方政治思想質疑三綱五常,走向曾國藩“理學即禮學”愿望的反面。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黃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