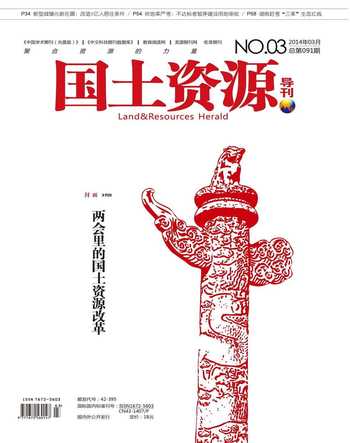中國經濟理性繁榮的內在邏輯
章玉貴
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有效增長,本質上并不取決于投資或出口驅動,而取決于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
從去年3月到今年3月,新一屆政府上任滿一年,若以數據衡量的經濟成績單,顯然不乏亮點。但在李克強總理看來,經濟增長向提質增效的軌道切換,才是諸多要務之首。
事實上,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在對體量巨大但問題纏身的宏觀經濟體系進行全面體檢,而從體檢結果來看,顯然無法令人樂觀,無論是積重難返的產能過剩問題,還是地方債和影子銀行風險,抑或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房地產調控,乃至國資改革等等,無一不是極為棘手的高難度命題。面對主要經濟體中產能過剩最嚴重的現狀,即便是再高明的經濟能手,恐怕無法做到手到病除。很難想象,一個經濟總量只占全球比重10%的國家,僅僅鋼鐵產能就超過全球產能的50%。而目前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船舶等五大產能過剩行業的總負債規模達到7.7萬億元。至于地方債和影子銀行風險,至少在目前看來,并未找到有效解決方案。幾乎占到中國經濟一年產出三分之一的地方債一旦危機全面爆發,由此觸發的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甚至比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危害更大。
正是由于看到了中國經濟日漸困難的發展生態,以及經濟轉型的緊迫性,最高決策層一年來日漸清晰的經濟發展路線圖表明:中國經濟在撥開高增長的迷霧之后,亟待以雙輪推動經濟增長向內生性軌道切換。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依靠資本與外需驅動的增長動力日漸衰減,在國際產業轉移紅利、“入世”紅利以及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之后,簡單追求高增長不僅是低質低效的政策選項,更會增加經濟轉型成本。而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來看,政府的能量和動員力再大,制度改進空間再大,也不能改變一個巨型經濟體在高速增長30年后增長動力衰減的趨勢。中國自1980年以來長達30余年的高速增長周期告一段落,轉向年均7%以至6%的中速增長,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自然邏輯延伸。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必須以經濟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非市場化力量對市場化改革的阻遏,以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有效需求提高有效經濟產出比例,還需以適當預增改革成本為代價,化解經濟領域的系統性風險,為理性繁榮清障。
經濟研究和實踐早已表明:光靠政府驅動而沒有符合要素市場價格規律的驅動,經濟難以獲得長足發展。
因此,包括各級各地政府以及其他市場參與主體應當明白:投資之于經濟增長最多只有工具價值,經濟學意義上也沒有所謂的“消費驅動型增長”概念,至于進出口,其實是經濟體之間資源稟賦的一種互換。所謂“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至多只是經濟增長的手段。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持續有效增長,本質上并不取決于投資或出口驅動,而取決于知識、信息、研發創新等所引致的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中國必須加大對研發與人力資本的投資,盡快實現要素價格市場化,提高勞動生產率。
可見,要實現中國經濟的理性繁榮,必須掃除阻礙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體制性障礙。這就要求最高決策層以前所未有的改革決心與執行力,制定壟斷行業改革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等關鍵領域改革的時間表,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破除某些部門對深層次改革的阻滯以徹底打破目前的權力配置格局,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行為空間受到切實保護,讓政府規制真正成為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切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