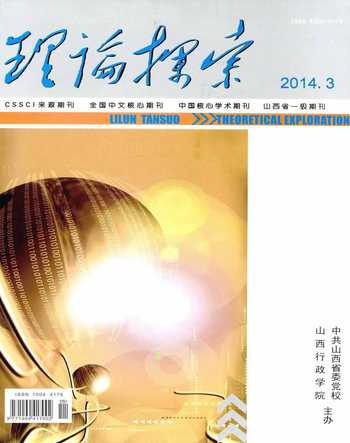法律規范詞的語義與法律的規范性指向
魏治勛 陳磊
〔摘要〕 規范法學向來重視對法律語詞的意義分析,這其中又以對法律規范詞的分析尤顯重要,因為規范詞往往通過對行為模態的設定而決定著法律規范的意義。通過界定“不得”的主要禁止性規范詞的地位、辨析其音義以及將規范詞“不得”與作為體標記的“不得”的嚴格區分,規范詞“不得”的準確意義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來,這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法律的規范性指向并將法治建設推向深化頗有助益。
〔關鍵詞〕 法律規范詞,語義分析,意義范圍,規范性指向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3-0107-06
現代中國法律是以漢語日常語言為表達載體的實在法體系,而現代漢語又是以復合詞為其基本詞類的語言文字系統。一般而言,漢語中的復合詞很多都是多義詞,甚至是多音多義詞。那么,要確定某個法律語詞的意義范圍及其規范性指向,就主要受到立法目的和法律文本語境的限制。在法律規范的語詞構成中,有一類語詞對于該類規范整體的意義及其規范性指向的確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法律規范中表達立法者意志指向并對行為模式具有方向性限制的模態詞,或者如法律語言專家所言,它們是詞性上屬于虛詞范疇的“規范詞”。〔1 〕 (P112 )根據法律規范類型的不同,法律規范詞可以區分為表達義務指向的“應當”、“必須”,表達允許性指向的“可以”,表達非命令性指向的“可以不”以及表達禁止性指向的“不得”、“禁止”等四類。① 在本文中,筆者以對禁止性法律規范的主要規范詞“不得”的意義及其規范性指向的考察為范例,深入揭示法律規范詞意義的析定對于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一、“不得”作為禁止性規范詞的地位界定
受制于立法者的規范目的和側重保護的法益的差別,法律規范的表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其形式變化不僅表現為所用規范詞的差異,而且還可以在句子的語態和主詞變化等方面得到體現,從而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樣態。就禁止性法律規范而言,以規范詞“不得”引領的句式亦非該類規范唯一的表達方式。立法者作為規范目的的設定者,同時必定有意識地追求著最為有效地實現其規范目的的手段,由此可以推論,法律規范表達形式的多樣性凸顯的乃是立法者在展示法律的規范性向度問題上對規范目的與實現手段之關系的理性考量。讓我們結合規范實例作出較為簡要的分析。
“禁止”的意義有多種表述方式。作為負載規范性向度的虛詞,“不得”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可用的禁止性規范詞。可以用作禁止性法律規范詞而具有相同或近似意義的詞項還有:不準、不許、不可(以)、不受、禁止、嚴禁等。我們以我國憲法第3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這一規范為例,這一規范還可以表述為:(任何人或組織)不得或不許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憲法)禁止或嚴禁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在采取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之后,法律規范的基本意義雖然沒有發生改變,但引發如下追問:為什么可以采取如此不同的表達方式?其合理性何在?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希望突出的規范語句的主詞不同,往往需要不同的表達“禁止”意義的語詞。學者指出,語言中產生同義詞的必要性在于,隨著人們對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認識的日益廣泛、深入、細致、深刻,就需要更多有細微意義差別的語詞來表達認識的這種微妙區分。〔2 〕 (P88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這一規則的不同表達方式為例,我們發現,盡管這一規則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似乎還是感到憲法所采用的表達方式更能夠突出立憲者的意圖。既然每一法律規范需要達成的具體目的有所不同,就可能要求突出不同的法律主體或法益,也就需要不同的規范詞,此時,對規范詞的選擇就會有微妙的差別。就這里談到的憲法規范來說,當規范以法律本身(實際上是立法者)作為主詞時,往往會選擇“禁止”或“嚴禁”作為規范語句的規范詞,此時的表述方式相應地就是:(憲法)禁止或嚴禁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這樣的表述既能達到保護公民人身自由的目的,同時也有利于突出憲法(或法律)的尊嚴。但當有意突出應受到限制的法律行為主體并以之為規范語句的主詞時,則會較多地選擇“不得”作為規范詞,那么,此時相應的表述方式就變化為:任何個人、機關或組織不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當立法者意欲重點強調需要保護的主體權利或利益時,則會將某一法律行為的受動者或者其所指向的具體法益作為規范語句的主詞,此時采用被動語態就成為立法者表述規范的最好選擇,這意味著規范選用的規范詞亦應發生改變,對于禁止性規范而言,此時最恰當的規范詞乃是“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從規范語句表達方式和規范詞選擇的上述情形可見,在法律規范具體表達形式變化背后起著支配作用的,乃是立法者對于其所規劃的規范意圖與語言表現手段的理性考量;這種語言表達選擇上的差異性也必將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法律主體對其行為方式的選擇,從而能夠對現實法律秩序的塑造產生深遠影響。
可見,在看似相同的立法目的之下,立法者卻可能會采用三種不同的表述方式之一種:直接以法律自身作為規范語句的主詞,規范詞一般用“禁止”或者“嚴禁”;或者以法律所要禁止的行為的發出者作為規范語句的主詞,規范詞一般用“不得”或者“不準”;抑或為了突出要保護的主體及其權利和利益,則以某種法律行為的承受者作為規范語句的主詞,規范詞一般為“不受”。通過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就能夠在闡明規范內容的同時,突出法律制度的目的性要素:在形式上進一步彰顯法律的尊嚴、凸顯法律的目標指向或者重點保護的主要群體或者價值。由于法律“不是客觀事實的保護者,而只是對歷史形成和發展的、符合目的性、適當性的以及——在最佳情況下——‘正義的相對表述” 〔3 〕 (P61 ),為了突出規范的目的性指向,法律規范除了要清晰地表達規范內容外,在表述方式上適當采用具有不同形式的規范語句也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加強規范效果的良好作用。
盡管禁止性法律規范可以有以上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然而一般地講,“立法者……傾向于用樸實的直陳式表述規范性的當為內容。” 〔3 〕 (P59 )而那種直接申明主體“不得為”某種行為的表述方式無疑屬于這種最為樸實的表達,因為任何法律規范的設定都必須針對法律主體的行為,以法律主體為主詞的規范表達方式有利于社會行為者簡明直接地在法典中發現其應遵循的行為依據。而且,統計數字也表明,在法律規范中,也是以這一類表達方式占居優勢地位。以憲法為例,在我國憲法中,一共有44處禁止性規定,其中以“不得”為規范詞的有20余處,以“禁止”為規范詞的有13處,以“不受”為規范詞的有11處。可以說,禁止性規范詞在我國憲法中的分布既照顧到了表述方式的豐富性,同時突出了以“不得”為主要規范詞的規范句式的主導地位;但總體上,那種直接昭示立法者意志而以法律自身為主詞的表述方式似乎仍嫌過多,這是我國憲法表述形式上與西方憲法的一個重要區別。在美國憲法中,憲法典及其修正案中共有禁止性規定91處,其中以“不得”為規范詞的有69處,以“禁止”為規范詞的僅有6處,以“不受”為規范詞的也同樣只有6處,“不得”在以上三種規范詞中占有絕對優勢。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僅以不同規范詞數量及其分布的差異來評價某種法律體系的先進與否,關鍵還要看這種差異背后的原因以及對由此導致的法律秩序品質的現實評價。
鑒于“不得”這一規范詞在禁止性規范語句表達中的主導地位,我們將“不得”視為禁止性規范語句的標志性規范詞,并在此意義上視“禁止”、“不受”、“不準”等規范詞為“不得”的同義變體。在此基礎上,將含有“不得”這一規范詞的禁止性規范視為該類規范的標準形式,通過進一步考察“不得”的語義和功能,深入揭示法律的規范性特質。
二、禁止性法律規范詞“不得”的意義辨正
確立了“不得”一詞在禁止性法律規范中的標志性規范詞地位,為界定“不得”的意義范圍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前提。在漢語中,“不得”一詞是由否定副詞“不”和副詞“得”組合而成的具有偏正結構的復合虛詞,其詞義雖然側重于“不”所表達的否定意義,但副詞“得”在構造“不得”的實體意義方面具有基礎性作用,也就是說,“不得”的意義乃是建立在“得”的實體意義基礎上的否定性表達。但問題在于,“得”亦是一個多音多義詞,所以欲確定禁止性規范中“不得”一詞的意義,就必須首先析定“得”的音調與意義范圍。
考察“得”的意義的首要途徑是借助權威工具書進行辨析。在《辭源》中,作為虛詞的“得”有兩種音和義:其一,“得”字讀作dé,作“能”、“可”講,也就是“能夠”與“可以”的意思。其二,讀作děi,作“必須”講。再看《辭海》的解釋:在《辭海》中,作為副詞的“得”有四種用法:其一,“得”讀作dé,是“能”,“可”的意思;其二,作疑問副詞,仍讀dé,作“怎得”、“得無”講;其三,讀de,作語助詞,表示“效果”或“程度”,如“說得好”,“好得很”等;其四,“得”讀作děi,作“必須”、“須要”講,如《紅樓夢》第94回:“這件事還得你去,才弄的明白”。從以上權威解釋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虛詞的“得”,有三種讀音(dé、de、děi)和四種基本含義。其中,“可以”與“必須”這兩種含義與我們所要分析的法律規范標志詞有密切關系:“可以”與“必須”都能夠被用作重要的法律規范詞。但“可以”與“必須”卻表征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規范性指向:“可以”表達的是法律對行為主體的權利或權力授予,〔4 〕而“必須”則表達對行為主體強制性義務的課予,凡是“必須”的行為,都是必為性的義務行為。作為由“不”與“得”構成的復合詞,對規范詞“得”的含義的探析勢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對規范詞“不得”的意義界定。
首先,對法律規范詞“得”的語義和用法予以考察、辨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憲法文本中,“得”字曾經作為規范詞得到廣泛應用。我們假定,在這些憲法性文件中,“得”既可以作為“可以”講,也可以作為“必須”講。但我們立刻就意識到,這樣的假定是不可能站住腳的。因為,法律規范要能夠獲得實在的規范效果,在形式上就必須保證意義的清晰、明確與一致性,不會造成理解的歧義。富勒將之作為法治的八項原則之一并認為:“這八個方向中任何一個方向上的全面失敗都不僅僅會導致一套糟糕的法律體系;它所導致的是一種不能被恰當地稱為一套法律體系的東西。” 〔5 〕 (P47 )如果一部憲法中作為重要規范詞的“得”字能夠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那么,它就不僅無益于法律表達的清晰性與一致性,而且必定會導致法律適用中的矛盾與沖突。以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為例,該憲法性文件規定,皇帝有宣告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如果規范詞“得”既可以理解為“可以”又可以理解為“必須”,則人們從中解讀出來的是兩種相互沖突的信息:在緊急情況下,皇帝一方面可以下達詔令限制臣民的自由,也可以不這樣做,是否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乃是一種具有選擇性質的權力;但當把“得”理解為“必須”時,該規范則被解讀為:在緊急情況下,皇帝必須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這是一種沒有選擇自由的必為性義務規范。對法律語義理解的沖突性必然導致法律實踐的混亂和法的實效性的喪失,此乃任何立法者力圖避免之大忌。既如此,我們必須在“得”字兩種可能意義之間作出確定的選擇。
其次,通過對規范詞“得”的兩種可能意義進行實證考察和檢驗,確定其合理的規范語義。規范詞“得”在憲法中的應用基本上只存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憲法文本中,② 亦能在某些較早的外國憲法中譯本中尋覓到其蹤跡。我們首先檢視1949年以前的中國憲法文本。國民政府1936年5月5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或稱“五五憲草”)第47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40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我們假定此處的“得”字可以解讀為“必須”。那么,該條憲法規范就可以理解為:中華民國國民年滿40歲者,必須被選為總統、副總統。顯然,這樣的理解是十分荒謬的,且不說,以當時的中國人口計,中國公民年滿40歲者何止千萬?而且,如果這些公民必須被選為總統、副總統,所謂的選舉還有什么意義?可見,至少在該條憲法規范中,將“得”字解釋為“必須”是行不通的。如已述及,既然一個規范詞在同一部法律文本中不應當具有兩種不同意義,則可以推斷,在這部憲法中,所有的規范詞“得”都不應當被理解為“必須”。那么,是不是在中國近現代的所有憲法文獻中,這樣的界定都能得到支持呢?事實表明,自中國近代第一部憲法文獻《欽定憲法大綱》始,新中國成立前各個時期憲法文本中的規范詞“得”都只能理解為“可以”。這一點可經由對《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一書中收錄的憲法文本的考查得到證實。〔6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上溯到古代法律文獻中對“得”字的應用加以考察,亦會有同樣的發現。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商紂王對西伯姬昌發布的一條詔令:“使西伯得征伐”。③這是一條授權姬昌征伐叛臣的法令,其規范詞“得”與現代法律中的授權性法律規范詞“可以”完全同義。一般而言,只有在用于口語表達時,“得”才可以解釋為“必須”。《辭海》中將“得”字解釋為“必須”時所例舉的也是口語表達:“這件事還得你去,才弄的明白” (《紅樓夢》第94回)。《辭源》所舉亦為同類例子。《現代漢語詞典》則直接將“得(děi,必須)”列為口語用法,即是明證。可見,規范詞“不得”中的“得”字,只能讀作“dé”,其基本含義為“可以”;則法律規范詞“不得”的基本含義,就只能界定為“不可以”。
當然,將法律規范詞“不得”的基本含義界定為“不可以”,僅僅是從規范詞“不得”復式構成的角度,通過解析規范詞“得”的含義而引申出的初步結論。事實上,我們必須注意到:其一,對具有禁止性含義的其他規范詞的具體語義應予充分考慮。現行中國法律中經常使用的禁止性規范詞主要有“不得”、“禁止”、“不受”三種,它們因法律規范語句主詞的不同而被靈活選用,雖然在具體含義上存在細微差別,但其所表達的法律規范性指向則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對立法者不希望發生之行為這種立法意向的表達。其二,規范詞“不得”并非僅僅是另一規范詞“得”的否定式,它同時是規范詞“應當”、“必須”、“允許”、“有權”等的否定式。因此,仔細追究起來,“不得”至少具有“不可以”、“不應當”、“必須不”、“不允許”、“無權”等含義,但這些含義之間的細微差異通常亦被忽略不計,完全可以在統合為標志性規范詞“不得”的基礎上獲得一致性理解:規范詞“不得”意味著立法者對其所限定的法律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禁止性指令。
三、作為規范詞與體標記的兩種“不得”的區分
確立了法律規范詞“不得”的基本語義范圍,就為我們深入研究“不得”一詞的規范性指向奠定了基礎。奧斯丁在開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之初,曾明確地指出,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尤其是嚴肅的“政治社會治理科學”的學科,如果容忍“語詞的諸侯割據”,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將清理這些容易混淆的語詞的意義作為重要事項列入議事日程。他強調,為了使實證主義的分析法學穩健推進,必須實現“語詞的帝國統一”。〔7 〕我們對于構成法律規范的意義具有重要作用的規范詞的界定也必須做到純粹、清晰。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將規范詞“不得”的意義和用法與容易混淆的其他性質的“不得”準確區分開來。
這里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將規范詞“不得”與體標記“不得”區分開來。“不得”作為虛詞,與“著”、“了”、“過”等共同構成了表征漢語動詞時態的“體標記”,在語法結構上與“不得”作為規范詞的情形存在明顯不同。一般說來,“不得”作為規范詞,其位置位于動詞之前;而“不得”作為體標記則往往要置于動詞之后。〔8 〕然而,由于“不得”一詞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具有的否定性意味,人們仍然容易將二者的用法混淆。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情境(這種情境在中國傳統的戲劇中經常出現):在劊子手即將對犯人行刑之際,突然有人高聲喊道:“殺不得”,我們稱之為“行刑情境”。“不得”的類似用法的句子還有:這件事馬虎不得,華而不實要不得,等等。在這里,“殺不得”在日常中往往會被理解為“不得殺”,也就是“不可以殺、不能殺”。尤其當說出這句話的人相對于聽者劊子手在權力上是“優勢者”的時候,“殺不得”又往往蘊含有命令的意味。而根據奧斯丁的觀點,權力上“優勢者”的“命令”恰恰是構成法律的一個重要要素。〔9 〕在這種情況下,“殺不得”和作為法律的規范性表達的“不得殺”往往很難界限分明,于是就愈加有著進行區分的必要性。
但作為體標記的“不得”畢竟與作為規范詞的“不得”有著非常基本的區別。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二者出現的位置不同之外,二者還有如下區別:其一,二者的詞性不同。雖然同為虛詞大類,但作為體標記的“不得”是副詞,而作為規范詞的“不得”則屬于助動詞(在英文表達中這一區別相當明顯)。其二,位置與詞性的不同,決定了二者功能上的根本區分。作為規范詞的“不得”的功能,主要起到限制它所修飾的動詞作用,通過對該動詞所代表的行為的否定,形成禁止性法律規范,進而具有構造法律行為模式和法律秩序的功能。但作為體標記的“不得”則發揮著完全不同的功能。漢語言學研究專家指出,“漢語屬于體范疇突顯的語言”,〔10 〕但由于“漢語的動詞沒有形態變化,動作的時間主要不是由動詞本身表示,而是由時間詞語、副詞或上下文表示,動作發生在過去或將來,一般需加時間詞語或副詞。” 〔11 〕 (P557 )漢語表示動詞時態以其獨特的方式而和西方語言根本區分:以英語為例,為了表明動詞所代表的不同時間向度,英語語法設計了16種不同的時態,一般要通過動詞詞形的變化或藉借時態助詞的輔助就可以完成對不同時態的表達。而漢語是表意的文字,沒有詞形的變化,漢語的時態變化只能通過時間狀語、上下文語境尤其是借助體標記來達成:“在其他語言(如英語)中由時制表達的時間概念,在漢語中可以在體范疇中得到隱含,這就是體標記的時間指向功能。” 〔10 〕而副詞“不得”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體標記詞。這就使得漢語的時態表達往往具有“體時交混”的特征。那么,作為體標記的“不得”一詞時如何體現這種“體時交混”的特征呢?我們知道,這里的“體”也就是觀念實體的意思,而“時”就是時制、時態,“體時交混”就意味著,“不得”一詞可以同時標志表達者的觀念與時間兩個不同維度。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以“殺不得”語句為例,這句話既表達了“不能殺”、“不可以殺”這樣一種實在觀念,同時表達了“現在就停下”這樣一種時間要求或“現在時”時態。但是,這一表達一般卻不具有規范性向度,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種具有規范效力的應然或當為表達,因而對聽者而言不具有規范強制力。概而言之,作為體標記的“不得”與作為規范詞的“不得”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主要承擔“時間指向功能”,而后者主要承擔“行為規范功能”。
盡管兩種不同的“不得”存在上述明顯區別,但仍舊有著混淆的危險。因為,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假如在劊子手行刑的情境中高喊“殺不得”的是一位無論對于劊子手還是對被行刑人作出死刑判決的官員來說都是權力上優位的人,甚至是一位國王,那么,根據奧斯丁的實證主義法學理論,這里的“殺不得”這一表達是不是就具有規范性指向?假如我們肯認了這一表達的“法律性質”,那么,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就與哈特一樣對奧斯丁的理論產生了近似的誤讀。誠然,劊子手“行刑情境”與“強盜情境”一樣,“對某些人而言,在如下的情況中,即一個人以威脅為后盾對另一個人發出命令,并且在上述之‘強迫的意義下,強迫他順從時,我們就找到了法律的根本要素,或至少是‘法律科學的關鍵。這就是對英國法理學有著深刻影響之奧斯丁分析的出發點”。〔12 〕 (P7 )但是,哈特顯然忘記了,奧斯丁是明確地區分了法律與一個具體的命令的不同的:“相對具體個別的命令而言,一項法律是一個強制約束一個人或一些人的命令,它普遍地強制要求為一類行為,或者不為一類行為。” 〔9 〕 (P30 )因此,在這里的“行刑情境”中,“殺不得”可以是一個勸告,甚至是一個命令,但卻不應當被理解為法律。在這一點上,奧斯丁的觀點是清晰而明確的。問題僅僅在于,“整整一代的英國法學院的學生都接受這樣的觀點:奧斯丁的‘法的命令說不能將作為‘法的命令和‘強盜的命令區別開來,這其實是受到了哈特的誤導。” 〔13 〕由此看來,我們究竟是能夠把作為體標記的“不得”與作為規范詞的“不得”在性質上嚴格區分開來的。
當然,“不得”中的“得”字還可以被用作動詞,而這種用法有著十分古老的淵源,且至今仍被沿用不輟,例如早在《詩經·周南·關雎》中,就已經有了“求之不得,寐寐思服”的句子,《孟子·告子上》則有“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的用法。除此之外,“不得”還是構成副詞的“不得已”的主要部分。但是,“不得”的這些用法與規范詞“不得”明顯不同,一般不會發生相互混淆的現象。
四、小結:法律規范詞語義分析的時代意義
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對任何一個社會問題要獲得準確的理解,就必須首先要求語言表達上的明晰性。德里達指出:“不管人們如何理解,語言問題也許從來就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問題。但與今天不同的是,它過去從未像現在這樣滲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領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體系方面千差萬別的話語之中。” 〔14 〕 (P7 )的確,在語言現象日益豐富與繁復的今天,在語言分析成為當今世界意義理解重要方式的情境下,進行法學理論研究已經不可能置語言分析于不顧了,正如麥考密克所言,“法律其實不過是一個語言學問題(The Law is simply a matter of linguistics) 。” 〔15 〕 (P12 )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在談到作為現代社會法律類型的“自治型法”時亦指出:“自治型法的一個標志就是對語義的細致考察。” 〔16 〕 (P67 )基于此,當下的法理學研究必須正視語言分析的重要性。法理學的理論分析,其首要的工作,就如同奧斯丁所做的那樣,必須清晰區分我們所要研究對象的基本界限或者范圍,這是消除法律的意義混淆、構造合理法律秩序的必要行動。
我國在2011年正式宣布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標志著中國法治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轉折:今后法治建設的主要任務,則是如何在法律實踐中更好地理解與適用法律以確保人民的權利實現和達成良好社會秩序,這就要求法學理論必須對法律的意義及其詮釋方法做出更加清晰的邏輯梳理與學理闡釋。如此,則分析實證主義的理論方法正是當下中國法治建設所必需的,分析法學理應成為中國法學的核心與脊梁。在注重法律適用的法治建設新階段,我們尤其應該重視指示法律規范向度的法律規范詞的研究。為什么研究法律規范詞如此重要?其主要理由,正如周禎祥先生所言:“由于規范是針對人的行動的,對規范和規范命題的邏輯研究很快就和人類行動概念結合起來,因為規范是對人的行動的約束,它就天然地和人類行動相關聯。” 〔17 〕 (P215 )規范法學作為專門探究法律規范和法律命題的學科,就必須從對法律的規范詞的研究入手,并由此與規范人類行動秩序和國家法治秩序的法律治理事業發生必然關聯,這是歷來規范法學研究的不二法門。規范概念就是設定人的行為模式的“模態概念”,就是 “不得”、“應當”、“必須”、“可以”等規范詞表征的法律的規范性指向, 立法者正是通過對規范詞的運用以設定行為模態進而達到塑造社會秩序之目的。因此可以說,對法律規范詞的研究,事實上就是對法律概念與法律規范命題的研究,這的確抓住了規范法學研究的命門。當西方規范法學的先驅們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規范法學概念系統和理論體系之后,規范法學自身也要求學術研究的細化和深化。這樣看來,對法律規范詞的研究就不僅應和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需求,即使從整個規范法學的視野審視,它依然能夠證成自身的合理性。
注 釋:
① 邊沁在《法律總論》將法律規范區分為四種類型:命令性法律,“應當做某事”;禁止性法律,“不得做某事”;非禁止性法律,“允許做某事”;非命令性法律,“允許不做某事”。參見張乃根:《西方法哲學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6頁。顏厥安在其《規范、論證與行動》一書中,則用邏輯矩陣圖將禁止性規范、義務性規范、允許性規范和非命令性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參見顏厥安:《規范、論證與行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0頁。由此可見,關于法律規范四種類型的劃分在東西方法學理論界已獲相當共識。從不同類型法律規范的規范性指向看,它們之間的方向性差異完全可以通過規范詞的意義辨析區分開來。
②但在我國的現行憲法中,尚有一處例外,此即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③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京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在《尚書譯注·西伯戩黎》中,亦采用此一表述:“使西伯得征伐也”。參見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頁。
參考文獻:
〔1〕康巧茹.法律規范命題推理的哲學淵源〔C〕//梁慶寅,主編.法律邏輯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陸善來.實用漢語語義學〔M〕.北京:學林出版社,1993.
〔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小春,吳越,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喻 中.再論可以P與可以不P的關系〔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
〔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鄭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6〕夏新華,胡旭晟.近代中國憲政歷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7〕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J〕. 5thed., London; John Murray, 1885,Vol.Ⅰ, pp. 85~86.
〔8〕李 訥,石毓智.論漢語體標記誕生的機制〔J〕.中國語文,1997(2).
〔9〕〔英〕約翰·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M〕.劉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10〕尚 新.體義相交理論:漢語體標記的時間指向功能〔J〕.語言科學,2005(5).
〔11〕房玉清.實用漢語語法〔M〕.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12〕〔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M〕.許家馨,李冠宜,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3〕陳 銳.奧斯丁的分析法學思想研究〔J〕.池州師專學報,2003(2).
〔14〕〔法〕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M〕.汪家堂,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15〕Neil MacCormick,H.L.A.Hart〔M〕.Edward Arnold Ltd, London 1981.
〔16〕〔美〕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M〕.張志銘,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17〕周禎祥.規范、動態道義邏輯和法律規范知識表達〔C〕//梁慶寅,主編.法律邏輯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楊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