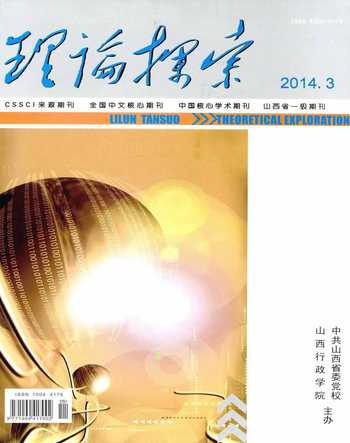行人交通違章的法律治理
吳建國
〔摘要〕 我國在行人交通違章的法律治理方面存在立法缺位、處罰畸輕、標準不一、手段單一等諸多缺失。結合域外治理行人違章的有益經驗,治理行人違章,從根本上減少行人違章現象發生,應根據“成本—收益”原則,提高行人交通違章成本;根據“權利責任對等”原則,賦予行人與機動車同權同責;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遵循“暢通原則”,進一步完善便民交通設置;按照“寬嚴相濟”的原則,建立違章處罰與安全教育相結合的長效機制。
〔關鍵詞〕 行人交通違章,法律治理,違章成本,路權
〔中圖分類號〕D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3-0120-05
據交通部門權威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交通事故死傷人數連續十年高居世界第一,交通事故已成“中國第一害”。在造成人員死亡的交通事故中,由行人交通違章造成的占總事故數的80%以上,由車輛違章和道路原因導致的事故只占總事故的百分之幾。〔1 〕 (P93-96 )這說明行人違章已成為威脅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然而,目前國內關于治理交通違章的法律研究主要集中于機動車駕駛人,而對行人交通違章行為及其法律研究頗少。筆者通過查閱全國各地治理行人交通違章的相關文件資料,對行人違章的治理現狀進行梳理,發現存有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我國在治理行人交通違章上存在著立法缺位、處罰畸輕、標準不一、手段單一等諸多缺失,缺乏應有的規范化和制度化。針對行人交通違章治理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在對其成因進行分析論證的基礎上,結合域外治理行人交通違章的有益經驗,提出治理行人違章的法律對策,以期從根本上減少乃至杜絕行人交通違章現象發生。
一、根據“成本—收益”原則,提高行人交通違章成本
生活在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會通過“成本—收益”的計算進行趨利避害,對自身所面臨的機會、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做出優化選擇。通過提高行人交通違章成本,使其因交通違章而付出的成本高于通過違章獲得的收益,違章人就會因得不償失而選擇放棄違章行為,從而有效遏制違章行為發生。然而,我國現行交通法規對行人違章的處罰過輕,導致行人違章成本過低,在規制行人交通行為方面沒有形成較好的威懾作用。1988年8月,我國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標志著我國對道路交通的管理步入法治化軌道。該條例明確規定將行人納入道路交通管理范圍,并在“第七章”專門列舉了針對行人的各種禁止性規定。但在“處罰”一章共16條的具體處罰規定中,卻僅有1條且是附帶針對行人違章的處罰規定,即第82條“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乘車人違反本條例規定的,處五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2 〕 (P43 )該條例在列舉了行人的各種違章行為后,卻對行人違章種類和情節輕重不予考慮,只規定了適用罰款或警告的單一處罰類別,五元以下的畸輕處罰標準。這種標準既使在當時看來處罰力度也顯然過輕,處罰方式單一化,既不能罰當其行,也無法形成寬嚴相濟、區別有致的處罰梯級。同時,為規避濫權而設定的處罰上限又在客觀上限制了各地在制定實施細則時的自主性,其畸輕的處罰標準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應有的修正。2003年,該《條例》被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取代,2004年,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2011年,《道路交通安全法》進行了再修訂。但是,其中關于行人違章的處罰規定,除將罰款數額從之前的五元以下提高到五至五十元以下外,其他規定則完全沿用了1988年《交通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該法雖在許多方面得到進一步完善,然而,修法卻沒能改變對行人違章處罰過輕、手段單一等問題。
相比而言,西方國家少有行人亂穿馬路和闖紅燈等違章現象發生。通過對行人交通秩序較好國家的實證研究,筆者發現,這些國家對行人違章普遍采用了相當嚴厲的制裁措施和多樣化的處罰手段,從而迫使行人放棄違章行為,轉而“自覺”遵守交通規則的。在美國,交通違章被認為是一種嚴重違法行為,其處罰統一由各州、市、縣法院負責執行,各地法院均設有一個民事法庭專門受理交通違章。在罰金數額上,西方國家對行人違章的罰款數額相對較高,但會視違章情節輕重而具有梯度性。美國對違章行人的罰款數額一般從2美元到50美元不等,但在洛杉磯等一些地方,警察對行人闖紅燈違章的罰金數額甚至高達191美元(約合人民幣1200元)。當行人或機動車駕駛人第一次違章時給予一定寬容處理,如因再度違章則會被處以較高罰金,超過一定期限拒不交納罰金或是違章情節特別嚴重且情況危急時,法院可以通過警察局對違章行人采取強制措施,執勤警察也可對行人給予拘留處罰。在美國,無論何種交通違章,只要被開具罰單,違章記錄就會被永久性存入個人社會安全檔案。這些記錄在公民的晉升、信用、保險、求職等多個方面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如雇主在招聘雇員、晉升職務時都會將社會誠信情況作為一個重要考核指標,保險公司也會根據公民的違章情況具體核定保費標準。違章記錄越多,所要繳納的保費就越高。在法國,如果行人在斑馬線外橫穿馬路,將給予4歐元(約32元人民幣)的罰款。在新西蘭,基于兒童與成年人在認識能力和行為能力上的不同,違章處罰也予以區別對待。對亂穿馬路的兒童罰款為10新元(約50元人民幣),而對成年人罰款則高達35新元(約180元人民幣)。澳大利亞對亂穿馬路者給予高達200澳元(約合1300元人民幣)的罰款。以嚴刑峻法著稱的新加坡對亂穿馬路行為的懲罰則更為嚴厲,且具有梯度性。對于初闖紅燈者,罰款200新元(約合1000元人民幣),如果多次違章,最重可判一年監禁,罰金數額也隨之劇增。在他們看來,嚴管重罰是對生命權的保護和尊重。〔3 〕 (P10 )歐洲的多數國家規定,行人違章穿越封閉高速公路造成交通事故的,由于這一行為極易導致多車連環相撞的威脅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重大交通事故,違章行人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入獄。在德國,當公民進行購物消費時,如果個人檔案中存在交通違章記錄就不能享受銀行提供的分期或延期付款服務,須當即全額付清。當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安全記錄良好的人可以申請長期貸款,而有違章記錄者卻不被允許。同時,銀行給有違章記錄者短期貸款的利率也要遠高于記錄良好者。因為德國銀行家認為,道路違章者不懂得珍惜生命,一旦出現意外事故,貸款很可能無法收回,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限制措施。人們由于擔心喪失貸款資格和購買力,因此對自己的交通行為更加負責,客觀上營造了一個人人遵守交通法規的良好社會氛圍。
目前,我國在治理行人違章上尚缺乏有效的處罰手段。對機動車駕駛員違章可以采取扣車、扣證、扣分等多種制裁措施,但是對于行人違章,除了罰款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抓手”。就罰款而言,違章者付出的成本較低且僅為單一經濟成本,難以有效遏制違章行為。針對違章對象的不同,其罰金的處罰效果也會有很大差別。由于窮人與富人在對罰金敬畏心理上的差異,單一標準的罰金容易造成“富人橫行馬路、窮人寸步難行”的消極社會效果。因此,交通立法應充分考慮處罰對象和實際效果,實現兩者統一。我們應當看到,違章成本并非只能是經濟成本,還應包括時間成本、勞動力成本、聲譽成本、信用成本甚至是人身自由成本等多個層面。鑒于此,可以考慮引入公益勞動、擔任臨時交通協管員、參加交通法規學習班等多種處罰方式,以補充單一罰金的不足,用時間、聲譽和精力等多種成本,甚至是復合成本代替純經濟成本。我們還可以考慮將攝像頭拍攝的行人違章視頻或截圖借助交通信息網站或當地報紙等媒體向社會公開,給予違章者一定的精神懲戒。加快行人交通誠信機制建設,進一步嚴格行人身份管理,探索建立公民交通誠信檔案,將行人的違章信息納入公民交通誠信數據庫,使之成為公民個人信用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其在升學、求職、晉升、購房、貸款等方面考量的依據。通過信用機制,讓更多人意識到交通規則的重要性,為人們營造一個“守信一路暢通,失信寸步難行”的社會信用環境。違章成本不得畸重畸輕,應視違章情節而逐級提高。我們可以將行人違章行為根據違章性質、違章頻次及對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進行分級和量化。對于行人的初次違章行為,可以視情節輕重給予口頭警告、批評教育和交納小額罰金,如果再次故意違章,就要提高違章成本,通過高額罰金增加其經濟成本,通過公益勞動增加其勞動力成本,通過自費參加學習班增加經濟、時間和聲譽等復合成本,借助媒體公布違章人信息或通報其工作單位以增加其精神成本,將違章情況記入公民個人誠信檔案增加其信用成本。對于少數違章情節特別惡劣、抗拒執法、拒不接受處罰的違章當事人,還可以考慮給予行政拘留以至入罪等更為嚴厲的處罰方式,使違章者付出人身自由的更高成本。總之,我們應當積極探索治理行人違章行之有效、靈活多樣的處罰方式,提高行人交通違章成本,以期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
二、根據“權利責任對等”原則,賦予行人與機動車同權同責
路權是指交通主體根據交通法規的規定,于一定空間和時間內,在道路上進行交通活動的權利,路權分為上路權、通行權、先行權、占用權。如機動車在機動車道行駛,非機動車在非機動車道行駛,行人在人行道上行走,都享有各自的道路權利,其他交通主體不得侵犯,否則就構成侵權行為。在處理交通事故時,違章一方往往承擔主要甚至全部責任。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國的城市交通建設是以車為本的。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指導下,城市的交通發展主要是為車而非行人服務的,表現為路面越來越寬,高架橋越來越多,行人卻在這些高大宏偉的路橋面前望而生畏,舉步維艱。行人路權被機動車肆無忌憚地侵犯,行人在城市交通中的位置被邊緣化。行人為爭路權而與搶道通行的機動車對峙和沖撞的情境時有發生,最終導致行人在斑馬線上被撞的交通事故頻發,安全線演變成“奪命線”,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當前道路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在現行的交通法規中,針對機動車與行人路權與責任的劃分幾近空白,這就為行政執法預留了太多空間。凡法律規范中權利義務留有伸縮余地的地方,行政機關就相應地取得了行政自由裁量權,其可以在法定幅度內選擇,也可以根據法律原則確定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具體定量。〔4 〕 (P305 )然而,缺乏羈束行政行為的交通執法在監管行人時更多地表現為行政不作為,不僅沒有能夠規范雙方權責關系,反而使之陷入一種亂象。行人與機動車在通行路權和交通責任上的權責不明確和實際不對等是誘發行人違章的重要因素。對侵犯行人路權的機動車違章行為進行處罰是交通執法部門的一項特定行政作為義務,行政主體對于這種義務的不履行,將直接導致特定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害,〔5 〕 (P64-73 )即行人的道路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應有保障。在城市交通上堅持以人為本,就要以行人能不能方便快捷出行作為路權設置的出發點。讓行人和機動車享有同等路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允許行人享有優先路權,不僅是遵行對行人傾斜保護原則之要求,更是現代城市交通文明之體現。如果無視行人路權,或將機動車路權凌駕于行人路權之上,行人的通行權就無法得到根本保障,勢必激起行人為爭取路權的違章反制行為,道路交通就極易陷入混戰狀態。這不僅直接危及行人交通安全,也增加了機動車的通行難度和事故發生概率,最終導致兩敗俱傷。真正還行人以路權,不是設幾個“讓行人先行”的標志就能解決問題的,關鍵要通過建章立制,明確行人的路權范圍,嚴厲制裁機動車在人行道上不減速慢行、停車以避讓行人等各種侵犯行人路權的違章行為,倡導“行人優先通行”之路權理念。道路管理部門也要優化人行道設置,重視獨立人行道建設、增設斑馬線、過街天橋或地下通道,不得隨意占用和減少人行道,以確保行人與機動車路權的實質平等。
給予行人與機動車平等路權,與此同時,也應當要求享有路權的行人承擔與其權利相對等的道路交通安全責任。加強行人的道路安全責任是保障行人路權實現的必要措施。交通立法雖然需要給予行人必要的傾斜保護,但這種禮讓并不等于可以恃意減輕行人的交通違章責任。相反,只有不斷強化行人道路安全責任,才能使行人路權得到最終保障。權利向來是與責任相應而生的,同權必須同責,否則勢必造成行人對路權的濫用,最終威脅到自身路權。美國被喻為裝在車輪上的國家,但大多數美國人無論駕車還是步行,都會敬重對方的路權。在處理機動車與行人相撞事故中,也不是簡單地偏向行人,而是注重責任認定。行人違反交規被撞,多數情況下主要責任還是由行人自己承擔。?因此,我們應當通過健全相關立法,在明晰行人路權的同時,加強行人道路安全責任,嚴厲制裁行人違章,使其承擔與權利相對應的安全責任。
三、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遵循“暢通原則”,進一步完善便民交通設置
由于道路上的行人本身不具備任何安全防護設施,相對于借助一定交通工具的其它交通主體而言,顯然是一個弱勢群體,在交通安全責任上與機動車不可能無條件的絕對平等。一邊是銅墻鐵壁,一邊是血肉之軀,行人在機動車面前猶如螳臂當轍,不堪一擊,在法律上具有給予一定傾斜保護的客觀需要,這也是法律所保護的實質正義之體現。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對人的基本價值更加關注,“以人為本”成為立法的價值取向和終極目的。如果離開了社會的道德基礎,缺乏必要的倫理價值,任何立法都難以找到成功的基石。〔6 〕 (P135 )“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立法者在交通法規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堅持對行人的尊讓性,給予必要的傾斜保護。從法律所保護的價值位階上看,二者亦不在同一位階之上,行人的生命健康權無疑高于機動車的優先通行權。生命健康權是最基本的權利,“由這些基本權利派生的其他權利,其價值位階低于基本權利。在與基本人權相沖突的時候,可以為保護這些基本人權而將它置于受適當限制和從緩實現的地位。”〔7 〕 (P181 )。倘若機動車駕駛人只是為實現自己優先通行之路權而不采取避讓違章行人的措施,則違背了價值位階原則。如果確因行人的違章行為造成威脅公共交通安全的緊急情境出現時,機動車駕駛人才能以公共安全之目的而選擇不避讓違章行人。此時,犧牲違章行人的生命健康權是為了保護更大范圍的生命健康權,可以被認定為緊急避險行為而免于處罰。總之,價值位階原則要求我們做到“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以人為本”的理念旨在保障行人路權的充分實現,針對行人的各種交通標識、信號及設施是否完備并符合“暢通原則”對行人能否順利通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5條規定“交通信號燈、交通標志、交通標線的設置應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暢通的要求和國家標準,并保持清晰、醒目、準確、完好。” 〔8 〕 (P29 )但是,在實際道路中卻普通存在交通標線模糊不清,或是應該有標線和警示牌的地方卻沒有設置,人行道與車行道缺少必要的隔離設置,供行人通行的斑馬線較少甚至缺失,人行道缺少連通性等問題,嚴重有違交通出行的“暢通原則”。具體地說,紅綠燈間隔時間設計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亂穿馬路的原因之一。這種不合理通常表現為紅燈等待時間過長,超出了普通行人正常的心理承受力,導致有人先行違章而觸發的羊群效應;〔9 〕 (P3-5 )綠燈通行時間過短,無法滿足老弱病殘孕等特殊群體的通行之需,這都在無形中為行人自覺遵守交規帶來壓力。由于交通設置的非人性化,還常會遭遇行人為順利通行而不得不違章的兩難情境,致使行人被動選擇違章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人遵守交規與順利通行的矛盾、行人違章合理與交警處罰無理的矛盾,勢必引起行人對交通法規的逆反心理,不配合以至對抗交通執法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了交通法規在民眾心目中的正當性和權威性。
“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為行人提供更多的交通便民設置。在宏觀層面,注重人行道、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等設施的合理規劃,確保行人通行的連貫性,減少行人不必要的迂回,完善人車交通分離系統建設。在微觀層面,在行人等待紅燈的區域設立“行人等候線”和圍欄,使行人等候線與圍欄形成一個“行人等候區域”,既可以起到提醒行人勿闖紅燈的作用,又規范了行人等待紅燈的行為,增強了闖紅燈違章的可量化標準。同時,對于交通信號燈的時長設置也需要增加人文關懷,紅燈等待時間不宜太長,綠燈通行時間不宜太短,以免在無形中增加行人過馬路闖紅燈的可能性。同濟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進行的一項調查問卷顯示,有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在許多情況下是因被迫無奈而違章。〔10 〕 (P130-134 )在立法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制定更多頗具人性化的便民設置,將會促使行人自覺守法,減少因交通設置不合理而導致的被動違章行為,避免行人與交通法規的對立。
四、按照“寬嚴相濟”的原則,建立違章處罰與安全教育相結合的長效機制
寬嚴相濟原本是一種刑事政策,“寬不是要法外施恩,嚴也不是要無限加重,而是要嚴格依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刑事法律,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來懲罰犯罪,做到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11 〕 (P352 )其精神和理念同樣可以適用于交通法規的立法和執法過程中。寬嚴相濟并非寬嚴無度,而是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有度,寬嚴審時。具體地說,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中規定“行人列隊在道路上通行,每橫列不得超過2人” 〔4 〕 (P49 ),但該條并不為大家所熟知,在實際通行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成群結隊通行的情形,完全遵守這一規定缺乏期待可能性,加之該行為的危險性相對不大,對違反該項規定的行人不能一罰了之,除給予必要的警示告知外,更為重要的應是對其進行交通法規的宣傳和教育。“以人為本”的理念必然禁止“創收式執法”,處罰不是目的,引導行人遵守交規才是交通立法與執法的意旨所在。對行人違章應做到一經發現,立即制止,使其不能為,而不是使其為而罰之。那種執勤交警站在道路對面,等待違章行人通過后進行處罰的執法方式不僅無法起到預防交通事故的實際作用,還極易激起行人對執法行為的抵觸情緒,進而抗拒執法。因此,文明規范的交通執法應盡量做到事前制止,而不是事后處罰,使執法更具人性化。美國對于行人違反交通規則的處罰采用罰款與教育并舉的方式,收到了較好的治理效果。在美國,如果行人是初次違章,一般以強制接受安全教育的方式代替罰款,每年只有一次機會,如果再犯將被重罰。這種懲罰與教育并用的方法成效顯著,接受了教育的違章者大都能夠自覺遵守交通規則。在菲律賓,違章人可以選擇接受處罰的具體方式,如不愿交納罰金,還可在違章地點當眾演唱國歌,通過激發其愛國意識和自尊心,以示處罰。在印度尼西亞,行人闖紅燈有可能受到剃光頭處罰。剃光頭在當地是一種羞辱式的懲罰方式,以喚醒違章行人的廉恥心。德國在嚴格處罰行人交通違章的同時,極為重視對公民的交通安全教育。德國人認為,違章處罰只是一種懲戒措施,培養遵紀守法的素養才是治理違章的根本,關鍵在于通過交通安全教育,營造一個人人遵守交規的社會氛圍,并把培養兒童交通安全意識作為整個教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是世界上交通事故率極低的國家,這主要得益于日本人從小培養起的交通安全意識。從娃娃抓起,寓教于樂是日本交通安全教育的成功經驗之一。為了使兒童盡早熟悉交通規則,日本建有“兒童交通公園”,模擬公路交通環境,通過身臨其境,教育兒童如何遵守交通規則。日本成年人嚴禁在兒童面前做出闖紅燈或橫穿馬路的違章行為,以免對兒童產生不良的示范效應。因此,我們應當廣泛利用新聞媒體和網絡、課堂等多種渠道和方式加大交通法規的教育和宣傳力度,讓更多行人了解交通法規,樹立規則意識,探索將交通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依托全民交通安全普法教育,營造一個人人遵守交規的社會環境。
行人遵守交通規則有賴于科學嚴謹的法律規范和制度保障,完善的行人交通違章監管和處罰立法是實現對行人違章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依據。我國應盡快建立和健全治理行人交通違章的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將行人違章等級、處罰標準、處罰方式和處罰程序等在立法中予以明確規定和具體量化,使其具有更好的明示性、強制性、穩定性與可操作性。通過立法,在合理分配路權的基礎上充分保障行人路權,同時強化行人交通安全責任,提高行人違章成本,建立違章處罰與安全教育相結合的長效機制,標本兼治,實現對行人交通違章治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從根本上減少行人違章現象發生。
參考文獻:
〔1〕吳 瀟,黃玉婷.對海淀區黃莊路口行人闖紅燈的統計調查與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6(6).
〔2〕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M〕.北京市: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3〕陳 百.行人闖紅燈各國罰多重〔N〕.北京晨報,2013-05-07.
〔4〕關保英.行政法模式轉換研究〔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0.
〔5〕周佑勇.行政不作為構成要件的展開〔J〕.中國法學,2001(5).
〔6〕李建華,等.法律倫理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7〕蔡定劍.法制現代化與憲政〔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8〕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規匯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9〕Andrea Devenow,Ivo Welch.Rational Herding in Financial Economic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4).
〔10〕李開兵,汪 劭.行人交通違規行為的心理學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2007(5).
〔11〕夏錦文.傳承與創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值〔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 楊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