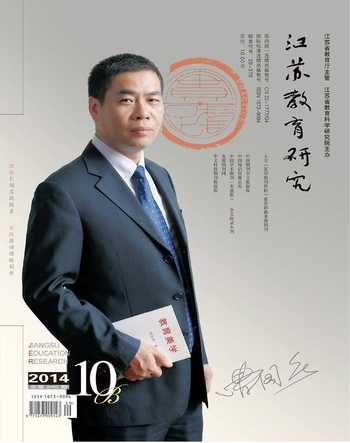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
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做個麥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
在一個時代里,有兩種人注定了他們的孤獨和痛苦:一種是落在時代后面的人,一種是走在時代前面的人。
一支長矛。一個身著鎧甲的中世紀騎士。一面皮盾、一匹瘦馬和一只獵兔狗。這是《堂吉訶德》開篇場景,也是不止一次在我夢里出現的畫面。在我的夢中,那一個孤獨的騎士,是我。穿越30個春秋的風風雨雨,一些春花般的夢已次第零落,越來越清晰且堅硬的是內心的堅守。我能體會到堂吉訶德一樣的孤獨,更多的是緣于對教育理想的一種堅守。
一
其實,我曾經的理想是做一個詩人。即使走上了講臺,寫詩還是我最大的興趣和愛好。說我跟語文教師有緣,不如說我跟文學有緣,組詩社,編詩集,辦詩會,樂在其中。1988年,我第一年帶高三,班上有70多名學生,一半是復讀的,我沒覺得什么壓力。因為年齡相仿,我整天跟學生泡在一起,上課也很隨意,更多的是把文學的熱情帶進了課堂,把語文當成了文學。隨意甚至有些散漫,一份熱情偶爾還有點率性。學生居然也喜歡我的課,喜歡我的語文,班上有不少人后來讀了中文系,成了我的同行。
因為學生的喜歡,學生的成長,我漸漸享受到為人師的樂趣。2008年高考,我帶學生走進考場時,有個學生走到我身邊:“曹老師,讓我握握你的手吧,我心里會踏實。”于是,一個熱烈的場面出現在備考休息室,48個學生爭先恐后地走向我,圍擁著我,紛紛向我伸出手來。高考回來的車廂里,后座突然傳來一個聲音:“曹老爸!”我站起身,將信將疑地問:“什么,你們喊我什么?”車廂里頓時爆發出一陣整齊的喊聲:“曹老爸!曹老爸!”撲面而來的波濤瞬間將我幸福地吞沒了。教師人生的幸福場景,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似乎是無意栽柳而葳蕤成蔭的一片風景。
愛與被愛,是一個教師的動力之源。這種源于內心的真誠,讓我甘心情愿去為孩子們做一切。做班主任的那些年,我和孩子們的心里都收藏著許多甜蜜的記憶。春天了,我跟孩子們去雙山島的江灘上野炊;中秋了,我給孩子們送上月餅,在操場的草地上共賞明月;生日了,我為每一個孩子送上全班簽名的賀卡……孩子們快樂,我也快樂著他們的快樂。
我曾經說過:“教書是我的職業,寫作才是我的事業。”從把教書當職業,到不知不覺地喜歡教書,更多的是孩子們給我的影響,是他們讓我把教書也當成了自己一生的事業,并且樂此不疲,正如我同事在QQ上簽名所說的那樣:“其實,一直是孩子們在陪伴著我們。”
二
拿破侖說:“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真正要教好書,成為一個學生喜歡的教師,成為一個學者型的教師,需要全心全意地付出。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做一個三好先生”,三好,一是好學,二是好思,三是好為人師。《勸學》中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名而行無過矣”,說的就是“好學”和“好思”。美國學者波斯納也說過同樣的話:“教師成長=教學過程+反思。”“好為人師”,就是要喜歡教師這個職業。
我的血液里流淌著不安定的變革的因子,但這些因子并非與生俱來。我閱讀教育論著,聆聽專家學者的報告,參加各類層次的專業研修,并拜特級教師黃厚江先生為實踐導師,拜鄭桂華博士為理論導師。學習,給了我實踐的底氣,思考,給了我創造的靈感。學習,給生命以動力,思考,給生命以活力,生命的動力與活力,讓課堂煥發了魅力。
上世紀90年代,我受魏書生老師的影響,開始靜下心來思考該怎么教學生才是最好。我去讀葉圣陶。葉老說:“教是為了不教。”他還說:“要讓學生自己去歷練。”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學習是學生自己的事,教師只是為學生學習服務的,我們可以幫助,指導,督促,鼓勵,但不能越俎代庖。
那年,我新接手高一的一個班級,便開始嘗試讓學生自讀自講,互評互補。我讓學生去查參考書,讓學生用練習冊答案,我指導一篇課文可以從哪些角度去學習,需要學什么。然后學生輪流講課文,講自己學到了什么,教師只是進行補充和評價。最后,還是請學生梳理歸納一堂課學到的內容。一個學期下來,班里的學生養成了主動學習的習慣,學會了自己去查資料,分析課文,學過的東西還記得特別牢,比原先教師講、學生聽的效果好得多。教師動腦,學生動手,這才是教學,是有效的教學。
學生怕寫作文。為什么怕?我不能蠻干,我得想明白。寫大作文,不少學生有恐懼感,擠牙膏一樣還是字數不夠,那么就化整為零,化大為小;作文評講,教師講,學生聽,很難針對學生個體,學生聽過也不往心里去,那么就自評互改,讓學生動起來;作文訓練序列的隨意性較強,一次一個樣,學生樣樣都不熟練,那么,就循序漸進,環環相扣。譬如寫景,我把寫景的訓練點分解,第一次1-2個點,寫300字左右的片段,只要達到目標,就是高分。第二次再增加1-2個訓練點,第三次再增加……逐層推進。分解訓練完成了,再訓練整篇的結構和立意,完成一篇完整的大作文。每次寫作后,教師指導如何評價,列出評價的標準和角度,讓學生逐條對照,先互相評點,再自我評點。寫得短了,學生自然不怕寫了。能得高分了,學生自然有興趣寫了。寫作,是學生自己的事,整個過程學生都在體驗和反思中,效果自然要好。
2008年,我評上特級教師,并成立了市級特級教師工作室。作為領銜人的我,在與工作室成員的切磋交流中開始更多地反思學科教學,提出了文本教學“質點—視點—遠點”策略。第一屆蘇派名師展示,我上了一堂《景泰藍的制作》,受到聽課者的好評;第二屆蘇派名師展示,工作室兩位成員開課,我開設了“質點說”的講座,江蘇師范大學魏本亞教授進行了現場點評,對我的主張和成員的課堂實踐作了詳細的剖析,并做了積極的肯定。南京師范大學博導楊啟亮教授說過:“教育科研也是生產力。”教育科研帶來的成效,讓我感覺到思想的光亮要比單純的技巧更有價值。
2009年,我的目光從學科轉向課堂,開始尋找適合學校實際的課堂教學的科學路徑。洋思、杜郎口、東廬、靜安附小、衡水……國內有知名度的課堂教學模式,我逐一學習,比較琢磨。根據自己的實踐體會和學校師生的現狀,我歸納總結了“先學后教、以學定教、教學互動、教有反饋”的“活動前置式”教學法,并在學校推廣,成為崇真中學的課堂教學模式之一。
三
理想,以一種浪漫而優美的姿勢站立,常常遠在現實的彼岸,一個終日埋首于現實的人,永遠無法看見她美麗的容顏。所以,教育,要保持一份浪漫的情懷,教育,需要有抵御功利誘惑的勇氣。然而,現實生活里常常有一個巨大的黑色的帷幕遮蔽著眾人的雙目,有一雙無形的手牽引著人們在功利的場地里轉圈,許多懷揣教育夢想的人,走著走著就迷失了方向,忘記自己從何出發又走向哪里。在很多時候,教育的目的從發展人,變成了培養人才,再變成培養精英人才,又簡單直接到了升學或就業,寬廣的大道窄化為獨木小橋,一步步滑向功利的泥潭。我曾在《讓教育有一點浪漫》中寫道:“應試轉盤上旋轉的孩子們,已經陌生了童年的色彩;升學績效評估下的教師們,已經淡漠了職業的幸福。理應充滿生機的孩子和充滿激情的教師,卻成了這個世界上最灰色的一個群體;理應成為樂園的校園,卻成了令孩子們望而生畏的煉獄。”毋需高深的理論剖析,只需一份教育的良知,我想,就應當去改變這樣的現狀。在崇真高中工作生活了20多年,學校在我的心里早已是一種家的感覺。作為家庭的一員,作為一校之長,我無法寬容自己得過且過,虛度時光。
上任伊始,在崇真中學全體教工會議上,我提出了“五個發展觀”:全員發展、全人發展、長遠發展、科學發展、快樂發展。全員發展,是面向每個學生的教育,但并非每一個學生都要進本二及以上的院校;全人發展,是學生個體素質的全面提升,但并非要求成為樣樣優秀的全才;長遠發展,是面向學生未來發展的奠基,我們必須為學生將來去做的事,也許眼前不見成效,但未來不可或缺;科學發展,是尊重規律的教育,適合學生的因材施教的教學;快樂發展,是尊重生命當下的教育,生命整個過程都應該是幸福的,尤其是最應該美好的青春時光。
“五個發展觀”是我堅守的教育理念,雖然并無新鮮之處,但從我口里說出來的時候,內心則充滿著憧憬。因為我沒有把它當作一句裝飾門庭的標語,而是視之為學校行動的指南。在口號盛行的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失去內心的真誠,教育變成了一種技術,學生成為了一種工具,為了滿足某些功利的需求。而我堅信自己是對的,我的勇氣與力量來自對教育的理解與真誠。
在我決定取消晚自修坐班制的時候,有人善意地提醒:“你不搞改革,即使有點差錯,你也有借口,因為不是你的原因;你搞了改革,出點什么問題,責任都是你的。”循規蹈矩是不是更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不是更安逸?但我覺得作為校長,就應該有責任有擔當,為師生著想,讓教育回歸本真,而不是明哲保身。只要方向正確,就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就這樣,學校延續了近20年的自修坐班制正式退出舞臺。兩年過去了,學生自修也漸漸養成了自主、自覺的習慣。
在錯已成為一種被周圍人接受的現實時,一個人選擇對并堅持不棄是何等的艱難。學校每周有社團活動,有家長怕影響孩子的文化成績,發短信給我:“請以分數為重”;宿舍常規檢查嚴格了,又有家長說:“到學校是來學習的,其他活動適可而止。”家長不滿意,家長不理解,我就邀請他們當面溝通,但不會放棄我的堅持。
我理想中的學校應該擁有這樣的一種美好:和諧,自由,生長,幸福。
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內心都應該是和諧的,美麗的。為了學校的易地新建,我換上雨鞋,在堆滿水泥黃沙磚石的工地上穿梭往來。一年過去,我的體重整整減了十斤。站在園林般美麗的崇真校園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輕松和愜意。亭臺樓閣相接,小橋流水多姿,白鵝浮綠水,黃鸝鳴翠柳,自然景觀與人文氣息相融相生。餐后或課間,三三兩兩的教師和學生徜徉其間,處處賞心悅目,怡情養性。
“敬愛”系列活動的開展,把敬老愛幼、敬師愛生的傳統美德發揚光大;“美時美刻”,為學生的校園時光刻下一個又一個美好的印記;書香崇真,滋養著師生的心靈;社團嘉年華、體育節創意秀,給了學生自主選擇與創造的機會;傳媒特色班、崇真校本課程系列給學生提供了個性生長的土壤。校慶日,我與學生一起切開喜慶的蛋糕,師生共賞焰火晚會,歡聲笑語蕩漾在校園的每個角落。迎新晚會后,五彩霓虹照亮校園的夜晚,百千枝條掛滿了師生祈福的紅絲帶。
給每一個學生以生長的機會,給每一個學生以成功的希望,這是一個教育者的責任。作為一所普通高中,我們肯定要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文化成績的提升上,但學校的生源決定了進入本二以上高校的學生不可能很多。與往年不同,2014屆畢業生里多了一批影視傳媒藝術生,33個同學報考,全部獲得了高校的專業合格證書,高考成績揭曉,其中有30個同學達到了本二院校的分數線。其實,傳媒藝術班成立之初,家長有懷疑,教師有顧慮。環顧市內所有普高,都是清一色普通文化類,“第一個吃螃蟹”是需要勇氣的。正是這份勇氣,我們為學生打開了多元發展的新通道。有一位喜歡唱歌的女生,文化成績并不好,升入高二的時候,幾乎喪失了繼續學習的信心。參加傳媒技能培訓后,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希望,她主動找到班主任匯報自己文化學習的目標、計劃。專業面試,她一個人獲取了5所院校的合格證,高中畢業后順利考入了傳媒大學的播音主持專業。新一屆傳媒班成立之際,她特意錄好視頻傳給母校,熱心地給學弟學妹介紹學習經驗。
“我致力于改變這所學校,這所學校在悄悄地發生改變。”2013年的歲末,我在日志里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我相信教育的明天,在我心里,這種信仰像是一輪朝陽,它照亮我的前方并一路相伴,更重要的是,它不斷賦予我激情、勇氣和力量。在這塊“麥田里”,我守望的不只是一份責任,更是一片希望。
(曹國慶,張家港市崇真高級中學,215600)
責任編輯:宣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