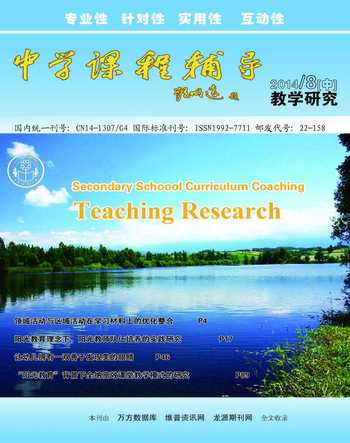淺談語文教學的人文色彩
鄧大虎
^ 摘要:縱觀幾十年眾多語文教師的語文教學實踐,那些富有成效的語文教學,總是將科學主義理性方法的實施限定在一定量度內,而盡力發掘語文的人文精神,將它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關鍵詞:語文教學;實踐;復雜語文教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性。語文教學實際就是語言教學,而語言本身不僅僅是一種工具,還是人本身,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種外在于人的客體,而是主體;不僅僅是“器”“用”,還是“道”“體”。它滿含主體情感,充滿人生體驗。因而人文精神是語言的基本屬性。好的語文教學,需要師生共有一種植根于語言人文精神的人倫情懷、人生體驗、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來凝固化的語言,充分施展個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種癡迷如醉、回腸蕩氣的人化情境,從中體悟語言妙處,學會語言本領。——這是語文教學成功的根本。科學主義理性方法,永遠不可能長度清晰地解決語文教學的復雜性,不可能根本解開語文教學之謎。
縱觀幾十年眾多語文教師的語文教學實踐,那些富有成效的語文教學,總是將科學主義理性方法的實施限定在一定量度內,而盡力發掘語文的人文精神,將它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相反,那些成效不大和失敗的語文教學,大都過分仰仗科學主義理性方法,超過限度,令其泛濫,從而遏止了語文人文精神的揮灑與展開。
我以為,幾十年語文教學的失誤就感動科學主義的泛濫,人文精神的消遁。而語文教學改革的總趨勢,是人們有意或無意地追求人文精神的漸趨復歸,如強調語言和思維的結合;強調情感教育、文理情并重;強調審美教育;強調語言感覺(語感);強調教學內容貼近學生身心;強調語文教師的人倫情懷與愛、師生主體投入;強調學生表達要有真情實感、真切體驗;強調求異思維、想象力培養;強調教師不同個性形成不同教學風格;還有,在語文教學中引入接受美學,模糊美學,格式塔完形理論等等,所有這些努力,實際就是在不同角度和側面沖破科學主義的樊籬,強化和貫注語文教學的人文精神。
幾十年語文教學科學主義的過度和泛濫大體表現在,過度追求教材體系的邏輯化、教學點的細密化;教學過程的程式化、序列化;教學方法上對語言和內容的透析化、準確理解化;語文知識完全量化;語文能力的訓練層次化;語文考核測試的標準化等等;比如,有人描述,新聞記者能力似乎可按這樣的序列訓練;①語言解碼能力→②組織連貫能力→③模式辨別能力→④篩選儲存能力→⑤概括能力→⑥評價能力→⑦語感能力→⑧閱讀遷移能力。還比如,語文課堂上這樣的現象似乎司空見慣,師問,①本文有幾段?②這段有幾句話?③分成幾個層次?④某句的主語、謂語、賓語是什么?⑤這個動詞為什么用得好?好在哪幾方面?⑥這個比喻的本體、喻體是什么?等等,用冷漠的知識分析取代辯證的語文感受,用大規模的狂轟濫炸、抽筋剝骨,扼殺語言的氣韻和靈動。
科學主義總試圖尋找一套純邏輯的語文教學秩序,而我們也似乎找一種這樣一種秩序。可是我們仔細審視這些“秩序”就會發現,當這些“秩序”越精密,越清晰,就越覺得不像語文教學,而更像數學、物理學。也就是說,科學理性的剖解越深入,就越背離語文教學的本質。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哲學家們總是在他們的眼前看到自然科學的方法,并且不可避免地總試圖按科學所運用的方法來提問題,答問題。這種傾向正是形而上學的真正根源,并且使哲學家們走入一片混沌不明之中”。人們這種對科學主義的執著信仰,有著深刻的人類淵源和民族文化的心態背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涇渭分明的相應的諸如“科學、哲學、經濟”等的學科思想,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體和部分的彼攝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會通。西方文化注重分別差異、主客分離,追求確實性,注重邏輯演繹。自上世紀下半葉,西學東漸,“五四”又歡迎“賽先生”,此后,我們對科學主義的信仰日益加強和執著。科學主義思潮直接導源于17世紀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這種哲學硬把人從他所生存的世界中分離抽象出來,使主客體相分裂,使人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和統治者”,把幾何學的推理或演繹方法應用到哲學,并試圖用力學、生理學原理解釋心理現象。它想念世界是純秩序、合邏輯排列的,受因果律支配的,可以無限分析剖解下去,以至徹底解構還原。
在科學主義理性哲學觀照下,語言完全是外在于人的客體,可以純理性地由大的語言單位向小語言單位解析,由語形向語義解析。篇章可解析為段,段可解析為句,句可解為成分(主謂賓定狀補),成分由詞組或詞構成,詞組和詞又可解析為詞和詞素;每一級語言單位,都是形負載著義,義依附于形,通過析形可以得義。文章似乎是由字而詞,由詞而句,由句而段而篇章,逐級疊加拼合的,文章義似乎是字義相加成詞義,詞義相加成句義,句義相加成段義,段義相加成篇章義。析形得義還可從另兩個角度進行,一是修辭角度,可以通過分析某修辭手段的構造,如此喻分析為喻體、主體、喻詞而得義等等,二是寫作手法角度,如是議論,即可析為論點、論據、論證,如是記敘,則可析為順敘、倒敘、插敘、補敘,時間、地點、人物、經過、結局等等。于是人們潛意識地認為,閱讀、聽話就是由大的語言單位向小的語言單位愛級解構;寫作、說話就是由上的語言單位向大的語言單位逐級重構。這就是以科學主義理性哲學為本位的語言模式的高度抽象,我們的寫作學、閱讀學、文章學等也由此而衍生,它們的概念、理論體系由此而建立。它完全抽去了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個性,否定了語言是人的生命形式,是生命的機制,是活潑潑的人性舒展,是生命的外形與寫照,使我們總想把一切外顯化、準確化、邏輯化,而忽視了語言是非常情意化的,往往要靠體驗感悟來內化,需要在一種情感的催動下,在情境的感染下“激活”、“點燃”,需要表象、想象的高度活躍來支撐符號化、聲音化的文字。這種解構與重構、解析與抽象榨干了、冰釋了語言的濃烈的人情、人性、人倫意向,使之成為了一堆堆僵死、冰冷的語碼。當我們力圖用這種科學主義的理性語言觀去解析一篇美妙的文章之所以美妙時,往往不得要領,不得神韻,解析的結局成為“天在山邊,走近山邊,天又遠;月浮水面,撥開水面,月還深”。科學的力量既有創造性也有破壞性,在這里它起的是破壞性作用。
我認為,要卓有成效的搞好語文教學,就必須動搖人們大腦中根深蒂固的這兩個觀念,一是科學主義的理性哲學觀,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現代語言觀,以及由此衍生的寫作學、閱讀學、文章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