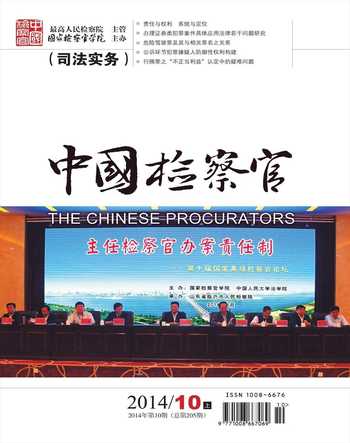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罪數的區分
許佳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狀表述復雜,使得該罪罪數的認定較為疑難。筆者擬對此略述管見。
一、問題的提出及區分標準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往往伴隨著偽造國家機關證件、虛報注冊資本、強迫交易、非法拘禁、銷售偽劣產品、集資詐騙等犯罪,二者之間是從一重罪處罰還是數罪并罰爭議較大。2001年4月l0日《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指出,“實施上述犯罪(即因實施傳銷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情形——筆者注),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2013年11月20日《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6條則是分兩款規定了一罪與數罪的不同情形,但該規定并沒有涵蓋傳銷犯罪活動中經常相伴發生的其他犯罪行為,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由此可見,目前關于傳銷犯罪的罪數認定標準有待進一步厘清和明確。
筆者認為,正確區分本罪的一罪與數罪,既要借鑒刑法學研究的成果,又要考慮傳銷犯罪活動的實際情況,具體應當把握如下因素:
一是犯罪行為的個數。實施一個犯罪行為的,原則上應當認定為一罪。結合本罪,主要涉及哪些屬于想象競合犯的問題,認定關鍵就在于如何把握一個行為的判斷標準。對此,理論界認識存在分歧,但“認為是以自然的、社會的判斷為基礎,而且加以從構成要件的觀點所作的規范判斷的綜合判斷,應當說是妥當的。”[1]
二是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對于存在數個犯罪行為的,理應在考慮行為之間關系的基礎上作出判斷。結合本罪,主要涉及哪些屬于牽連犯的問題。而“牽連犯中的兩個以上的行為,必須是各個行為彼此不屬于同一犯罪構成要件。”[2]對此,認定的關鍵在于兩方面:一方面是牽連關系的判斷。理論上有主觀說、客觀說和折衷說,通說為客觀說,認為數行為之間在其類型上即社會生活的一般經驗上,必須具有通常應當看作作為手段、結果關系的。[3]另一方面是牽連犯的處罰原則。對此,理論上也有不同認識。但結合有關刑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對于牽連犯原則應從一重罪處罰,但刑法有特別規定的除外。這種見解兼顧了刑法規定與理論依據,較為適當。
三是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直接客體種類。犯罪的直接客體是決定犯罪性質的最重要的因素,揭示了具體犯罪所侵害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該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程度。[4]結合本罪,一般而言,數行為觸犯不同種類的直接客體,且必然、同時發生的,原則上宜認定為數罪。
二、一罪的情形
(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犯罪
處理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犯罪的關系,涉及到對《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騙取財物”的理解,即能否將其作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有的學者指出,“騙取財物”是對詐騙型傳銷組織(或者活動)的描述,亦即,只有當行為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具有“騙取財物”的性質時,才成立本罪。[5]這是符合立法本意是。所謂“對詐騙型傳銷組織(或者活動)的描述”,實際上是明確了在認定構成本罪時必須查明“騙取財物”這一本質特征的存在。《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立法宗旨就是處罰組織、領導詐騙型傳銷活動的行為,《意見》第3條也明確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認為被騙,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
筆者認為,“騙取財物”是本罪的構成要件之一,但構成本罪并不需要特別證明行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主要應從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方式認定其“騙取財物”。對于實施組織、領導傳銷犯罪行為,同時觸犯詐騙犯罪的,根據前述行為個數判斷的標準,詐騙行為是兩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屬于一個詐騙行為觸犯兩種罪名的想象競合犯,應當從一重罪處罰。《意見》第6條第1款也對此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同時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和集資詐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根據該規定,如果行為人通過傳銷手段非法籌集資金,大肆揮霍、贈與、行賄;或者抽逃、轉移、隱匿;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或者攜款潛逃等,給投資人造成巨大損失,造成金融管理秩序混亂等,應以集資詐騙罪予以認定,因其量刑要比本罪重得多。
(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關聯犯罪
在傳銷活動中,犯罪分子為了騙取不法錢財,難免會提供一些偽劣產品。對此,有人認為,由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實際上與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是一個行為,屬于一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的情況,成立想象競合犯。[6]對此,筆者認為,從客觀表現上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是假借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騙取財物的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則是在生產、銷售活動中采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等欺詐手段,二者并不是一個行為。同時,“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實際上只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一個幌子或名義,這種所謂的經營活動可能實際上沒有發生。也就是說,生產、銷售偽劣商品行為根本不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因此,此種情況下,同時觸犯兩罪并不符合想象競合犯“行為人只實施了一個行為”的基本特征。
但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相對于傳銷活動而言,屬于高概率出現的行為,會經常用于傳銷犯罪活動之中。根據前述牽連關系的判斷標準,屬于二個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牽連犯情形。鑒于目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對此從一重罪處罰為宜。基于同樣道理,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等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之間亦存在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故亦應以牽連犯認定處罰。
三、數罪的情形
當行為人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采取的犯罪手段侵害了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或者擾亂社會管理秩序,觸犯了多個罪名,一般應當數罪并罰。《意見》第6條第2款明確規定,“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實施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妨害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等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很顯然,從這些犯罪侵犯的直接客體而言,均與市場秩序本身關系不大,且不屬于傳銷活動犯罪中必然、同時侵犯的社會關系,其社會危害性程度明顯增加,對此實行數罪并罰是合適的,罰當其罪。
在此,筆者想對犯本罪同時構成非法拘禁罪的罪數認定作一分析。傳銷犯罪活動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依據的。為了拉人頭,他們不惜采用引誘、脅迫、搜查甚至非法拘禁的手段。有人認為,非法拘禁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存在牽連關系,故應作為一罪處理。[7]對此,筆者并不認同。如前所述,對于牽連關系的認定,應當采取客觀說的標準。事實上,隨著新型傳銷的不斷發展,非法拘禁的情況越來越少,而且非法拘禁與傳銷活動并不存在必然聯系,兩罪之間本質上并不構成牽連犯的情形。還有學者認為,兩罪屬吸收關系[8]。實際上,一個犯罪行為之所以能夠吸收其他犯罪行為,是因為這些犯罪行為通常屬于實施某種犯罪的同一過程,前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后一行為發展的必經階段,后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前一犯罪行為發展的自然結果。非法拘禁明顯不符合吸收關系的基本特征。
注釋:
[1][日]山中敬一著:《刑法總論(II)》,作者轉譯,成文堂1999年版,第923頁。
[2]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82頁。
[3]蘇惠魚主編:《刑法學(第四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頁。
[4]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5]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48頁。
[6]勞娃:《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司法認定》,載《中國檢察官》2013年第3期。
[7]賈宇:《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5期。
[8]李超、肖家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相關問題的探討》,載《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4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