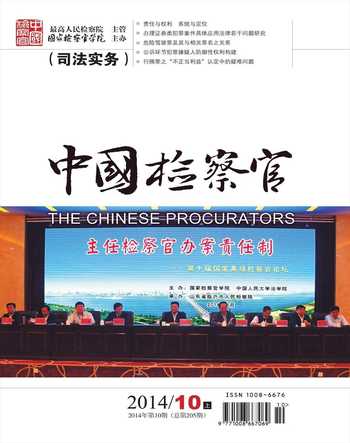公訴環節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權利構建
解兵 刁嵐松 鄭欣
編者按 2012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總則,并在各訴訟環節中均加強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障。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檢察機關應當如何將這一原則落在實處,引起廣泛的討論和思考。本期公訴方略特刊發兩篇關于公訴環節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的文章,分別對一般意義上的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和特別程序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加以探討,以饗讀者。
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權是保障其人權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根據權利的性質和作用可以分為防御性權利和救濟性權利,防御性權利是指犯罪嫌疑人對控方追訴進行抗衡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在檢察公訴環節,應確保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權利的實現。
一、“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及其實現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了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者強迫承認犯罪”,這是被指控的犯罪人享有的最低限度權利保證之一。許多國家以規定被告人有沉默權的方式落實“不強迫自證其罪”的原則。沉默權既然是一種權利,那么使用這種權利就不應當有不利的后果。但是,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卻與該法第118條 “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相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成為虛設。為了更好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檢察機關在審查公訴案件時應當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審查任意自白規則的實施。應當審查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履行了告知義務,告知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法律規定,保證其供述是建立在自愿、真實的基礎上所作的選擇。同時,對于自愿認罪的,要保證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
第二,嚴格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公訴人在審查案件時,一旦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他方式,證實偵查機關取得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通過生理強制或精神強制的方式獲取的,就要堅決予以排除,不能因指控犯罪的需要而加以采納。
第三,要仔細區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解和如實供述的關系。在法庭上,公訴人不應當因為被告人進行辯解,就認為其是認罪態度不好、負隅頑抗,而建議法庭加重處罰。
第四,應當建立沉默權不當行使的不利推定意識。盡管“不能因為沉默而得出對被告人不利的推論”,但是此原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確行使沉默權條件下才能成立,否則,公訴人應當在提起公訴或者庭審時建議法官作出不利于其的推定。例如,當訴訟滿足一定的條件,公訴方提供的證據已經完全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拒絕發言或辯護,公訴人應當建議法官要求其承擔由此帶來的不利后果。
二、辯護權及其救濟
辯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體現一個國家的法治理念與法制建設水平。刑事辯護能夠幫助公安、司法機關把關涉當事人如此重大權利的偵查、批捕、起訴、定罪判刑等工作做準確、做公正,從而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1]在辯護律師依法執業保障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方面,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了許多體現人權保障的規定,但是仍有一些細節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建立審查起訴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時辯護人到場制度
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是避免錯案發生、促進司法公正、增強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措施,而律師在場是從根本上解決刑訊逼供的良方妙藥。新《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收到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但法律未規定已經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在檢察人員訊問時是否有權申請辯護人到場。本文認為這種律師在場權不應局限于偵查階段,可以延伸至審查起訴階段,理由如下:
第一,刑事案件自偵查機關移送至檢察機關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時,案件事實和證據已經基本固定,檢察機關訊問的內容大多是對案件事實的核實、告知相關訴訟權利,此時允許辯護人到場不至于影響案件程序的正常進行。
第二,檢察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可以幫助辦案人員分析判斷案件事實。犯罪嫌疑人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往往更愿意吐露真實想法,并可以減少與司法人員的對抗心理。
第三,審查起訴階段的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會向檢察機關提出相關權利主張,如在偵查階段受到刑訊逼供等。實踐中檢察人員有時為達到懲治犯罪的目的及追求追訴成功率,對這些情況很少理會、敷衍了事。建立辯護人到場制度,可以起到一個監督的作用。
(二)建立為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辯護機制
新《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267條、第286條對指定辯護作了詳細的規定,除了新增的對于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的法律援助的提供主體仍然規定為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法律援助主體的規定擴展到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相對于審判階段而言,審前偵查、審查起訴階段被追訴人的權利更容易受到傷害,因而也更需要得到律師的幫助。[2]新《刑事訴訟法》將法律援助的適用提前至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可提前實現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為其人權保障設置合法屏障;另一方面也利于為那些沒有經濟能力聘請律師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從而保證他們與那些有經濟能力的犯罪嫌疑人享有同等的訴訟權利,實現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盡管如此,從目前司法實踐來看,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似乎仍然沒有擺脫舊法的慣性思維,指定辯護仍然為法院一家之事。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為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辯護并不多見,往往抱著法院會處理的依賴心理,將案件移送了之。本文認為檢察機關公訴環節應當構建完善的指定辯護機制。
第一,指定辯護應實行“何時發現、何時指定”。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如果接到了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或其近親屬申請,或者自行審查時發現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應當”為其指定辯護。這里的“應當”包括“必須”和“立即”兩層意思,“立即”就意味著立刻、馬上,以使符合條件者準確、及時的享受到辯護權。
第二,檢察機關應當對指定辯護的適用情況實行法律監督。對一般刑事案件的審查或者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引導偵查一些大案、要案時,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如果發現公安機關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應當指定辯護而未指定的,或者通過其他途徑發現上述情況的,可通過檢察建議等形式及時指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不受侵害。
(三)建立辯護權救濟制度。新《刑事訴訟法》詳細規定了刑事案件各個階段的辯護權,但均沒有規定辯護權的救濟手段。雖然新《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但是,如果有關機關不予糾正,辯護律師又該如何救濟?如果負責審查的檢察機關久拖不決,辯護律師該如何做?
因此,立法機關或者法律解釋機關需要制定一套辯護權救濟制度,對侵犯程序性權利的行為予以制裁,以切實有效維護辯護權的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注釋:
[1]朱孝清:《刑事辯護與檢察》,載《人民檢察》2013年第3期。
[2]宋英輝:《刑事訴訟法修改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