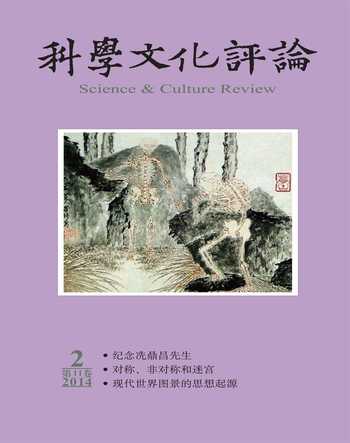解剖學:科學、藝術、教育及其他(Ⅱ)
第一個將人體解剖引入醫學教學的是博洛尼亞大學的蒙迪諾(Mondino de Liuzzi,ca.1270-1326),他于1316年寫成的《人體解剖》(Anathomia corporis humani)是一本近代意義的解剖學著作,內中包含許多插圖,然而直到1478年此書的印刷本才在帕多瓦出現。在維薩留斯的《人體構造》出版之前,蒙迪諾的著作一直是歐洲各大學醫科流行的解剖學標準教科書。主要由于蒙迪諾的影響,解剖學在意大利的一些大學獲得相當的重視,博洛尼亞、帕多瓦、比薩等著名大學里都設有解剖學教授席位和用于公開教學演示的解剖學教室。
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天體運行論》問世的同一年,維薩留斯(AndreasVesalius,1514-1564)發表了他的偉大著作《人體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人類對天體的認識與對自身的認識同時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近代科學就此拉開大幕。這篇短文無須在維薩留斯的生平與貢獻上過多著墨,也不會討論他對蓋倫是修正還是顛覆,筆者的興趣是書中的解剖學圖像。我們知道,《人體構造》初版是由巴塞爾的著名出版商歐泊因努斯(Johannes Oporinus,1507-1568)印制的,除了卷、章、節的裝飾圖外,書中包含大約250幅木版插圖,既有表現肌肉和骨骼的全身圖像,也有描繪血管、神經、四肢、胸腔、腹腔、內臟和大腦的局部解剖圖;最精彩的是前兩卷中的全身圖像,雖然剝去了衣物和皮膚,圖中的模特或立或行,又被置于不同的室內或野外環境中,呈現不同的姿態,即令是一架骨骼也顯得栩栩如生,無論從科學還是藝術的標準來看都是上佳的作品。
書中沒有注明插圖的作者,也沒有其他資料表明出版商工作的程序。毫無疑問,維薩留斯本人提供了所有圖像的草圖,他又委托威尼斯的提香工作室繪圖和制作木版。提香(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是享譽歐洲的大畫家,他的工作室聚集了大批有才華的畫師,其中一位版畫家肯定參與了插圖的制作,他就是來自德國的約翰內斯·斯特凡努斯(Joannes Stephanus of Calcar,ca.1499-1546)。維薩留斯1538年出版的《解剖六圖》(Tabulae Anatomicae Sex)中的三幅骨骼插圖,以及《人體構造》中的作者像就肯定出自其手。維薩留斯在《解剖六圖》的序言中寫道:“沒有人能夠僅僅憑借形象來研究植物學或解剖學,但是繪圖對于知識傳授是一個寶貴的手段”一接著他明確提到斯特凡努斯的名字,希望將后者所繪的骨骼圖印刷出來以使他的學生及其他聽眾受益。圖1(封二)是斯特凡努斯為他制作的木刻肖像,圖中維薩留斯正向觀眾展示手臂肌肉的解剖構造,桌子前端的兩行拉丁數字28、1542則表示他當時的年齡與作畫的年份。
圖25(封三)是《人體構造》第一版的書名頁,描繪的是在一個臨時搭建起來的解剖學教室進行公開教學的場景。畫面中央的人就是帕多瓦大學解剖學教授維薩留斯,他的一只手直接接觸到尸體內臟,這與教授高高坐在講臺上宣講蓋倫的著作,而由解剖手、標本制作員實行操作的老式解剖學演示(參閱本刊上期127頁圖7)截然不同。解剖臺正前方立著一架完整的骨骼,左側立柱上站著一個裸體的活模特,兩者都是作為教學輔助參考物而準備的。畫面中有兩個年輕人在讀書,他們多半是醫科學生而不是相當于高級講師的Reader(參閱本刊上期“圖說”)。有意思的是畫面中擁滿了觀眾,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買票進來的。根據16世紀一位目睹者的記錄,前來解剖學教室觀看示范教學的不僅有醫科大學生,還有市民和修士,但他們必須付錢。資本主義就是不放過任何可以掙錢的機會,即使在它的原始階段。
在西方,座位呈階梯狀排列的解剖學教室被稱為anatomical theater,有人干脆譯作“解剖學劇院”。它起源于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后來傳到北方地區,特別是今屬荷蘭、比利時的低地國家。圖2(封二)是荷蘭畫家斯達克(Andrics Jacobsz Stock,1580-ca,1648)的作品,描繪了一個叫皮特-鮑(Pieter Paaw)的荷蘭醫生1616年在萊頓大學進行解刨學教學的場面。圖中骷髏手上握著一面小旗,旗上的拉丁文是“死亡是人類的最終歸宿”(Mors ultima linea rorom)。圖3(封二)則提供了萊頓大學解剖學教室的內景:整個教室呈圓形,中間是演示用的解剖臺,由下至上共有六排同心圓的坐席,坐席之間和四周墻壁上都有動物和人體的骨骼,正面墻上的壁櫥里陳列著各種解剖學器具,最前面的一對骷髏代表亞當和夏娃,他們中間還可以看到智慧樹與蛇,其余骷髏大多擎著旗子,旗上寫著不同的拉丁文箴言,例如左上角的那面旗上的文字與圖2完全一樣,右上第二面旗上是羅馬詩人荷拉斯的詩句“我們不過是塵土和陰影”(Pulvis et umbraSUIXIUS)。值得注意的是,畫面上還有一些游客,由此顯示了這個場所的雙重功能:上課時是解剖學教室,課余是自然史博物館。
刺激解剖學在西方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對人體美的追求,這方面的代表非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莫屬。早在1487年,他已畫出了著名的維特魯維人(Vitruvian Man)并提出“人是世界的模特”的說法。圖7是繪有維特魯維人圖像的芬奇手稿,將它與圖8給出的一位注明了身體各部分標準尺寸的中國成年男性圖像加以比較是有趣的,后者出自元末著名醫生滑壽(ca.1304-1386)的《十四經發揮》。據醫史專家黃龍翔考證,該書正文主要輯自元代針灸科教授忽泰的《金蘭循經取穴圖解》,圖也很有可能出自后者。無論滑壽還是忽泰,年代都比芬奇略早。
為了讓作品中的人物盡可能貼近真實,達·芬奇相繼在佛羅倫薩、米蘭、帕維亞和羅馬的醫院和醫學院解剖了幾十具尸體,他的興趣并非單純追求精準刻劃人體和個別器官,而是企圖通過解剖人體來了解思維、知覺、智慧和生命的本源等根本性問題,其最終目標是寫作一本關于人體的學術著作。這一計劃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了大量人體解剖的素描和數百頁的研究筆記,其素描作品的意義已經超出繪畫藝術的范疇,從中可以看出芬奇在解剖學和醫學上的大量創見,例如他觀察了嬰兒在母體內的發育過程,研究了眼睛的工作原理,描繪了視覺神經與大腦的聯系,揭示了遠視眼的原因,發現了喉頭、氣管與發聲的關系,研究了頭骨的形態并給出腦部不同的截面圖,摹寫了脊骨的曲度、傾斜度以及脊椎骨之間的結構,發現了臉部肌肉與表情的關聯,說明了疝氣的成因,發現了腹腔的闌尾,準確描述了肝臟硬化和動脈變窄等現象,研究了消化和循環系統,他對心臟和血管的研究可以說是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所發現的血液循環學說的先聲。
2012年,英國皇家收藏基金會在白金漢宮舉辦了一個展覽,去年夏天又將它搬到愛丁堡的國際藝術節上,這個題為“達·芬奇:人體機械學”的專展,通過與現代3D掃描圖像進行比較,向觀眾闡明了芬奇解剖素描的精確程度。有的專家認為,芬奇的觀察精度在許多方面超過了19世紀的權威著作(《格雷解剖學》,這在醫學知識有限、臨床設施粗陋的500年前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達·芬奇的人體解剖素描也非盡善盡美,一個顯著的缺陷是關于女性生殖系統的描繪,與同代畫家相比,他很少畫全身的裸體女性,唯一幸存的一張女性生殖器的素描奇怪地變形,而他關于人體子宮的解剖圖并非寫生,而是臨摹母牛的。專家們認為,這與他個人的經歷與性取向有關,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對女體進行公開解剖是不允許的,當然私下里有人偷偷地干。實際上在16、17世紀的解剖學著作中,很少出現女性身體和器官的圖示。圖14是一部15世紀波斯手稿中保存的孕婦圖像,從人物服飾來看可能來自印度。圖15是一幅中世紀晚期的女性解剖圖譜,其功能不是提供精準的視覺形象,而是傳達身體、疾病、創傷與星官的關系。圖16是提香畫派的一個晚輩菲亞雷提(OdoardoFialetti,1573-1638)的作品,發表在1626年出版的一本解剖學書(De formato foetuliber singularis)中。
中國畫不重視具象的人體,精確的解剖圖更無從談起了,不過出于針灸實踐和教學的需要,醫家和畫師還是留下了一些相關的作品。哈佛大學的日籍科學史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在其所著《身體的語言》一書中,將(《人體構造》與《十四經發揮》中的兩幅側身圖并列比較,并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古代的醫生看不到肌肉,卻鑿鑿有據地逐一標出穴道和經脈?
除了《十四經發揮》中的那些圖外,中國古代流傳最廣的就是一組名為(《臟腑明堂圖》的針灸掛圖了。標明經絡穴位的“明堂圖”起源于何時已無從考據,晉代葛洪(《抱樸子》中提到“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南朝僧人知聰帶到日本的醫藥書籍中包括《明堂圖》和《針灸甲乙經》。唐貞觀年間孫思邈曾據前人考證匯成彩色的《明堂三人圖》,宋代王惟一于天圣年間考訂明堂穴位,撰成(《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并將內容刻石立碑頒布全國。存留至今的《臟腑明堂圖》多為明、清刻本,乃一男性人體圖像,一般包括“正人”、“伏人”、“側人”和“臟腑”四幅掛圖。圖19是明代醫生楊繼洲(ca.1552-1620)所撰(《針灸大成》中的“臟腑之圖”,圖20、圖21則是珍藏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中一份波斯手稿中夾帶的人體解剖圖,據稱原是14世紀的作品。
西方近代解剖學知識于明末傳入中國,早期來華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翻譯了《泰西人身說概》與《人身圖說》兩本書,介紹維薩留斯等人的解剖學工作,是為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近代解剖學著作。兩書印本均極為罕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人身圖說》稿本分上、下兩冊,下冊包括“五臟軀殼圖形”共21幅。據比利時漢學家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考證,《人身圖說》的底本是法國人帕雷(Ambroise Par,ca.1510-1590)所著《普通人體解剖學》的1610年拉丁文版(1561年法文初版)。帕雷是一位法國外科醫生,他書中的大量內容甚至包括插圖都仿自維薩留斯的《人體構造》。后來服務于清廷的法國傳教士們,向康熙帝介紹了包括哈維血液循環發現在內的解剖學新成果。遵照康熙的旨意,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等人在宮中用滿文編纂完成《欽定格體全錄》(1703年),書中包含精美的解剖學插圖,選自哥本哈根大學醫學教授托馬斯·巴托林(ThomasBartholin,1616-1680)編寫的解剖學基礎教程。不過康熙認為“此乃特異之書,故不與普通文籍等量觀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學無術之輩濫讀此書也”。因此僅手抄三部,各自收藏在宮中、暢春園和承德避暑山莊。后來有兩部稿本流出清官,分別被丹麥皇家圖書館與法國自然史博物館收藏。
到此這篇“圖說”的篇幅已經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必須在下面交代一下。本期封面采用的是清代畫家羅聘(1733-1799)所繪《鬼趣圖》之一。羅聘字遯夫,號兩峰,是“揚州八怪”中最年輕的一位。他將八張“鬼畫”裝裱成冊頁形式,是為《鬼趣圖》。本刊所采之畫,但見山石蕭蕭,林木扶疏,一正一背兩具骷髏正在交談,這可能是傳統中國畫中較為準確描繪人體骨骼的唯一例子。不過它們肯定不是寫生的結果,盡管沒有交代來源,研究者還是發現它們與《人體構造》卷1中的全身骨骼第一圖(圖22a)和第三圖(圖23a)的高度相似性。那兩幅圖也曾被不同的歐洲解剖書模仿采用,最終演變成稿本《人身圖說》中的那個樣子(圖22d,圖23d);而羅聘《鬼趣圖》與《人身圖說》之間的相似性更是一目了然:由于采用輪廓線描的畫法,原始圖像中的透視效果已經蕩然無存了。
《鬼趣圖》在當時很有名氣,其上共有一百來個題跋,其中沈大成(1700-1771)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為時最早。羅聘生前曾三上北京(1771-3,1779,1790-8),為他題跋的人中很多是京都名士。曾任翰林院檢討的詩人與書畫家張問陶(1764-1814)在畫上題詠道:“對面不知人有骨,到頭方信鬼無皮,筋骸盡朽還為厲,心肺全無卻可疑。”可見時人對明末清初傳人中國的解剖學知識還是不甚了了。至于羅聘是否看過《人身圖說》的印本或抄本,何時、通過什么途徑獲得那兩幅骨骼圖像的,目前還缺乏充分的資料來說明。
(撰文 夢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