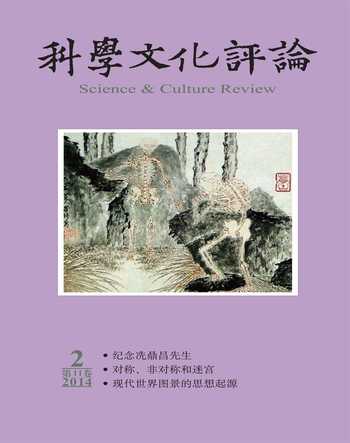原初引力波與暴脹宇宙學
夏樹
摘要:2014年3月17日,天文學家宣布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發現了B模式偏振。根據暴脹宇宙學模型的預言,B模式偏振是宇宙誕生之初產生的原初引力波留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的特殊痕跡。引力波作為廣義相對論的重要預言,至今沒有得到確證,這一發現是引力波理論提出以來關于引力波存在的最重要證據。同時,這一發現強有力地支持了大爆炸和暴脹理論,或對今后宇宙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引力波CMB 偏振B 模式 大爆炸 暴脹
2014年3月17日,哈佛一史密森天體物理中心(Harvard-SmithsonianCenterforAstrophysics)的天文學家宣布,他們已經找到了原初引力波(primordialgravitational waves)存在的重要證據。研究小組利用架設在南極的BICEP2(Background Imaging of Cosmic Extragalactic Polarization,宇宙泛星系偏振背景成像)望遠鏡,觀測到了大爆炸初期所產生的原初引力波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coslnlc Microwave Background,CMB)中留下的痕跡。這一發現不僅是迄今為止關于引力波存在的最直接的證據,還同時揭示了大爆炸宇宙形成之初的物理隋景,對于今后宇宙學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引力波與引力波的探測
1916年,愛因斯坦根據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就像加速運動的電子會產生電磁輻射一樣,加速運動的質量或能量會發出引力波。根據廣義相對論,質量或能量的存在會使得附近的時空產生彎曲,當物質運動時,就會擾動附近的時空,這種擾動像水中的漣漪,以一定的速度(光速)向周圍傳播,形成引力波。引力波所經之處,亦會引起時空的擾動,也就是說,當引力波經過觀測者時,觀察者會發現時空被扭曲了。通常用引力波經過時引起的時空擾動的幅度來衡量引力波的大小。
引力波是廣義相對論的重要推論之一,對引力波的探測也是物理學的重要課題。由于一般物體發出的引力波的可觀測效果非常微弱,對引力波的直接探測往往寄希望于大質量天體的劇烈運動,比如超新星爆發、雙星合并以及黑洞形成等極端天文學事件。二十世紀60年代,被稱為“引力波天文學之父”的Joseph Weber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引力波探測器,使用一根長153cm,直徑66cm的鋁棒,通過測量引力波經過時鋁棒的共振來檢測引力波的存在。之后,還有其他一些測量精度更高的棒狀引力波探測設備陸續建立起來。現在主流的引力波探測裝置是激光干涉儀引力波探測器,通過激光的干涉效應來偵測引力波引起的時空擾動。現正在運行中的幾臺大型的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測器包括建設在美國的LIGO(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意大利和法國合作建造的VIRGO干涉儀等。另外,歐洲與美國正在籌劃LISA(Laser Interferometer SpaceAntenna)項目,將激光干涉儀直接架設在太空中。但是,所有這些引力波探測裝置至今都沒有獲得公認的有效測量結果。
證明引力波存在的第一個突破是在1978年,由Russell Hulse和JosephTaylor通過觀察脈沖雙星系統的軌道周期變化而計算得到。根據廣義相對論,雙星系統在繞質心公轉時會發出引力波,而引力波將帶走部分能量,使得公轉軌道半徑變小,周期變短。Hulse和Taylor在1974年發現了脈沖雙星(binary pulsar)PSR1913+16,經過4年的觀測,他們發現雙星軌道周期變化率與根據廣義相對論計算出來的理論值相吻合,成為了引力波理論提出60年來的第一個定量證據,二人也因此而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二、大爆炸與暴脹模型
另一處有望觀測到引力波的實驗場則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微波背景輻射是大爆炸(Big Bang)之后遺留下的,充滿整個宇宙的電磁輻射。根據宇宙暴脹(cosmicInflation)理論的推測,大爆炸產生的原初引力波將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留下一種特殊的痕跡——B模式偏振(B-modepolarization)。天文學家通過分析BICEP2望遠鏡三年來的觀測數據,最終確認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發現了B模式偏振,即找到了原初引力波存在的重要證據,并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暴脹理論。
宇宙創生的熱大爆炸學說認為,宇宙始于一個密度極大、溫度極高的初態,經過不斷的膨脹而成為今天我們所見的狀態。這一理論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基于這一理論所建立的宇宙學模型成功地解釋了可見宇宙中的諸多觀測事實,例如元素的起源、星系光譜的宇宙學紅移、3K微波背景輻射以及宇宙的大尺度各向同性等,是目前人們普遍接受的主流宇宙學模型,被稱為宇宙學的標準模型。
然而,標準模型也面臨著一些困難,包括奇點問題、視界問題、平直性問題和磁單極問題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古斯(Alan Guth)、林德(Andrei Linde)等人在80年代提出并發展了暴脹宇宙模型。暴脹宇宙模型認為,宇宙極早期經歷了一個短暫但是迅速的指數膨脹階段,在大約10-30s的時間里增大了1030倍。暴脹模型能夠解決標準模型的視界問題、平直性問題等困難,并給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預言。
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與B模式偏振
根據暴脹理論,宇宙暴脹時期產生的原初引力波會在CMB上留下了特殊的痕跡,即B模式偏振。一旦在CMB中找到了B模式,就意味著找到了早期引力波存在的重要證據。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是大爆炸之后遺留的熱輻射。根據大爆炸理論,在宇宙形成早期,由于溫度極高,電子的動能大于其電離能,整個宇宙介質處于等離子體狀態,主要由氫核、氦核、自由電子和光子組成。此時由于自由電子密度很高,光子不斷地被散射,平均自由程很短,整個宇宙是“不透明”的。在大爆炸之后約380000年時,宇宙的冷卻使得絕大部分自由電子被原子核俘獲,形成中性的原子,而光子不再被頻繁地散射,這一過程稱為光子的退耦,或原子復合(recombination)。原子復合過程之后,獲得自由的光子開始穿行于宇宙之間,形成了一個彌漫整個宇宙的背景輻射,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CMB)。
自1965年CMB被發現以來,大量的觀測表明CMB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CMB輻射具有黑體譜,相當于溫度為約2.7K的黑體輻射。第二,整個CMB存在微小的溫度起伏,幅度大約為30μK。第三,CMB輻射具有一定的偏振,其強度和方向隨角度變化而變化。
CMB偏振的成因可以追溯至CMB形成時期宇宙介質溫度的各向異性。CMB偏振由光子的湯姆遜散射(Thomson scattering)產生,如果被散射光子溫度的角分布具有非零的四極各向異性(quadrupolc anlsotropy),將使得散射光具有線偏振。考慮如圖7所示的散射過程,一束電磁波沿-X方向射向中間的自由電子,那么z方向上將能夠探測到偏振方向平行于y軸的電磁波。如果從空間各個方向人射的光是各向同性的,那么z方向出射的光將是各種不同方向偏振光的均勻混合,也就是無偏振。如果入射光并非各向同性,而是具有四極各向異性,例如圖中所示,沿-y方向入射的光(細線段)溫度略高于-x方向的入射光,那么出射光將具有平行于x軸的偏振(細線段)。
CMB偏振只能由上述的湯姆遜散射過程產生,同時要求散射的發生不能太頻繁。如果散射很頻繁,也就是說光子的平均自由程很小,那么溫度不同的區域會因為能量交換而很快地回到熱平衡狀態,由溫度各向異性而產生的偏振效應也會很小。在宇宙歷史中。像這樣能夠產生背景光子偏振所需要的散射條件的時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形成CMB的原子復合階段。另一個則是稍晚些時候宇宙中天體形成時期的再電離(reionization)階段。在原子復臺階段。隨著光子的退耦,散射頻率迅速下降。由各向異性導致的偏振被保留了下來,因而在CMB中應當能夠觀察到全局分布的偏振效應。
根據暴脹模型,光子溫度分布各向異性來源于暴脹時期宇宙中的量子漲落。能夠造成四極各向異性的擾動有兩種,一種稱為標量擾動(scalar-perturbation),即宇宙介質能量密度的漲落,另一種稱為張量擾動(tensor-perturbation),由引力波對時空的壓縮·拉伸效應引起。如圖1所示,想象一組圓形排列的測試粒子,當一列引力波經過時空時,它們會被拉伸成橢圓形,處于不同位置的粒子之間的時空距離就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如果粒子對應光子,那么光子的波長也將被相應地拉伸或壓縮,這就導致了四極各向異性,使得散射光具有一定的線偏振。
因而,CMB偏振場的強度和偏振的方向都與暴脹的過程相關,觀測并分析CMB偏振將能夠給出關于原初宇宙的豐富的物理信息。我們知道,一個矢量場可以被分解為一個無旋(curl-free)分量(類似于靜電場)與一個無散(divergence-free)分量(類似于靜磁場)的疊加。類似地,天空的偏振場也可以被分解成為類電場的E模式(E-modes)和類磁場的B模式(B-modes)的疊加,如圖8所示。兩種偏振模式的區別在于,B模式偏振具有特定的手征性,而E模式則不具有。標量擾動(能量密度漲落)和張量擾動(引力波)都能夠造成CMB偏振,但是E模式偏振主要由標量擾動產生,而B模式偏振則只由張量擾動造成。也就是說,如果能在CMB中找到B模式偏振,那么可以看作是對宇宙暴脹模型的一大支持,同時意味著發現了原初引力波存在的重要證據。
CMB溫度漲落在幾十μK量級,偏振強度應當比溫度變化更小,因而對偏振的觀測要求望遠鏡具有極高的分辨能力。2002年,架設在南極的DASI(Degreeangular Scale Interferometer)望遠鏡首次觀察到了CMB偏振的E模式,偏振強度的變化幅度大約為4μK,這一結果與暴脹模型的預言相符。由于B模式偏振的強度更小,觀測更加困難,直到2014年,同樣在南極工作的BICEP2小組分析了2010至2012三年的測量數據,終于確認在CMB中發現了B模式偏振。根據BICEP2小組公布的報告,觀測到的B模式偏振功率譜很好地符合了目前主流的標準宇宙學模型(人-CDM模型)給出的預言。只有一點出人意料的是,測得的B模式強度比標準模型給出的預言要大一些,小組成員,明尼蘇達大學的Clement Pryke教授表示:“我們本來打算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針,但結果卻發現了一根撬棍。”
四、發現B模式偏振的意義
CMB中B模式偏振的發現具有重大的意義,宇宙暴脹理論的創立者之一Alan Guth認為,這是一個諾貝爾獎級別的重要發現。
首先,發現B模式偏振就意味著找到了原初引力波在CMB上所留下的痕跡,這一發現將成為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又一重要支持。CMB中的B模式偏振是自引力波理論誕生以來,關于引力波存在的最直接的證據,即使不能給懸而未決的引力波存在問題畫上一個句號,也將給未來的引力波探索以巨大的鼓舞。
這一發現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CMB偏振包含了宇宙形成初期的信息,對于我們了解宇宙是如何誕生的至關重要,使得我們能夠在眾多不同的宇宙學模型之間做出選擇,并進一步劃定模型中各個參數的范圍,對宇宙的演化給出更確切的預言。理論物理學家們曾提出過諸多不同的方案試圖解決標準宇宙學模型的困難,暴脹模型盡管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卻并不是唯一的理論;并且暴脹理論本身還有眾多不同的版本,各自給出了不同的預言,這些都亟待宇宙學觀測結果的檢驗。麻省理工學院的Max Tcgmark教授稱,這次的發現將給宇宙學帶來一次“春季大掃除”,對未來宇宙學理論和實驗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CMB偏振作為暴脹模型的預言而得到了證實,是對暴脹理論的重要支持。然而,眾多不同的暴脹理論之中,有很多并不能推出達到可觀測強度的引力波,這些版本或將因此被合棄。暴脹理論的另一位奠基者Andrci Lindc認為,BICEP2給出的數據將淘汰掉90%基于暴脹的宇宙模型。甚至,一直以來十分引人注目的弦理論(stringTheory)或許也需要修正,因為結合了弦理論的暴脹模型所給出的引力波能量也遠低于BICEP2的觀測結果。
另外,還會有一大批非暴脹宇宙模型,例如循環宇宙(cyclic universe)、膜宇宙(ekpyrotie universe)等,面臨被排除的危險。作為暴脹理論的支持者之一,史蒂芬·霍金宣稱自己贏得了與同事,理論物理學家Ncil Turok的打賭,理由同樣是因為后者提出的循環宇宙模型并沒有能夠預言原初引力波的存在。
物理學家一般認為,宇宙大爆炸始于普朗克尺度(1.22×1019 GeV),在這樣的能標下,引力的量子效應是不容忽視的。現有的物理理論,包括廣義相對論與量子理論在內,都不足以描述這個能量尺度之下宇宙的行為。目前物理學的實驗手段還遠遠不能創造如此高能的實驗條件(位于日內瓦的大型強子對撞機能夠到達的能量尺度約為1.4×104GcV),對宇宙誕生初期的物理行為進行研究,因而CMB是獲得早期宇宙信息的最重要途徑。B偏振模式的確認,不僅為以量子理論為基礎的暴脹宇宙模型提供了支持,還同時肯定了量子理論與引力之間存在著更深刻的聯系。自1965年發現CMB以來,到2014年B模式偏振的發現,我們的觀測能力已經提高了超過106倍,這是一個驚人的速度。越來越精確的宇宙學,將能使我們看到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宇宙,幫助我們一步一步地接近物理學的終極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