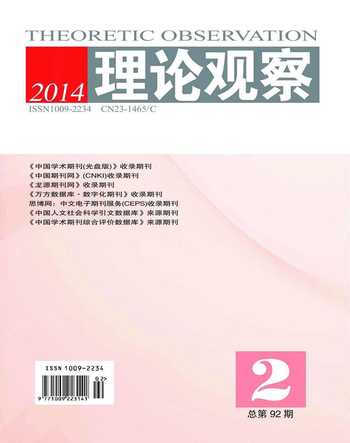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初探
[摘 要]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相比于傳統理性選擇理論更加重視制度的因素,運用“理性人——制度”的分析視角研究政治問題并對制度概念做出了界定。盡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內部對制度概念的理解仍有分歧,但是都基本認同制度的規則性內涵,重視制度的結構性和程序性特征。隨著學術交流的深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也在應對其他理論的挑戰的同時不斷深化發展。研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有助于豐富對制度概念的認識,有助于更好地進行制度建設。
[關鍵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理性人假設;規則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2 — 0027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2
[作者簡介]王禹(1990—),男,安徽安慶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制度主義政治學。
一、“理性”向“制度”的讓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的提出背景
在政治學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革新是理論創新的重要條件。理性選擇理論正是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考察政治過程。理性選擇理論的方法論主要存在三個特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理性人假設和交易政治觀。其中,理性人假設所引起的反響最大。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參與到公共選擇中的行動者都是以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為基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內生的理性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唐斯指出,“理性人僅僅指這樣一種人,他們在自己知識的限度內,運用每單位有價值的產出的最少的稀缺資源投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理性人假設由于能夠保證在分析人的行為時的邏輯一致性與可驗證性,因此成為重要的分析工具。
當運用理性選擇理論研究美國國會行為時,學者們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發現了一個重大矛盾:如果理性選擇理論成立的話,那么美國國會的立法很難保持穩定多數,從而使得從一個議案到另一個議案都會出現阿羅循環現象。然而,事實上美國國會的投票結果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由于既有理論難以回應這一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問題,理性選擇學者紛紛轉向了制度研究。〔2〕有研究成果表明,國會的制度解決了一些立法者們經常會面對的集體行動的困境。〔3〕對制度限制個體行為能力的認識,促使理性選擇理論進一步加強了對制度的研究,由此,理性選擇理論發展成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理性選擇理論到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發展歷程實際隱含了研究視角的改進:
從一維的理性選擇的研究視角轉變到二維的“理性人—制度”的研究視角。首先,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沿用了理性人的前提假設,認為行動者都具有一套內生并且固定的偏好。其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重視制度的作用,認為制度塑造了理性人的決策活動。
總的來說,理性選擇理論將個人假設為社會性內涵不足的而且與制度環境和社會現實缺乏關聯的理性行動個體,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開始逐步重視政治過程中制度的作用。由此可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研究的基本特點即微觀意義上的行為分析與宏觀視閾下的的制度分析的融合。在把握了這種特點后,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
二、分歧與共識: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對制度內涵的理解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內部對于制度的定義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下文將從不同觀點的討論中探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制度觀。
首先,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的規則中心模式將制度界定為規則的集合,一旦成為組織與制度中的成員,就表明他們同意遵循這些規則,并且將從制度的成員關系中獲得利益。該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奧斯特羅姆認為,制度就是一種規則組合,人們據此決定成為某一決策領域成員的資格,決定信息的提供方式,決定應該采取何種行動的具體情境,決定個體行動被聚合為集體決策的方式。〔4〕
第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的決策規則模式制度將制度定義為決策規則,認為制度是避免出現集體行動的困境的手段,它提供一套一致同意的規則,將偏好導入決策過程中。這些規則所需達成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任務或目標。蓋伊·彼得斯在這里指出,在這種觀點中“制度的價值是,規則得到實現認可,因此參與者在加入制度時能夠認識到什么是他要接受的。從理性的角度看,制度提供了一種做選擇的穩定方式。”〔5〕
第三,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的“組織中的個體”模式將制度理解為理性行動者實現自身目標的依據。正如唐斯在《官僚制內幕》中表達的觀點:制度對于理性行動者來說不是一種約束,而更多的是一種依據。而制度是理性行動者傾向于尋求既提高組織績效也提高個人效用的策略的最優選擇。〔6〕
第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的委托——代理模式和博弈論模式將制度視為某種結構。在主張委托——代理模式的觀點的學者們看來,制度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關系結構。而在博弈結構的制度模式中,設計博弈活動的行動者試圖建立一種回報模型,它以利益使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服從。〔7〕
盡管存在理解上的不同,但是,對于制度的定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仍存在一定共識。
首先,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是從“理性人——制度”兩者互動的視角來理解制度的。如果說舊制度主義幾乎沒有為個人影響留下空間,而理性選擇理論忽視制度的因素,那么,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制度能夠塑造個體理性行為,抑制著人們可能的機會主義行為,通過選擇議程上影響替代性方案的范圍和順序,或者提供有關其他行動者的信息和減少不確定性的執行機制,使得制度規制下的理性人能夠通過算計之后的制度性行為實現自身利益。在這里,形塑個人決策是結構的目標。而決策者也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理性個體與制度的互動關系可以理解為“個體塑造著制度,而他們的決策又被先前的制度選擇所塑造。”〔8〕需要指出的是,在贊同“算計途徑”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看來,制度通過向理性行動者提供有關其他行動者行為的確定性程度,改變其期望,以使制度得以影響個人行為。在既定的制度條件下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違反制度則將受到處罰,這成為人們服從制度的理由。
其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更多地將制度界定為規則或者激勵機制,強調制度的規則性內涵。在英語中,Institution主要包含制度和組織等兩種含義。但是,正如柯武剛和史漫飛明確表示的,“組織不是制度” 〔9〕。而且,從上文所述中可見,不管是“組織中的個體”模式抑或委托—代理模式和博弈論制度模式,這些觀點實質上仍將制度理解為某種規則,只不過更加重視其中的結構性特征和程序。
綜上所述,在采用“理性人—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看來,制度基本可以與規則互換。作為規則的制度,因其約束主體行為而具有強制性,因其能夠實現理性行動者的福利而具有激勵性。制度正是因為具有激勵性,所以具有自我強化性,因此產生了制度的穩定性。對此,維恩加斯特解釋道,“因為所有的制度都是潛移默化的,有權改變制度的人沒有動機去改變制度,因此穩定的制度必須具有自我強化機制。”〔10〕需要說明的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制度觀暗含了一個對制度的評價問題。既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把政治看成是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那么,制度的存在就是為了避免這些困境。因此,好的制度就是能夠有效避免集體行動困境的制度。
三、挑戰與應對: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觀的發展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制度觀受到了學界的重視,也獲得了很多批評意見。在學術探討過程中,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不斷完善自身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首先,在歷史制度主義看來,“理性人”的假設將人的行為動機簡單化、固定化。偏好不是與生俱來的,偏好的形成實際上受到了制度的塑造與影響。同時,理性人假設僅僅是理論的假設,難以檢驗。這些學者傾向于將個體看成是達到滿意程度即止的人,而不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人。
針對上述批評,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也開始認識到偏好是從個體與制度的互動中產生出來的,并且逐漸認可了偏好從某種程度說取決于個體所加入的制度,“偏好的固定性問題只能適用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并且只有在制度背景固定的情況下才能使用。”〔11〕正如諾斯所解釋的,如果個體進入制度,如果他們在制度中要取得成功,他們就不得不很快會適應規則和接受制度價值。〔12〕
第二,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不僅包括規則,更包括組織。與此同時,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序、規范,而且還包括認知模式、道德規范等。這種觀點將制度與文化界限打破,將文化也界定為制度。
針對上述批評,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認為,雖然制度確實需要組織的支持,而且規則可以隱含在組織結構之中,而組織使得制度具體化,但是,制度一旦被植入組織便難以被移植,而有效制度的本質特征是普適性,也就是柯武剛和史漫飛所指的“一般而抽象的、確定的和開放的,它們能適用于無數情境。”〔13〕因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雖然重視組織的作用,但仍將制度理解為規則。另外,雖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基于功能主義立場,更加注重制度的效果和制度的設計,往往忽視對制度進行完備的界定,但是學術交流的擴大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進一步加深對制度問題的研究,而且正在從正式制度擴展到非正式制度和文化實踐。
〔參 考 文 獻〕
〔1〕〔美〕安東尼·唐斯.民主的經濟理論〔M〕.姚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5.
〔2〕Peter A.Hall,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 Studies,No.45,1996:836-957.
〔3〕Cf.Barry Weingast and William Marshall,The in-
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6,No.1,1988: 132-163.
〔4〕E.Ostrom(ed.),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M〕.
Beverly Hills:Sage,1982.
〔5〕〔8〕〔12〕〔美〕B.蓋伊·彼得斯.政治科學中的制度理論:“新制度主義”(第二版)〔M〕.王向民,段紅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2—53,63,48.
〔6〕〔美〕安東尼·唐斯.官僚制內幕〔M〕.郭小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7〕何俊志,等.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9〕〔13〕〔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17,115-117.
〔10〕〔美〕羅伯特·古丁,漢斯-迪特爾·克林格曼.政治科學新手冊〔M〕.鐘開斌,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262.
〔11〕何俊志: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交流基礎與對話空間〔J〕.教學與研究,2005,(03).
〔責任編輯:杜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