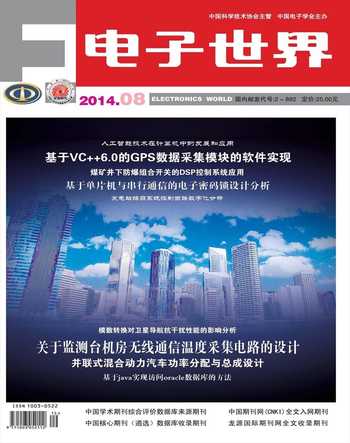顛覆與重構:大數據時代下的廣義收視率
【摘要】傳統的收視率依賴抽樣數據、局部數據和片面數據,大數據能夠獲得全面數據、完整數據和系統數據,大數據的無需抽樣能夠終結傳統收視率的數據造假難題,大收視時代的廣義收視率能夠糾正傳統收視率的統計偏向問題,因此,大數據大收視時代下的廣義收視率能夠努力改進數據統計的先進性、真實性、普遍性,成為診治傳統收視率弊端的一劑良方。
【關鍵詞】收視率;大數據;大收視時代;廣義收視率
所謂收視率,按照全球電視受眾測量指南(Global Guidelines For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GGTAM)的定義,是指根據抽樣調查所估計的,某個特定時段里收看電視人口占所有電視滲透人口的平均百分比,其中電視滲透人口是指擁有電視收視手段或工具的人口(也指所調查空間里的所有人口)[1]。通過收視率調查,獲得樣本家庭或個人在連續觀測的各個時間段內是否收看電視以及收看什么頻道、什么節目等記錄信息。用于收視率指標,包括與收視率相關或由此而衍生的其他指標,如市場占有率、觀眾構成、開機率、總收視點、到達率、觀眾忠誠度等。電視收視率的數據收集方法主要有四種:電話訪問法、日記法、人員測量儀法以及海量樣本回路數據收視研究。隨著電視業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電視節目收視率,現在已成為電視人頭頂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電視臺要依據它來確定哪一個欄目將被淘汰;電視從業者要依據它來確定哪個月可以得到更多的獎金;制片人要依據它來決定一種革新的進退。這一切都緣于廣告客戶依據電視節目收視率來確定投放還是不投放或者投放多少商品廣告。
但是以往傳統的收視率依賴抽樣數據、局部數據和片面數據,而且片面追求收視率使得收視率造假、節目同質化成為眾矢之的。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使得人類第一次有機會和條件,深入獲得全面數據、完整數據和系統數據[2],就像望遠鏡能夠讓我們感受宇宙,顯微鏡能夠讓我們觀測生物,這種能夠收集和分析海量數據的新技術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信息化時代的收視率,成為診治傳統收視率弊端的一劑良方。
一、我國傳統收視率的主要弊端
收視率是一個從西方引進到中國的舶來品,其在我國已經有80年的發展歷程。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國家對電視業的“斷奶政策”、廣告公司唯收視率為其投放廣告的風向標,電視收視率調研在我國得到迅速發展,其在促進我國電視節目的平民化浪潮、擺脫過去“以傳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最終使得中國電視走下傳播者“神壇”,回歸“服務于民”,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市場競爭越激烈,這種純粹的商業利益主導下的傳統收視率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這些弊端主要表現在:
第一,定量抽樣調查容易帶來數據污染。隨著電視業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電視節目收視率,現在已成為電視人頭頂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電視臺要依據它來確定哪一個欄目將被淘汰;電視從業者要依據它來確定哪個月可以得到更多的獎金;制片人要依據它來決定一種革新的進退。這一切都緣于廣告客戶依據電視節目收視率來確定投放還是不投放或者投放多少商品廣告,而這又直接決定了電視節目的生存與否和電視人的收入高低。因此各電視臺各個電視節目均爭相提高收視率。而傳統收視率是基于一定范圍內的定量樣本戶的統計數據,這樣就給賄賂樣本戶的不良操作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造成統計數據的污染。
第二,統計數據范圍狹窄,影響了統計數據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傳統收視率是一種狹義的收視率,是統計在一定時段內收看某一節目的人數(或家戶數)占受眾總人數(總家戶數)的百分比[3],是僅僅基于電視屏幕的收視率。這對于已經信息化、網絡化的今天,其統計數據的范圍過于狹窄,影響了統計數據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因為三網融合背景下,不少觀眾是通過互聯網或移動互聯網收看電視節目,直播、點播、回播,論壇、社區、微博、微信等均成為受眾收看電視節目的新平臺,因此,統計收視率時也應該將這些數據也納入進去。
第三,定量抽查的小樣本數據帶來的高收視率容易以偏概全。受眾的口味千差萬別,但同時受眾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又有著從眾心態。如果定量抽樣的范圍過于狹窄,媒體的議程設置同受眾的從眾心態相結合就會產生強大的蠱惑力,比如越是低俗化、庸俗化的節目越容易契合某些受眾的收視心理,這樣就會造成一段時間一定范圍內的較高收視率。而如果從較長時間來看,這些節目只能紅于一時而不能紅于一世,更不可能遍及更大更廣范圍內的全部受眾的收視行為,因此,這樣的定量抽樣的小樣本數據不足以反應全面范圍內的收視情況。
此外,這種追求片面范圍內、片段時間內的定量抽樣數據也很容易誤導節目的同質化、低俗化甚至庸俗化。因為在高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幻影之下,各電視節目為了追求高收視率,試圖以貌似大眾化實則低俗化的節目來吸引某些受眾,而某個節目一旦紅火,換湯不換藥的類似節目就會跟風而上。在頻道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這種同質化、低俗化的電視節目必定會搶占高雅節目的收視空間,從而會影響另外一部分受眾的收視需求。同時這些高雅節目的長時間潛移默化的吸引力才能達到的收視峰值自然又會脫落于追求較短時間、一定范圍內的傳統收視率的范圍,從而成為了無效數據。
二、傳統電視節目收視率的批判性反思
總體上來說,我國電視節目收視率調查業的發展歷程,也是電視節目收視率在中國不斷引發爭議的過程。在20世紀90 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對電視節目收視率的爭議主要還是有關調查數據科學性、準確性的質疑。2003年后,由于電視低俗化日趨泛濫并逐漸成為一個行業上下普遍關注的問題,電視節目收視率更多地是被視為電視低俗之風或節目質量、品位下降的元兇而遭到批判。例如,時任重慶電視臺臺長李曉楓就針對電視節目越來越庸俗化、低俗化現象,直接提出“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的論斷。
中國有句老話,“蘿卜青菜,各有所愛”。正如同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品牌的電視機一樣,對于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必然因為不同的知識背景、個性喜好、年齡差異等等因素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視節目質量本身的高低與觀眾欣賞人數的多少并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叫座”的并不一定“叫好”,反過來說,“叫好”的也不一定能“叫座”。因此,筆者認為,傳統的收視率太過于追求短時間、一定范圍內的抽樣樣本數據,而這種數據必然是片面的,充其量只是一種了解喜好某一個電視節目的受眾群體的人群數量、性別比例、背景狀況等等的參考數據,不足以反應全部受眾的收視行為,更不能作為短期內節目質量高低的客觀依據。
因此,在商業利益的作用下,傳統收視率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商品經濟體制下電視市場運作的必然結果,是電視節目市場為了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商業利潤原則而處心積慮生產出來的“話語霸權”[4]。電視節目傳統收視率終歸是商業電視的產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帶有商業社會的“原罪”。正如法國文化批評學者布爾迪厄曾指出的那樣,電視節目傳統收視率的出現形成了一個時刻對電視施加影響的經濟場,而電視節目收視率成了一個隱匿的上帝,它統治著這個圈子[5]。
三、顛覆與重構——大數據大收視時代的廣義收視率
傳統收視率的這種數據造假、數據范圍狹窄、片面以及高收視率帶來的電視節目畸形發展現狀一直為社會所詬病。鮑紅志的新作《收視率》以短篇小說的形式生動地展現了調查樣本用戶如何被收買地整個過程,以藝術地手段再現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傳統收視率“數據被污染”的造假現實。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著名導演馮小剛則直接公開炮轟國產劇的收視造假問題。而在前不久針對馮小剛兩會期間再度炮轟收視率造假問題,國家標準委應聲頒布了國內首個電視收視率調查國家標準《電視收視率調查準則》(簡稱“國標”),并將于今年7月實施。但對于這種并無具體法律約束力,僅依靠自愿建議性的標準,其落地執行究竟有無實際效果阻斷收視率造假行徑,尚在各方的懷疑之中。
筆者認為,在三網融合背景下,大數據、大收視時代的廣義收視率能夠為廣受詬病的傳統收視率帶來新的啟示:
第一,大數據集的無需抽樣能夠終結傳統收視率調查樣本被污染、調查數據造假等難題。大數據統計的內容包括電視機頂盒(既包括有線數字電視機頂盒,也包括IPTV和OTT TV等網絡機頂盒)回路數據、基于移動終端視頻消費的回路數據,社會化媒體或具有社交元素的即時通信媒體中有關視頻分享和用戶討論的數據,以及與在線視頻服務有關的ISP服務器后臺數據等共同組成的大數據集[6]。大數據的本質在于無需抽樣,是將自該節目產生以來所有時間段、全部范圍內、全部平臺上的數據統一匯總,這樣就直接杜絕了傳統收視率定量抽樣、樣本戶少導致的賄賂收買樣本戶、以不良手段提高收視率的不良行為。以海量的收視數據來反映真實的收視率,這樣便能從技術上避免了傳統收視率因為抽樣而造成的數據污染問題。
第二,全媒體、大收視時代的廣義收視率能夠克服傳統收視率的片面性偏向。在全媒體時代,不少網絡用戶直接通過網絡來收看電視節目,因此統計收視率也應該將數字電視、IPTV、OTT TV、互聯網平臺的直播、回看、點播等所創造的收視價值均應該納入收視率的統計范圍之中,使得不僅要測量現實社會中直接打開電視機下的收視率,更應該評價電視節目在網絡中的影響力。例如澤傳媒的全屏收視率便是以傳統收視率與網絡收視率之和作為判斷節目整體收視率的指標。這種廣義的收視率較之傳統收視率統計的數字會更為全面,也更為公平。
第三,大數據的多樣性、高速率能夠實現對任一收視行為的發生時點及其持續時長的數據提取,其數據的共享性要求客觀上觸及到單純的市場競爭中商業保護利益的底線,促進了電視節目的公平、公開、公正化競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收視率自身具有的商業社會的“原罪”。
綜上所述,正如維克托在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中所說,“世界的本質是數據”[7],在當今只能惟收視率是瞻的情況下,以大數據的無需抽樣來終結傳統收視率的造假難題,以全媒體、大收視時代下的廣義收視率來克服傳統收視率的片面性偏向,努力消除數據污染,努力改進數據統計的先進性、真實性、普遍性,應該成為改革傳統收視率弊端的一劑良方。
參考文獻
[1]鄭維東.收視率與收視率調查//聚焦收視率[M].王蘭柱.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3.
[2][7]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IV-V,V.
[3]柯宜坤.電視節目有效收視率的思考[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3).
[4]張興龍.收視率時代的文化危機——以《丑女無敵》的收視率現象為個案[J].廣告大觀(綜合版),2009(3):38-40.
[5]時統宇.電視批評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
[6]鄭維東.收視率與大數據[J].廣告大觀(綜合版),2014(05).
作者簡介:常啟云(1978-),女,河南信陽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陽理工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