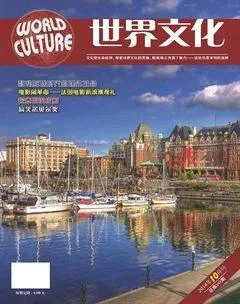馮納古特和他的傳世之作《第五號屠場》
常耀信


馮納古特(Kurt Vonnegut,Jr., 1922—2007),美國當代小說家。由于他的作品中多有科幻成分,世人多把他視為科幻作家,他對此很不以為然。后來他的傳世作品《第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Five)問世,評論界便開始刮目相看了。
馮納古特生于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市。中學畢業后就讀于康奈爾大學,攻讀生物化學專業。“二戰”中應召赴歐洲作戰,被德軍俘虜,關押在德累斯頓(Dresden)城。德累斯頓在“二戰”中是一座不設防的文化城,但在1945年2月13日,盟軍飛機對該城狂轟濫炸,將其夷為平地,13.5萬人葬身火海。馮納古特因被關在一個屠宰場的地下冷藏庫才幸免罹難。這次轟炸和屠殺深深銘刻在他的記憶中。在他看來,德累斯頓的烈焰不啻于世界末日。“二戰”后他在芝加哥大學研究人類學,兼做記者,后遷入紐約東部的斯克內克塔迪市(Schenectady),在通用電器公司擔任對外聯絡工作。該地后來成為他的許多小說的背景,即他稱之為紐約州的伊利翁的地方。馮納古特1950年移居科德角(Cape Cod),潛心創作,作品多刊載于科幻小說雜志上。1969年《第五號屠場》出版,確立了他在美國文壇的地位。1972年他當選為國際筆會美國分會副主席和國家文學藝術協會會員。
馮納古特所處時代的動蕩對他的創作有很大影響,如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的泛濫,60年代的越南戰爭和美國社會的廣泛騷動。馮納古特身處當代世界,深感技術文明社會對人的壓抑。在這樣的社會中,苦難、失望、死亡接踵而至,而人只有逆來順受。因而他認為這個世界沒有目的,沒有秩序,沒有希望。社會的殘酷常使他(以及他小說中的人物)寄情于科學幻想,以期減輕自己的痛苦。馮納古特是一位具有人道主義思想、諷刺筆鋒極為犀利的作家。《自動鋼琴》(Player Piano,1952)提出人與機器的關系問題,指出人應當是世界的主人;《泰坦的女妖》(The Sirens of Titan,1959)說明人要愛自己周圍的人;《夜母》(Mother Night,1961)通過一個犯下“反人道的罪行”的間諜之口,提出“與其可恥地活著還不如死去”的思想;《貓的搖籃》(Cats Cradle,1963)針砭宗教和政治對人民的欺騙,預示科學可能對人類造成的威脅;《第五號屠場》則以辛辣的手筆揭示出戰爭的殘酷,以悲涼的筆調強調了死亡的不可避免。馮納古特是一位富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獨具一格,是20世紀60年代“黑色幽默”風格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和同代作家海勒等人一樣,從20世紀現代生活悲劇的“黑色”中看到幽默,又用幽默來諷刺“黑色”,以期讀者在無可奈何的苦笑之后加深對現實生活悲劇性的認識。馮納古特在文體上也獨樹一幟。他的作品短句較多,情節突兀,敘述秩序常被打亂。這種創作方法也反映了西方當代生活的支離破碎和無目的性。
《第五號屠場》是體現馮納古特人生觀和創作方法的代表作,這本書自傳性很強。它是以1945年盟軍對德國德累斯頓城的大轟炸為背景,基于作者的親身經歷,揭露戰爭罪行的一部力作。同時,該書也描寫了當代美國社會的庸俗不堪,以及一些心靈敏感的人為了擺脫這種生活所做的努力。書中也充滿了作者對許多現代人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死亡問題的思考。馮納古特和小說的主人公一樣,生于1922年,“二戰”中當過戰俘,在德累斯頓大轟炸中,命運和他開了一個玩笑,險些喪命。作為這一悲劇的目擊者,馮納古特清楚地知道,這場轟炸完全沒有戰略價值,僅僅是為了打擊敵人的士氣而讓13.5萬平民白白搭上性命。而且,他后來也了解到,這次轟炸是“二戰”期間最殘酷的一次軍事行動,其毀滅力甚至超過了長島原子彈所造成的罪惡后果。德累斯頓事件標志著馮納古特對科技的持久的不信任、對人類的相互殘害等可怕事實的深刻認識的開始。這些日后成為他的小說和所有作品的中心主題。
小說主要是通過第三人稱敘事者敘說(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由作家親自敘事除外)。故事情節是這樣的:主人公比利·皮爾格林從“二戰”活著回來,在家鄉成為一位眼科醫生,結婚、生兒育女,生活得優裕自在,后來精神開始崩潰。接著他又遇空難,雖然幸免一死,但他的妻子卻在急忙趕往醫院看望他的路上遇車禍身亡。于是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論飛碟和時間旅行,開始在電臺上、在出版的信件中講述他在特拉爾法莫多爾星球上的生活情況。他說他在女兒結婚的那天晚上讓那個星球上來的外星人給綁架走,那些外星人告訴他關于第四空間的概念,在這個空間里,一切時刻都永遠存在著,供人們重新審視和再次經歷。他說之后他就被釋放回地球來傳布這一信息。這時的比利開始在不同的時間地帶來往穿梭。比如進入老年的比利睡下,醒來時卻是他結婚的那天;他1955年從一個門進去,而從另外一個門里走出來時的時間卻是1941年;他說他已經多次看過自己的誕生和死亡,對自己的行動方向和下一步要重新度過哪個階段的生活,他完全不能自控。他經常重新經歷戰時的恐怖,在思想上永遠是個戰俘。小說的重點情節是主人公比利對“二戰”時德國的“再訪”情況:再次看到他的戰友羅蘭·威利死于被押送到德累斯頓去的悶罐車上,看到另一個戰友因在大轟炸后的廢墟里“偷一個茶壺”而被德軍當場處決,回想起另一個戰友保爾·拉扎羅威脅說戰后一定要雇傭一個殺手為羅蘭報仇。比利在一個公園里被槍殺,當時他正在向一群人發表演講,他說他在遭到槍擊時,“死了只有一小會兒,死僅僅是紫光和一陣嗡嗡聲而已”。比利由于戰時的經歷而瘋了。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戰時和戰后表現得像一群孩子,死亡、受害,卻對戰爭的含義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的戰爭很像孩子們的征討。
《第五號屠場》是一部反戰小說。它是一項關于戰爭——人類的自相禍害、關于生活和歷史的嚴重聲明。比利在戰時就已經精神分裂,戰后他的生活似乎很平靜,但是他的頭腦里充滿了死亡和痛苦,再也正常不起來了。小說記錄了發生在他生活中的死亡情況,讀來仿佛一曲對死者和待死者的挽歌。“死亡在戰后仍在繼續”,小說的最后一章作家用自己的聲音這樣直接告訴讀者。在這里作者提到羅伯特·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的被暗殺,以及躺在越南的死尸。書中提及死亡達100余次,每次后面都跟著“就那么回事”這樣一句話,它包含著諸如憤怒、痛苦、無可奈何以及對歷史和生活的厭煩與玩世不恭情緒等多種感情色調,讓人感慨之余又陷入深思。作家似乎在暗示,生活是荒誕、偶然性極強且令人尷尬的,所以人們并不關心它是否已完結。對世間一切的毫無意義感到無可奈何與絕望,使得作家于小說最后將發言權給了一只小鳥。

作為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著名荒誕派小說之一,《第五號屠場》從人物性格刻畫到結構,都是為著表現它的中心主題即生活的荒誕性而服務的。主人公比利即是這種荒誕的醒目的化身:從相貌到行動到講話,他沒有一處不是荒謬和尷尬的。他走路的樣子,和人們交往的情況,他的舉手投足——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個幼稚而糊涂的、沒有什么個人意志而完全受環境和命運所左右的不幸的人。讀一下小說第二章,回想一下他在前線德軍戰線后面讓人踢來踢去的場面,就會了解不管是在戰爭還是在生活中,他是一個多么天真而無能為力的人。他的名字對他的性格頗有象征意義。他的名“比利”立刻讓人聯想到19世紀美國小說家赫爾曼·麥爾維爾的小說《比利·巴德》里天真圣潔的主人公比利·巴德;他的姓“皮爾格林”立刻讓人聯想到17世紀英國小說家約翰·班揚的小說《天路歷程》中主人公“朝圣”的故事。這樣的一個人正是先知人物的胚子,只有這種人在經歷了人生的苦辣酸甜之后,才會悟出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道理來。比利的“福音”是:人對人要充滿愛心,不要以暴力相待。小說的荒誕處之一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卻出自一位半傻之口,而且又經過一個滿腹消極情緒的作家的編輯和修訂,人們對此是不會嚴肅對待的,恰如作家在書中所抱怨的,人們天天“到處放屁,但卻不讓人講不同的話”。果然被他言中了,比利關于外星人的不同的觀察和審視事物的方式,讀者和比利周圍的人一樣,多會權做笑料或無稽之談,掩卷之后也就忘得所剩無幾了。
這部小說的荒誕主題也可以從它的結構安排上看出來。首先,小說對時間這個概念的處理別出心裁。它基本上使用意識流手法,對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的突兀跳躍活動情況,小說表現得逼真而活靈活現。比利的頭腦依照聯想模式運動——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存在、相互連接,他只要遇到一點可以和往昔相連的事情,他的頭腦就立刻沿著時間的軌道飛回到那個過去的時刻去。這樣一來,讀者被迫從一個精神分裂者的角度去觀察世界,連續的完整的生活于是呈現為一幅幅單擺浮擱的畫面或片段,時間的順序完全被打亂,小說的結構顯現出凌亂和龐雜。這種情況出現在小說的十章的整體安排上,也出現在它的每一章中,小說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大拼盤,讓讀者自己去決定取舍、各取所需。
小說的荒誕主題也由它的場景描寫和語言的運用充分表現出來。作家通過這些手段表達出貫穿全書的“黑色幽默”,讓讀者在發笑以后又感到悲傷。比如第四章描寫比利在被運往戰俘營的路上,他險些被甩出悶罐車廂的情景,讓人讀來五味俱全。他就要送自己“上十字架”了,他不斷咳嗽,口里“拉出稀粥”,作者在這種可憐的情況下又同時提出牛頓的運動定律和當時大國為之競爭而引起世人恐懼的火箭,把這些一起并列,讓人情不自禁地發笑,但同時又感到這笑聲竟是建立在一個人的死與活這樣悲慘的事件上的,悲哀之情油然而生。這正是“黑色幽默”的藝術效果所在。
關于《第五號屠場》還要說到,它是美國當代小說革新技巧的典范之一。比如它運用了許多明顯的“準小說”手法。“準小說”的特點之一是告訴讀者,他們所閱讀的實乃作者的杜撰。馮納古特在書中反復申明,他是在講故事。他的口頭語般的 “就那么回事”的作用之一,是給他所說的一切都染上一層令人懷疑的色調。還有他常說的“聽著”似乎暗示給讀者,幕后有人在左右情勢的發展,這樣,一切就都變為虛構,從而打破現實主義手法所力求取得的現實感。此外,作家的露面和評論也讓讀者感到,他們所閱讀的乃是虛構故事。在故事進行中,作家有不少次直接出面評論,而且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他直接敘事,拋開敘事者不用。作家還通過更微妙的方式露面,比如比利一天夜里接到一個醉漢的電話,就暗示作者可能在幕后活動。馮納古特寫的是自己的戰爭經歷,而他的小說讓人鮮明地感受到一種科幻色彩,說明其“準小說”技巧的嫻熟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