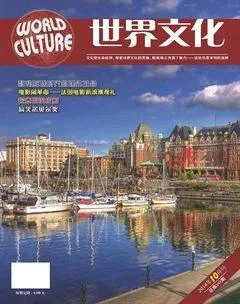符號的魅影
郭星
奇幻小說(Fantastic Literature)的源頭最遠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話。神話中所描寫的眾神和英雄的故事不僅作為原型被當代奇幻小說作者廣泛運用,甚至小說本身就常常以某種失落的神話傳說的面貌出現。具體到英國的奇幻小說,除了西方文學的共同神話傳統——古希臘、羅馬神話之外,古代日爾曼人的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是一個重要的源頭。
盎格魯-薩克遜人作為古代日爾曼人的一支來到不列顛群島,同時也帶來發源于北歐的日爾曼人神話與傳說。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在今天可以從冰島的 《埃達》《薩迦》中看到經過整理的記錄。和古希臘神話的優雅和諧不同,在古代日爾曼人的世界中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冰火兩重天。以主神奧丁為首的眾神與黑暗力量的對立是整部神話的核心。宇宙充滿了戰爭和沖突的陰影。在最后的正義與邪惡之生死決戰后,眾神的國度被毀滅,在一片廢墟之上,新的秩序又將重新建立。正如古英語專家西佩教授所言,北歐神話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邪惡力量獲得勝利。這一傳統后來在英國中世紀的英雄史詩《貝奧武夫》中得以繼承。《貝奧武夫》整部史詩的世界是一個黑暗的世界,貝奧武夫與怪獸及惡龍的戰斗反映的是英雄超人的力量。日爾曼人的神話通常表達的一個觀念就是面對強大的惡的力量,妥協是沒有出路的,無論自身的力量多么有限,勇敢地與邪惡戰斗就是一切意義的所在。到了20世紀,日爾曼的這一神話傳統在奇幻小說中獲得了重生。特別是在“二戰”期間,面對強大的邪惡力量(納粹德國),在看不清前途的情況下,是妥協還是戰斗至死是當時英國人所面臨的重大抉擇。日爾曼的英雄主義告訴人們必須學會在看不清前途,沒有上帝指引的情況下持續地戰斗。這是20世紀奇幻小說運用北歐神話的一個重要原因,它為這個沒有信仰的時代提供了一個異教美德的范本,以其獨有的方式解除了人們的焦慮。
盎格魯-薩克遜時代之后,隨著諾曼人的入侵,新的神話傳統傳入了不列顛群島,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亞瑟王的傳說,并逐漸發展出一個著名的系列故事,就是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的故事。在英國的關于亞瑟王的文學作品中,著名的《高文爵士和綠衣騎士》就包含了明顯的奇幻元素。綠騎士闖入亞瑟王的宮廷提出砍頭游戲的挑戰,高文爵士挺身而出,勇敢地接受挑戰,并砍下了綠衣騎士的頭。綠衣騎士從容地撿起落地的頭顱,聲言第二年還將繼續挑戰,繼而離開。高文爵士信守與綠衣騎士的約定,尋找綠衣騎士的路途中來到一座城堡,入住后受到城堡女主人的誘惑而堅守原則。離開城堡后遇到綠衣騎士,與他比試過后,綠衣騎士宣稱他就是城堡的主人,女主人的誘惑是他故意安排試探高文爵士的。他稱贊了高文爵士的勇敢和高尚,最后高文爵士光榮地返回了亞瑟王的宮廷。這部作品中,綠衣騎士所擁有的強大魔法力量和高文爵士進入的那個充滿魔力的城堡都是具有奇幻色彩的元素。從亞瑟王系列傳說中產生出了現代奇幻小說的一大內容,即一個由想象構造出的騎士世界。
中世紀出現了大量關于基督教的寓言故事。基督徒作家都將創作具有奇幻色彩的虛構故事視為傳達宗教理念的途徑,他們將過去的一些故事模式和形象重新借用,創作出具有奇幻色彩的形象,以此來傳達基督教的觀念。這一時期的宗教寓言故事常常在具有奇幻色彩的形象與基督教理念之間確立一種固定的一一對應關系。例如,無名氏作者的《珍珠》就是一部充滿基督教涵義的作品。如果僅僅在文字層面理解這部作品是不可能的,在其文本背后是與更高的終極意義相關聯的。作品中描繪了一個人為了自己丟失的“珠子”而傷心。這個“珠子”從世俗的角度可視為他的女兒或者一件珍寶。之后他看到了這件珍寶在天堂的幻象。據此,他繼續執迷于解釋這些幻象以尋找這件珍寶,并期待與之重逢。在作品中,主人公試圖以自己的知識和想象來理解來自天堂的啟示卻終不成功,體現了終極真理和人類理解的巨大鴻溝。作品中天堂與人間無法妥協和不能連結的本質差距是人類必須意識到的一個冷冰冰的現實。除此之外,在中世紀的圣徒故事和宗教奇跡劇中有很多關于進入天堂、地獄或者煉獄的歷險故事,這些也都為當代奇幻小說中英雄歷險故事提供了借鑒的模板。
從中世紀末期到文藝復興后的許多重要的英國文學作品中,超自然內容已經不再是作品的主題,而是夾雜在現實題材當中出現的。莎士比亞的許多作品都包含了奇幻的元素,例如《暴風雨》中就存在著一個烏托邦式的奇幻島嶼;而《仲夏夜之夢》中對于仙境的描繪則帶給讀者無限驚喜。當然,他的這些作品僅僅是具有奇幻的性質,超自然僅僅是作品的一個組成部分。《理查三世》《裘利斯·愷撒》和《哈姆雷特》中都出現了鬼魂的形象以引導劇中人物,《麥克白》中的女巫則是麥克白自己心魔的象征,導致他走向了弒君的道路。莎士比亞關注的是人類的精神問題,超自然元素更多地承擔的是推動情節的功能,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從文藝復興開始,隨著地理大發現,新的科學、藝術以及政治觀念的發展,人對世界的認知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在文學作品中,基督教的幻想作品成為這一時期唯一“合法存在”的幻想文學,而這些幻想作品又都被局限在了基督教思想的框架之內。隨著理性意識的增長,特別是從1600年到1750年發展起來的經驗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文學對于超自然的觀照日益被限制在了信仰的藩籬之中。從斯賓塞的《仙后》、班揚的《天路歷程》到彌爾頓的《失樂園》,都是在這一框架之下創作的。
在斯賓塞充滿基督教象征意義的《仙后》中,紅十字騎士的歷險其實可以看作是對上帝真理追尋的隱喻。在這個過程中,人可能會走上歧途,但最終會在上帝的啟示之下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作品最后出現的惡魔就是啟示錄中象征撒旦的惡龍,和惡龍的戰斗就建立在這個啟示真理的故事的基礎之上。紅十字騎士在戰斗中逐漸意識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并且在象征著善的泉水的幫助下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同時,他也走出了自己思想的迷霧,進入到了更為寬廣的終極真理的領域之中。當然,拋開《仙后》的象征意義,我們可以將斯賓塞的作品視為一個創造了另一個世界或者說是架空世界的作品,其中的騎士、巨人、怪獸都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奇幻故事的組成要素。
同樣,班揚的《天路歷程》也是一個關于基督徒通往天堂之路的隱喻。雖然小說中描寫了超自然,但是這里的超自然之地是洗凈罪惡本質的人類靈魂的家園。作家希望讀者在象征的意義上讀這部作品,不希望它被當作單純的虛構幻想。當然,以現代讀者的角度來看,作品中那些具有奇幻色彩的形象會讓我們忘記其本身的宗教含義,因而僅僅在世俗層面來看,這部作品也可作為歷險故事來讀。這應該歸因于班揚對于基督徒旅程中的生動描寫,虛構的幻想既服務于神學思想的表達,同時也作為奇幻作品具有藝術上的魅力。班揚的作品對于20世紀的奇幻小說作家如C.S.路易斯等有深刻的影響。
到了彌爾頓的《失樂園》,作家試圖通過作品為人類的墮落狀態以及上帝對人的懲罰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很多比較激進的讀者包括詩人布萊克,都在他的作品中讀出了身處日益物質化和世俗化的復辟時代,作者內心深處的波動。盡管彌爾頓意在展現由于野心而生的邪惡之源,描繪對于撒旦以及亞當和夏娃的公正懲罰,但是作家對歷經磨難的反叛者撒旦仍然抱有相當程度的同情,作家也更企望讓亞當和夏娃勇敢地獲取知識,而不是安穩地生活在樂園中。
綜上所述,以超自然事物為核心內容的奇幻敘事,從遠古神話時代發端,卻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推進逐漸被壓抑和排除。當人類進入到科學技術高歌猛進的現代社會,啟蒙理性、實證主義的光芒照亮了人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所有超自然神奇事物無所遁形,蒸發殆盡。伴隨著這個過程,關于超自然的神奇敘事也就在文學領域消失了。文學的描寫對象理所當然地被圈定在了經驗現實的范圍之內。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學中的奇幻敘事才再次出現,盡管它一直被主流批評家排擠,但許多創作嚴肅題材的作家也開始了以幻想為內容的創作。“二戰”后,這種文學幻想的傾向并沒有減弱,而是不斷以新的形式出現。
與此同時,大量以超自然事物為描寫對象的通俗小說也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創作潮流。一直到J. R. R.托爾金的《指環王》于20世紀50年代出版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后,這一與遠古神話遙相呼應的以超自然幻想為內容的小說新類型才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以托爾金作品為代表的當代奇幻小說作為一個亞文類崛起之初,就面臨嚴苛的批評,圍繞小說的“真實性”問題,這一類型的小說被指責為“逃避主義”,無法登入文學的大雅之堂。其實,在當代大眾流行文學的幾個類型當中,奇幻小說擁有與其他類型小說不同的獨特性。相對于科幻小說、偵探小說,奇幻小說的面貌喚起讀者許多的回憶。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它不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的新事物,而是和前現代的文學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又是現代社會的獨特產物,是具有現代意識的作者創作出來給現代讀者讀的小說。在這個類型的小說身上,有著多重復雜的內容,反映著當代社會新的深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