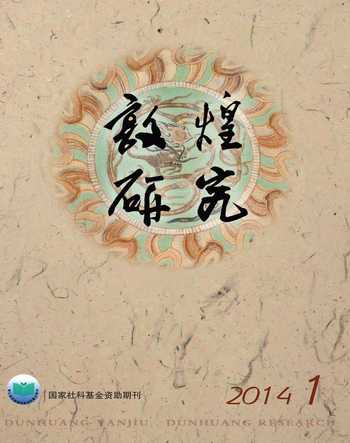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zhuǎn)變與法身思想
內(nèi)容摘要:敦煌佛教一直以漢傳體系的佛教為主流,隨著唐密的興起,密教逐漸將一些顯教的神祇及其功能移植到密教經(jīng)典中,開始吸收或利用顯教的圖像內(nèi)容和構(gòu)圖形式。密教中央法身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四方佛的義理與華嚴(yán)毗盧遮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思想有一致性,密教五方佛是以大乘經(jīng)典和圖像為基礎(chǔ)組織起來(lái)的神祇系統(tǒng),敦煌石窟為我們展示了這一圖像發(fā)展、演化過(guò)程。說(shuō)明顯密結(jié)合、顯體密用是敦煌密教發(fā)展的主流,而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zhuǎn)變就是顯體密用的一個(gè)典型例證。
關(guān)鍵詞:敦煌佛教;顯密五方佛;圖像轉(zhuǎn)變;法身思想
中圖分類號(hào):K879.2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4106(2014)01-0007-14
據(jù)學(xué)界研究以大日如來(lái)為首的密教五佛,是直接依據(jù)《金光明經(jīng)》、《觀佛三昧海經(jīng)》所說(shuō)的四佛思想發(fā)展而來(lái)[1-3]。其中《華嚴(yán)經(jīng)》中能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毗盧遮那佛(晉譯盧舍那佛),至《大日經(jīng)》以大日如來(lái)(摩訶毗盧遮那佛)為中方之佛,發(fā)展為五方佛,在《金剛頂經(jīng)》中最終形成了金剛乘的五方佛或五智如來(lái),標(biāo)志著密教神佛體系的建立和系統(tǒng)化。密教中央法身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四方佛的義理與華嚴(yán)毗盧遮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思想有一致性。密教五方佛是以大乘經(jīng)典和圖像為基礎(chǔ)組織起來(lái)的神祇系統(tǒng),敦煌石窟為我們展示了這一圖像發(fā)展、演化過(guò)程。
一 敦煌北朝至隋時(shí)期的四方佛
大乘佛教以前的佛陀觀,認(rèn)為只有釋迦一佛,在同一佛國(guó)土佛不并出。最初的多佛思想是依時(shí)間擴(kuò)展的,首先形成的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三世佛”的概念,是以釋迦佛為中心的依時(shí)間軸發(fā)展多佛思想。同時(shí),與此相對(duì),依空間軸也擴(kuò)展出了多佛思想,即十方諸佛的概念,以此漸漸形成大乘佛教的“三世十方佛”之說(shuō)。
十方配十佛是在大乘十方諸佛思想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較早的經(jīng)典有鳩摩羅什譯《十住毗婆沙論》、佛馱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jīng)》和《華嚴(yán)經(jīng)》(此經(jīng)十方佛名與前二經(jīng)不同)等,就是來(lái)自從空間方面擴(kuò)大解釋佛陀的多佛思想,或隨此而起的多佛國(guó)土思想{1}。此外,《觀佛三昧海經(jīng)》和曇無(wú)讖譯《金光明經(jīng)》有四方佛,其中《觀佛三昧海經(jīng)》將十方佛、四方佛并記,但兩者四方佛名有出入。以上《十住毗婆沙論》和《觀佛三昧海經(jīng)》十方佛名為同一體系,《觀佛三昧海經(jīng)》、《金光明經(jīng)》的四方佛則屬同一體系,二者四方佛有別,茲列如表1。
隨著大乘佛教的傳布,表現(xiàn)多佛思想的四方佛造像逐漸盛行。據(jù)與以上譯經(jīng)同時(shí)期的《法顯傳》記述,在法顯求法至北印度時(shí),即見到一些表現(xiàn)四佛的四面造像。如“僧伽施國(guó)”崇信佛法:
王益信敬,即于階上起精舍,當(dāng)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后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獅子,柱內(nèi)四邊有佛像……
法顯至“摩竭提國(guó)巴連弗邑”亦見:
凡諸中國(guó),唯此國(guó)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jìng)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揠戟,高二丈余許,其狀如塔。以白氈纏上,然后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yán)各異。[4]
法顯求法至北印度所見精舍后立有石柱,柱內(nèi)四邊有佛像,或見每年的“行像”車,其狀如塔,四邊有龕,龕內(nèi)有坐佛及侍立菩薩,可能即《觀佛三昧海經(jīng)》記述“四柱寶臺(tái)”內(nèi)的“四世尊”——四方佛。
我國(guó)早期石窟中心塔柱四面開龕造像的形式,應(yīng)該受到了印度“其狀如塔,四邊有龕,龕內(nèi)有坐佛及侍立菩薩”的影響。有些中心塔柱四面龕內(nèi)的造像可能就為四方佛,茲舉例如下:
1. 甘肅河西地區(qū)保存有我國(guó)漢地開鑿較早的石窟寺遺址,其中在武威天梯山、張掖金塔寺及馬蹄寺、酒泉文殊山和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都存有中心塔柱窟。一些中心塔柱四面各開一龕,每龕內(nèi)塑一結(jié)跏趺坐佛。如建于北涼時(shí)期的金塔寺石窟,東窟中心柱四面分三層開龕造像,下層每面正中各開一圓拱形大龕,龕內(nèi)各塑一趺坐佛,龕外兩側(cè)塑二菩薩(背面各塑一弟子)。西窟中心柱也四面分三層開龕造像,下層每面正中各開一圓拱形大龕,每龕內(nèi)各塑一趺坐佛,龕外兩側(cè)塑二菩薩[5]。
2. 莫高窟北周第428窟前部人字披頂,后部平棋頂,有中心塔柱,四面各開一圓券龕,龕內(nèi)塑趺坐說(shuō)法佛一身,弟子二身,龕外塑菩薩二身。
3. 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北魏第24窟為平面方形的中心柱窟,基座以上共三層,下面兩層各面開龕造像,均為一趺坐佛二脅侍菩薩。北周第45、46、51、67窟均為平面方形的中心柱窟,中心塔柱四面每面開龕造像,均為一趺坐佛二脅侍菩薩[6]。
隨之,四面像碑、四面造像塔或四面造像柱等也開始流行。在我國(guó)北方尚存有大量四面造像石、塔,其中甘肅、山西、陜西等是較為集中的地區(qū),茲舉數(shù)例于下:
1.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北魏景明二年(501)四面石造像,通高60厘米。造像石四面各開一龕,龕內(nèi)均為一趺坐佛二脅侍菩薩(圖1)。
2. 北魏太昌囗年(532?)石造像塔,為三層樓閣式出檐方塔,通高41.4厘米。四方基座刻有銘文,紀(jì)年有殘損。三層塔身每面開尖栱龕,龕內(nèi)為相同的趺坐禪定像[7](圖2)。
3. 山東神通寺四門塔。位于山東省歷城縣神通寺遺址東側(cè),建于隋大業(yè)七年(611)。塔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開一道小拱門。塔內(nèi)有中心柱,柱四面平臺(tái)上面對(duì)拱門各置石雕趺坐佛像一尊,高123厘米至147厘米,此四佛一般被認(rèn)定為東方阿閦佛、西方無(wú)量壽佛、南方寶生佛、北方微妙聲佛。由寶生佛石座上的造像銘記可知四像最初造于東魏武定二年(544)[8]。
4.現(xiàn)藏日本濱松市美術(shù)館北周保定五年(565)石造四面像,高31.5厘米。整體觀之,即為一無(wú)塔剎的小佛塔。為四面石柱形,下有基座,中間為四面佛龕,龕內(nèi)均一趺坐佛二脅侍三尊像,三尊像姿勢(shì)相似{1}。
還有不少無(wú)造像銘記的四面像塔{2}。由一些金石文獻(xiàn)記載來(lái)看,這些造像碑石多被稱為“四面像”或“四佛”,這在一些造像碑銘中就有記載,茲舉例于下:
1. 北魏建義元年(528)《道勇造彌勒像記》碑文有“敬造彌勒……四面尊像”的銘記[9]。
2. 大魏武定七年(549)《張保洛造像記》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薩”的銘記{3}。
3. 北周保定四年(564)《圣母寺四面像碑》有“造四面像碑”的銘記{4}。
尤其是一些四面造像尚有題名,其中有些題材就是四方佛。如河南省登封縣少林寺所藏東魏天平二年(535)造像碑陰銘文中,有“南方寶相如來(lái),東方阿閦,(中略)北方微妙聲佛,崔進(jìn)合家西方無(wú)量壽”之記載,銘記中的四方佛名與《金光明經(jīng)》和《觀佛三昧海經(jīng)》的四方佛名相同[10]。
引人注目的是,敦煌石窟尚保存有一些題名的四方佛造像。敦煌北朝石窟中心塔柱多為四面造像,尤其是北朝晚期洞窟,如北周第290、428、442窟等,塔柱四面各開一大圓券龕,內(nèi)塑佛像,姿態(tài)相同,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可能是依據(jù)《金光明經(jīng)》所造四方佛[11,12]。北周故事畫大多移至窟頂。入隋則更以窟頂為主,說(shuō)法圖逐漸成為主要題材。有些洞窟四壁中段繪千佛,正(西)壁和南、北壁兩側(cè)中央繪說(shuō)法圖或開龕塑像,東壁門頂也繪說(shuō)法圖,其中就有四方佛造像。有些尚保存有部分造像題記,如敦煌西千佛洞北周第12窟(現(xiàn)編號(hào)第10窟),莫高窟隋代第305、419窟等(圖3)。據(jù)學(xué)者研究四方佛名出自《觀佛三昧海經(jīng)》{1},與經(jīng)典中四方佛列表對(duì)比見表1。
由以上北朝至隋時(shí)期殘存的四佛造像題記來(lái)看,敦煌北朝至隋時(shí)期的四方佛名出自《觀佛三昧海經(jīng)》。但四方佛造像題名并非完全依據(jù)經(jīng)文中的四方佛名,而是將四方佛名與十方佛中四方佛名的混用,可知四方佛是在十方諸佛思想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2}。這些洞窟中繪塑四方佛,應(yīng)是以四方佛代表十方諸佛,說(shuō)明敦煌北朝至隋洞窟四壁千佛中間繪塑說(shuō)法圖,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以四方佛表現(xiàn)十方佛,這應(yīng)與敦煌北朝石窟重禪修觀像的背景有關(guān)。十方佛是這一時(shí)期僧人主要的禪觀內(nèi)容,這在鳩摩羅什譯《觀佛三昧海經(jīng)》、《思惟略要法》等佛經(jīng)中有大量記載,已有專家詳論[13,14]。莫高窟第305、419窟雖是隋窟,但造像題材及其組合都與北朝洞窟一脈相承。因此,以上敦煌四方佛造像題記,對(duì)認(rèn)識(shí)北朝、隋時(shí)期北方四面佛造像題材及所表現(xiàn)的佛教義理具有重要的資料價(jià)值。
二 敦煌唐、五代時(shí)期的四方佛
隨著隋代經(jīng)變畫的繪制,敦煌初、盛唐時(shí)期大多是通壁而繪的大型經(jīng)變,覆斗形窟頂四披則多繪千佛,在個(gè)別洞窟中出現(xiàn)了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的構(gòu)圖,如盛唐第117窟,至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中唐時(shí)期(786—848)開始大量出現(xiàn)。
吐蕃早期新開洞窟沿襲覆斗形頂?shù)男沃疲唔斁亩酁閳F(tuán)花,四披繪千佛,每披中央繪說(shuō)法圖,構(gòu)成四方佛,如第93、111、112、154、470、471、472、474窟等。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晚期洞窟,可分為前后兩個(gè)階段。前段建造于公元9世紀(jì)初至839年左右,如第141、144、145、158、231、369、370窟等。此期洞窟基本沿襲了吐蕃早期洞窟四披的布局和內(nèi)容,盛唐以前頂部?jī)H繪千佛的現(xiàn)象完全消失,皆為千佛中央繪一鋪說(shuō)法圖,有的是在塔中說(shuō)法,或在樹下說(shuō)法,大多數(shù)仍是四方佛內(nèi)容[15]。這些洞窟四方佛的形象大多相同,均為袒右袈裟,雙手說(shuō)法印或禪定印,沒(méi)有相區(qū)別的標(biāo)志。其中第158窟窟頂十方凈土圖像中的密教四方佛(下文詳述)、第231窟四方佛的題名對(duì)認(rèn)識(shí)這一時(shí)期四方佛圖像的變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231窟是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洞窟,也是吐蕃統(tǒng)治時(shí)期有明確紀(jì)年的兩窟之一,此窟由陰嘉政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所建。除了窟頂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外,主室西壁龕內(nèi)塑一趺坐佛二弟子,龕外南側(cè)畫普賢像,上畫四身趺坐佛,從南至北題名為“南方寶相佛、東方不動(dòng)佛、下方囗囗囗、上方廣眾佛”;北側(cè)龕外畫文殊像,上畫四身趺坐佛,從北至南題名“東方不動(dòng)佛、南方寶相佛、西方無(wú)壽佛、北方天鼓音佛”(圖4)。圖像結(jié)定印或說(shuō)法印相。
洞窟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的構(gòu)圖,晚唐至五代、宋而不衰。據(jù)晚唐咸通八年(867)第192窟《發(fā)愿功德贊文》記述:“又于天窗畫四方佛并千佛一千二百九十六軀。”現(xiàn)第192窟主室窟頂(天窗)西披畫千佛,中央趺坐佛一身,東、北披各存千佛一角,可知此窟窟頂四披千佛中央的趺坐佛為四方佛[16]。說(shuō)明晚唐洞窟四披中央說(shuō)法圖中的趺坐佛亦為四方佛。至五代、宋時(shí)期的一些洞窟中,除了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外,還在四披四角繪有四天王像,尤其是一些五代洞窟中保存有四方佛題名:
第100窟窟頂四披上各畫十方諸佛,下部畫千佛,千佛中央各畫說(shuō)法圖一鋪,東、西、北披說(shuō)法圖題記尚存,東披“南無(wú)東方不動(dòng)佛”,西披“南無(wú)西方無(wú)量壽佛”,北披“南無(wú)北方天鼓音佛”,南披題記不存。
第108窟窟頂西披僅存部分千佛,東、南、北披各畫赴會(huì)佛三鋪,下繪千佛,中央說(shuō)法圖各一鋪。其中東、南二披存有題記,東披“南無(wú)東方不動(dòng)佛”,南披“南無(wú)南方寶相佛”。
第146窟窟頂東、南、北披上各畫十方佛赴會(huì)三組,下繪千佛,千佛中央各繪說(shuō)法圖一鋪;榜題分別為:“南無(wú)東方不動(dòng)佛”、“南方寶相佛”、“南無(wú)北方天鼓音佛”。西披上畫說(shuō)法圖一鋪,兩側(cè)十方佛赴會(huì)各一組,下千佛,榜題“西方無(wú)量壽佛”(圖5)。
第261窟西壁佛壇上塑一趺坐佛像、二脅侍菩薩、二半跏坐菩薩、二天王。佛像頭部壁上畫菩提寶蓋、二飛天,兩側(cè)畫說(shuō)法佛各二鋪,四佛均有榜題,從南到北的順序是:“南無(wú)東方旃檀佛會(huì)”、“南無(wú)南方寶德佛會(huì)時(shí)”、“南無(wú)西方無(wú)量佛時(shí)”、“……北方天故佛會(huì)”。
另外,第61、437窟等四披千佛中央的說(shuō)法佛也有題名,但題名已不全,或書寫有誤。此一時(shí)期有些洞窟龕頂或東壁門頂也繪有四方佛,如隋代第397窟外龕頂部五代繪有四佛,初唐第323窟、晚唐第127窟主室東壁門頂五代時(shí)期繪四方佛。其中第323窟從北至南繪三組一佛二菩薩,題名“南無(wú)東方不動(dòng)佛”、“南無(wú)南方寶相佛”、“南無(wú)西方無(wú)量壽”。北方佛可能因布局不當(dāng)沒(méi)有繪。還有一些洞窟的經(jīng)變畫繪十方佛赴會(huì)圖,僅四方佛有題名,以四方佛代表十方佛,如第98窟北壁思益梵天經(jīng)變上部繪十方佛赴會(huì),其中四方佛有榜題,現(xiàn)存榜題“南無(wú)南方寶相佛”、“南無(wú)北方天鼓音佛”。
以上四方佛均繪于五代時(shí)期,即曹氏歸義軍統(tǒng)治敦煌時(shí)期,其中第100、146窟四方佛名完全相同。第98、108、323窟現(xiàn)存題名與第100、146窟相同,所缺佛名也應(yīng)相同。僅第261窟東、南方佛名與以上洞窟有別。
從敦煌唐、五代時(shí)期的洞窟來(lái)看,四方佛題材在這一時(shí)期極為盛行,除了窟頂四披外,還繪于龕頂、龕兩側(cè)及門頂?shù)取S绕涫侵刑频?31窟、五代第98、100、108、146、323、261窟等四方佛題名,為認(rèn)識(shí)這一題材所據(jù)經(jīng)典和義理提供了重要資料。其中除第261窟四方佛名所據(jù)經(jīng)典不詳外,余皆出自唐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其中《序品》有四方佛名:
爾時(shí),薄伽梵于日晡時(shí),從定而起,觀察大眾,而說(shuō)頌曰:金光明妙法,最勝諸經(jīng)王;甚深難得聞,諸佛之境界。我當(dāng)為大眾,宣說(shuō)如是經(jīng);并四方四佛,威神共加護(hù):東方阿閦尊,南方寶相佛,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天鼓音。
《金勝陀羅尼品》說(shuō)到六方佛名:
南無(wú)十方一切諸佛,南無(wú)諸大菩薩摩訶薩,南謨聲聞緣覺一切賢圣,南謨釋迦牟尼佛,南謨東方不動(dòng)佛,南謨南方寶幢佛,南謨西方阿彌陀佛,南謨北方天鼓音王佛,南謨上方廣眾德佛,南謨下方明德佛,南謨寶藏佛……[17]
此經(jīng)所記四方佛有兩個(gè)體系,一是東方阿閦、南方寶相、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天鼓音的四方佛,另一體系四方佛名中南方則為“寶幢佛”。可知此經(jīng)南方“寶相佛”與“寶幢佛”可以混用。
《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為《金光明經(jīng)》之別譯本,四方佛中南方寶相、西方無(wú)量壽與《金光明經(jīng)》譯名相同。東方“不動(dòng)佛”則為“阿閦佛”之意譯,《金光明經(jīng)》均譯作“阿閦佛”,《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除《序品》譯為“阿閦佛”外,其余則譯為“不動(dòng)佛”。《金光明經(jīng)》中“北方微妙聲佛”,《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均譯作“北方天鼓音佛”,為同名異譯。下面將敦煌唐、五代洞窟四方佛題名與《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所記列表對(duì)比(見表2):
此外,筆者在調(diào)查第231窟時(shí)發(fā)現(xiàn),西壁龕外兩側(cè)各繪四佛,北側(cè)四佛題四方佛名,南側(cè)四佛則題東、南、上、下四佛方名(榜題佛名以如上述),對(duì)此頗為疑惑。檢索《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后發(fā)現(xiàn),在《金勝陀羅尼品》“南無(wú)十方一切諸佛”中,也僅記有東、南、西、北、上、下六方佛名,且兩者佛名相同。說(shuō)明第231窟六方佛應(yīng)是依據(jù)《金勝陀羅尼品》所繪,這也為此時(shí)期四方佛出自《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提供了旁證。
另外,不僅五代第98、100、108、146等窟四方佛依據(jù)《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繪制,而且四披四角的東方提頭賴吒天王(持國(guó)天)、南方毗琉璃天王(廣目天)、西方毗樓博叉天王(增長(zhǎng)天)、北方毗沙門天王(多聞天)四天王也與此經(jīng)相同(這幾窟中的四天王圖像大多有榜題)。據(jù)《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序品》可知,四天王既能護(hù)佑四方佛,還可護(hù)法護(hù)世:
東方阿閦尊,南方寶相佛,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天鼓音。我復(fù)演妙法,吉祥懺中勝,能滅一切罪,凈除諸惡業(yè)。及消眾苦患,常與無(wú)量樂(lè),一切智根本,諸功德莊嚴(yán)……護(hù)世四王眾,及大臣眷屬,無(wú)量諸藥叉,一心皆擁衛(wèi)。
敦煌五代洞窟對(duì)《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四方佛及四天王的繪制,應(yīng)與曹氏歸義軍在敦煌的處境有關(guān),曹氏政權(quán)一直處于四面皆蕃敵的困境中,而四方佛“能滅一切罪,凈除諸惡業(yè)”,四天王則可護(hù)法、護(hù)世、護(hù)國(guó)。
由此來(lái)看,敦煌唐、五代時(shí)期延續(xù)了北朝、隋時(shí)期的四方佛圖像,但依據(jù)經(jīng)典、表現(xiàn)形式、繪制位置及功能等均發(fā)生了變化。敦煌唐、五代時(shí)期的四方佛,多出自《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主要繪制于窟頂四披千佛中央,周圍多繪有十方佛赴會(huì),說(shuō)明四方佛代表十方三世佛。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有兩種:一是對(duì)早期顯教四方佛的沿襲,圖像無(wú)明顯特征和區(qū)別。另一是第158窟十方凈土中以生靈座表現(xiàn)的密教四方佛,明顯受到唐密圖像的影響。其在洞窟中的功能,除了四方佛除惡滅罪和四天王鎮(zhèn)國(guó)護(hù)法的現(xiàn)世利益之信仰外,應(yīng)與這一時(shí)期流行的禮懺法會(huì)等功德活動(dòng)有關(guān){1}。
三 盧舍那佛與十方三世佛及四方佛
由上可知,敦煌石窟中的四方佛分別依據(jù)《觀佛三昧海經(jīng)》和《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繪制,在洞窟中四方佛多與十方佛或千佛組合在一起,應(yīng)是以四方佛代表著十方佛,或十方三世諸佛,這從其依據(jù)經(jīng)文也可看出。《觀佛三昧海經(jīng)》卷9《本行品》云:
時(shí)會(huì)大眾見十方佛,及諸菩薩國(guó)土大小,如于明鏡見眾色像。財(cái)首菩薩所散之華,當(dāng)文殊上即變化成四柱寶臺(tái),于其臺(tái)內(nèi)有四世尊,放身光明儼然而坐。東方阿閦,南方寶相,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微妙聲,時(shí)世尊以金蓮華散釋迦佛,未至佛上化為華帳,有萬(wàn)億葉,一一葉間百千化佛,化佛放光。光中復(fù)有無(wú)數(shù)化佛,寶帳成已,四佛四尊從空而下……
經(jīng)中提到觀想十方佛后,并接著觀想四方佛。其間文殊師利觀佛之功德,于是財(cái)首菩薩散花供養(yǎng),花落文殊菩薩上,現(xiàn)出四柱寶臺(tái),臺(tái)內(nèi)有四方佛,四佛以金蓮花散釋迦佛上,又化為百千化佛。
接著又云:
我(十方佛)念昔曾空王佛所出家學(xué)道,時(shí)四比丘共為同學(xué),習(xí)學(xué)三世諸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jiān)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yè)當(dāng)墮惡道,空中聲言:汝四比丘,空王如來(lái)雖復(fù)涅槃,汝之所犯謂無(wú)救者。汝等今當(dāng)入塔觀佛,與佛在世等無(wú)有異。……懺悔因緣從是已后,八十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于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諸佛現(xiàn)前授我記別。東方有國(guó),國(guó)名妙喜,彼土有佛,號(hào)曰阿閦,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國(guó),國(guó)名日歡喜,佛號(hào)寶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guó),國(guó)名極樂(lè),佛號(hào)無(wú)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guó),國(guó)名蓮華莊嚴(yán),佛號(hào)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18]
四方佛與十方佛相同的是,往昔為比丘時(shí),都曾入佛塔禮拜佛像,原來(lái)四比丘“習(xí)學(xué)三世諸佛正法”,不能堅(jiān)持佛法修行,后因入塔觀像,才徹悟懺悔,獲得授記。文中提到“習(xí)學(xué)三世諸佛”和觀想“十方諸佛”,說(shuō)明是以四方佛代表三世十方諸佛。這在《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也能看到:
時(shí)彼菩薩于世尊所……于其四面各有上妙師子之座,四寶所成,以天寶衣而敷其上。復(fù)于此座有妙蓮花,種種珍寶以為嚴(yán)飾,量等如來(lái)自然顯現(xiàn)。于蓮花上有四如來(lái),東方不動(dòng),南方寶相,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天鼓音。是四如來(lái)各于其座跏趺而坐,放大光明,周遍照耀王舍大城,及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諸佛國(guó)土,雨諸天花,奏諸天樂(lè)。
四方佛放大光明可照十方諸佛世界,“過(guò)去未來(lái)現(xiàn)在佛,安住十方世界中”[17]404,422,從四方佛到十方諸佛世界,四方佛不僅代表著十方佛,也函攝著三世十方諸佛。我們?cè)谥性缙谠煜裆暇涂梢钥吹讲簧俦憩F(xiàn)這一理念的實(shí)例,即在四面塔柱各面開龕造像,以四方佛代表十方佛,龕外雕繪千佛代表三世諸佛,形成“十方三世佛”的供養(yǎng)形式。茲舉例于下:
云岡石窟北魏第6、11窟中心塔柱。第6窟中心柱上層、第11窟中心柱下層的四面龕內(nèi)主尊均為一立佛,中心柱四角均雕有千佛。其中第6窟中心柱四角各雕九層閣樓式塔柱,每層雕三坐佛,代表三世佛,與四面龕內(nèi)主尊組成十方三世佛造像。
又如前述西安郊區(qū)查家寨出土、現(xiàn)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的景明二年(501)四面造像石。造像石四面相等,基本為一個(gè)正方體。造像石四面各開一龕,龕內(nèi)均為一結(jié)跏趺坐佛及二菩薩。除下面為天神、力士、供養(yǎng)人,龕外上、左、右均雕刻小佛像,龕內(nèi)四面像與龕周小佛像組成十方三世諸佛的含義非常明確[19]。
在敦煌石窟中則有不同的布局形式,如敦煌北周第428窟中心柱四面各面造一佛二菩薩,四壁上部均影塑千佛。又隋代第302、303窟中心塔柱作須彌山形,下部為方形臺(tái)柱,上層四面龕內(nèi)各塑一趺坐佛;上部作圓形七級(jí)倒塔,各級(jí)影塑千佛。有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早期洞窟所繪千佛圖像就是三世十方諸佛,尤其是北朝至隋代洞窟四壁千佛中間繪塑說(shuō)法圖,有相當(dāng)一部分表現(xiàn)的是十方佛中之四方佛,這些十方佛與其四周的千佛共同組成十方三世佛[20]。隨著敦煌中心塔柱的消失,這一造像形式被移至洞窟的四壁,即四壁繪千佛,中央繪或塑說(shuō)法佛,如隋第305、419窟(東壁均為千佛)等。由此來(lái)看,這些洞窟十方三世佛的布局形式雖有不同,其表現(xiàn)以四佛函攝十方三世佛的義理是一致的。
初盛唐時(shí)期四壁多繪經(jīng)變畫,隨之這一形式又移至窟頂,出現(xiàn)了在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的構(gòu)圖,這一構(gòu)圖形式在中唐開始大量繪制,至五代宋而不衰。其間也有一些變化,如第158窟窟頂繪千佛、赴會(huì)菩薩和十方凈土,其中突出繪有密教生靈座的四方佛。在中唐晚期第7、358、359、361窟中,僅東、南、北披是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的構(gòu)圖,西披不繪千佛,則以中央繪說(shuō)法圖,兩側(cè)各繪五組化佛(十方佛赴會(huì)圖)的形式表現(xiàn)。五代第100窟四披上各畫十方諸佛,下部畫千佛,千佛中央各畫說(shuō)法圖一鋪。第146窟東、南、北披上各畫十方佛赴會(huì)三組,下千佛中央各繪說(shuō)法圖一鋪;西披上畫說(shuō)法圖一鋪,兩側(cè)十方佛赴會(huì)各一組,下繪千佛。尤其是一些五代洞窟四披千佛中央說(shuō)法圖上繪十方佛赴會(huì)圖的形式,更加形象地表明了四方佛代表或函攝十方三世佛的義理。
由上可知,敦煌石窟中的四方佛正是《觀佛三昧海經(jīng)》、《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等經(jīng)文和義理具體而形象的表現(xiàn):四方佛代表著十方佛或十方三世諸佛,四方佛與十方三世佛互相函攝。從北朝至五代、宋,雖然四方佛與十方三世佛的構(gòu)圖形式不同,但萬(wàn)變不離其宗,都是以四方佛表現(xiàn)十方三世佛的義理。
與此同時(shí),我們注意到《華嚴(yán)經(jīng)》以十方一切世界代表窮窮無(wú)盡的宇宙觀,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思想。“盧舍那佛成正覺,放大光明照十方,諸毛孔出化身云”,“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于佛身中現(xiàn)色像”[21]。這是說(shuō)法身盧舍那佛與十方三世諸佛互相函攝,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華嚴(yán)義理。那么由十方三世佛簡(jiǎn)化為四方佛,以四方佛代表十方三世佛也就是自然的事,而盧舍那佛與四方佛的組合,也就是從義理到圖像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一個(gè)必然現(xiàn)象,我們也可看到盧舍那佛與四面佛或四面石像組合的實(shí)例。
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20086號(hào),拓片71.8×80厘米,有北齊皇建二年(561)□善等造四面像記:
夫盧舍無(wú)形,丈陸之容已彰無(wú)名之真名,迷之者沉論(淪)苦海,悟之者出世之常路。政(正)信佛弟子□善等一十三人,遂發(fā)洪愿,敬造四面石像一區(qū)。綰飾訖既,莊嚴(yán)成就,依稀(希)相好,紡(仿)紼(佛)神宜。庶茲福業(yè),仰鐘皇家,國(guó)祚永隆,七世先亡,及現(xiàn)前眷屬,法界眾生,同沾斯善。
皇建□□四月癸……功……
顏娟英先生認(rèn)為這應(yīng)是盧舍那佛與四方佛結(jié)合的早期造像實(shí)例{1}。由盧舍那佛與十方三世佛互相函攝,再由十方三世佛簡(jiǎn)化為四方佛,最終出現(xiàn)盧舍那佛與四方佛結(jié)合的造像。這里四方佛應(yīng)代表著十方諸佛國(guó)土,即十方三世諸佛。另外,松原三郎對(duì)四面造像曾有精辟的論點(diǎn),認(rèn)為四面造像是對(duì)印度窣堵坡外加佛龕佛像的沿襲,是一種塔像合一的供養(yǎng)形式。中國(guó)的這類佛塔可追溯至北涼石塔。北涼石塔的覆缽式塔肩為三世佛造像,此后的北魏樓閣式塔,如曹天度塔四面為千佛造像,曹天護(hù)塔為四面造像,進(jìn)而發(fā)展為北朝的中心塔柱窟。塔是法身、涅槃的象征,造像則代表三世十方佛,可見其以塔像合一表現(xiàn)法身與十方三世佛結(jié)合的源流[22,23]。
盧舍那佛與四面佛或四面石像組合的例子并不多,但其類似的圖像卻不少。有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北周第428窟、隋代第427窟、初唐第332窟等早期盧舍那佛與四壁或窟頂千佛(十方三世佛)圖像的繪制,就是在“十方三世”思想中引入“盧舍那佛”造像,盧舍那佛開始作為十方三世如來(lái)的主尊。而唐代一些洞窟西壁龕內(nèi)主尊與南、北兩壁彌勒經(jīng)變、阿彌陀經(jīng)變(或觀無(wú)量壽經(jīng)變)組合,就是盧舍那佛與代表三世境界的彌勒凈土、十方境界的西方凈土組成的盧舍那“十方三世”境界[24]。尤其是唐代洞窟多為西壁龕內(nèi)主尊塑像與龕外兩側(cè)繪文殊、普賢像組成的法華三尊或華嚴(yán)三圣像形式[25],其龕內(nèi)主尊盧舍那佛(釋迦如來(lái))與窟頂四披所繪四方佛及十方三世佛,應(yīng)具有法身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含義。同理,窟頂四披以十方三世佛為代表的四方佛與龕內(nèi)主尊盧舍那佛可形成五方佛造像,其中中唐第231窟龕內(nèi)外繪塑五方佛像和五代第261窟西壁佛壇五方佛造像應(yīng)是以上組合的延續(xù)或另一表現(xiàn)形式。
第231窟五方佛已如上述。第261窟西壁佛壇上為一佛二菩薩塑像,主尊趺坐于蓮座上,左手撫膝,右臂舉于胸前,手殘,兩側(cè)各一半跏坐菩薩。主尊兩側(cè)各畫弟子、天龍八部,上方兩側(cè)分繪兩組說(shuō)法圖:“南無(wú)東方旃檀佛會(huì)”、“南無(wú)南方寶德佛會(huì)時(shí)”、“南無(wú)西方無(wú)量佛時(shí)”“……天故佛會(huì)”,其中“天故佛”,即“北方天鼓音佛”。可知所繪為四方佛,與主尊組成五方佛造像(圖6)。此窟東壁門頂繪盧舍那法界立像,與門南、北兩壁騎獅文殊、騎象普賢赴會(huì)菩薩組成華嚴(yán)三圣像。因此,相對(duì)的西壁佛壇上的一佛二菩薩造像,也應(yīng)是華嚴(yán)三圣造像,其主尊也就是法身盧舍那像。這也是一組身份明確的盧舍那佛與四方佛結(jié)合的五方佛造像實(shí)例。
總之,不論是經(jīng)文,還是造像,都說(shuō)明四方佛代表十方三世諸佛,受著《華嚴(yán)經(jīng)》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思想影響,敦煌石窟中盧舍那佛與十方三世佛組合圖像的繪制,形成了盧舍那佛與四方佛組合的五佛造像,即大乘顯教的五方佛造像,其中第231、261窟的題名五方佛圖像就是典型例證。
四 敦煌金剛界五方佛圖像的成立
眾所周知,密教大日如來(lái)的形成受到《華嚴(yán)經(jīng)》的影響,從華嚴(yán)教主毗盧遮那佛演變而來(lái),只是為了與華嚴(yán)毗盧遮那相區(qū)別,在其名前加了“摩訶”(大)一詞,毗盧遮那就成了密教的摩訶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lái))。大日如來(lái)成為密教最根本的崇拜對(duì)象,也是密教哲理的核心象征。
隨著善無(wú)畏《大日經(jīng)》的譯出,出現(xiàn)解釋法身的中央大日如來(lái),多佛思想乃轉(zhuǎn)變成統(tǒng)一的宇宙觀,至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經(jīng)典不空譯《初會(huì)金剛頂經(jīng)》(別稱《真實(shí)攝經(jīng)》)中,形成了以大日如來(lái)為中尊的金剛界五方佛,標(biāo)志著密教神佛體系的建立和系統(tǒng)化。茲以《初會(huì)金剛頂經(jīng)》以及相關(guān)的經(jīng)軌所說(shuō)的圖像為準(zhǔn),將五方佛體系的一些特征列表如下(見表3){1}:
密教中央法身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四方佛與華嚴(yán)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義理有一致性。善無(wú)畏《大毗盧遮那經(jīng)廣大儀軌》:“瑜伽者觀察,一身與二身,乃至無(wú)量身,各各住三昧,咸皆受佛化,愿生華藏海,同入于一體,成大曼荼羅。”[26]與《華嚴(yán)經(jīng)》“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實(shí)際上是同一義理。對(duì)此華嚴(yán)四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yán)經(jīng)隨疏演義鈔》做了明確說(shuō)明:
十方諸佛皆我本師海印頓現(xiàn)……且如總持教中,亦說(shuō)三十七尊,皆是遮那一佛所現(xiàn),謂毘盧遮那如來(lái),內(nèi)心證自受用,成于五智。從四智流四方如來(lái),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閦如來(lái),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lái),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wú)量壽如來(lái),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lái),法界清凈智即自當(dāng)毗盧遮那如來(lái)。[27]
十方諸佛為“我本師”(華嚴(yán)毗盧遮那佛)頓現(xiàn),密教“三十七尊”(金剛界五佛、二十菩薩、四攝、八供養(yǎng))為“遮那一佛”(金剛界大日如來(lái))所現(xiàn),說(shuō)明《華嚴(yán)經(jīng)》主尊毗盧遮那佛化現(xiàn)十方諸佛與金剛界大日如來(lái)所現(xiàn)四方佛等三十七尊的義理相通。隨著密教的傳播,我們從敦煌金剛界五方佛的形成可以看到這一義理的表現(xiàn)以及毗盧遮那到大日如來(lái)的圖像轉(zhuǎn)變。
不空一代可謂唐密的大弘時(shí)期,而唐密圖像的完備亦在這一階段。不空在天寶年間為護(hù)法護(hù)國(guó),“請(qǐng)福疆場(chǎng)”,曾長(zhǎng)期在河西弘密。從敦煌寫經(jīng)和石窟造像可以看出,應(yīng)對(duì)敦煌密教的繁盛產(chǎn)生了影響。自盛唐以后,密教圖像在敦煌大量出現(xiàn),且一直持續(xù)發(fā)展,與不空不無(wú)關(guān)系。中唐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shí)期,與中原佛事聯(lián)系不斷,密教圖像開始大增。榆林窟中唐第25窟胎藏界大日如來(lái)與八大菩薩圖像中大日?qǐng)D像作菩薩形,頭戴寶冠,頸飾項(xiàng)圈,曲發(fā)披肩,趺坐施定印,但榜題則為“清凈法身盧舍那佛”。一方面說(shuō)明受敦煌華嚴(yán)思想和毗盧遮那法界圖像流行的影響[28],敦煌密教習(xí)慣將大日如來(lái)以華嚴(yán)教主盧舍那佛(毗盧遮那佛)稱之;另一方面也說(shuō)明敦煌華嚴(yán)毗盧遮那佛向密教大日如來(lái)尊格和圖像的轉(zhuǎn)變。
至吐蕃晚期前段洞窟(9世紀(jì)初至839年左右),在第158窟窟頂與自然方位相合的十方凈土圖像中出現(xiàn)了密教四方佛圖像。位于東方凈土的阿閦如來(lái),身呈黑色,右手施降魔印,坐象座;南方凈土的寶生如來(lái),身呈黃色,左手施與愿印,坐馬座;北方凈土為不空成就如來(lái),身呈綠色,手印不明(圖像剝落),坐金翅鳥(迦樓羅)座;西方阿彌陀如來(lái)的形象,則與初唐以來(lái)西方凈土中的表現(xiàn)形式相同,下部殘損,其乘座不清。其中除西方阿彌陀佛外,東、南、北與金剛界四方佛的生靈座完全相同,身色、印契基本相符[29]。但這一時(shí)期四方佛圖像仍以北朝以來(lái)的顯教四方佛為主流,只是大多為依據(jù)《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所繪東方不動(dòng)、南方寶相、西方無(wú)量壽、北方天鼓音的四方佛。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四披繪四方佛的洞窟中出現(xiàn)了十字交杵蓮花井心,即蓮花中繪十字金剛杵的圖案。
如第370窟主室窟頂四披畫千佛,千佛中央各一坐佛,藻井畫交杵蓮花井心(圖7)。又如西千佛洞第18窟四披畫千佛,千佛中說(shuō)法圖各一鋪(東、北、西披大面積崩毀),藻井畫交杵蓮花井心。十字金剛杵,又稱羯磨杵,是以三股金剛杵組合成十字形,為密教的重要修法道具。三股四方打開的金剛杵有十二股叉,表摧破十二因緣之義。十字金剛杵也表三摩地?zé)o動(dòng)搖,豎窮三世,橫遍十方之意。“豎的一支金剛杵,表體性之豎窮三際,歷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永恒不變;橫的一支金剛杵,表體性之橫遍十方,遍滿法界,無(wú)所不在。這種特性,與毗盧遮那如來(lái)所代表的三世十方思想以及在時(shí)空上的永恒性是一致的。”{1}郭祐孟先生認(rèn)為藻井井心繪十字交杵,不是明確的密教形象——大日如來(lái)(摩訶毗盧遮那佛),但可能有暗喻大日如來(lái)的含義[30]。因而,第370窟等窟頂十字杵應(yīng)有暗喻大日如來(lái)的含義,與四披千佛中央的說(shuō)法圖形成五方佛。這是顯密結(jié)合的表現(xiàn)形式,即井心密教“十字金剛杵”暗喻的大日如來(lái),與四披顯教四方佛代表的三世十方佛的組合。因此,可以說(shuō)第370窟主室窟頂?shù)臉?gòu)圖是敦煌五方佛圖像的濫觴,也是窟頂密教五方佛構(gòu)圖形式的雛形。這些新因素是顯教五方佛向密教五方佛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一個(gè)重要交匯點(diǎn)。
公元838年吐蕃贊普達(dá)磨滅法和公元845年唐武宗會(huì)昌廢佛,前者敦煌遠(yuǎn)處邊陲,后者敦煌已是域外,因此,這里的密教繼續(xù)發(fā)展。在建造于9世紀(jì)40年代至大中二年(848)的后段洞窟中,洞窟窟頂壁畫出現(xiàn)了進(jìn)一步的變化。后段洞窟現(xiàn)存洞窟四個(gè):第7、358、359、361窟[15]。此四窟窟頂有一些共同特點(diǎn),僅東、南、北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西披不繪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兩側(cè)各繪五組化佛(十方佛赴會(huì)圖)。而且,說(shuō)法圖下有綠色或紅色的蓮池,有的還有孔雀、迦陵頻伽、化生天人及各種樂(lè)器在空中飛舞的情形。這些都與阿彌陀凈土和無(wú)量壽佛凈土中的西方凈土十分相似,進(jìn)一步表明西披表現(xiàn)的就是西方無(wú)量壽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無(wú)量壽佛說(shuō)法圖或佛座下方繪有孔雀,以有別于密教生靈座的形式表明身份(圖8),說(shuō)明四披千佛中央說(shuō)法圖仍是四方佛內(nèi)容。此四窟東、南、北披三佛的圖像有別,其中第7、358、359窟沿襲了傳統(tǒng)的四方佛形象,應(yīng)是《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中東方阿閦、南方寶相、北方天鼓音的四方佛系統(tǒng)。
而第7窟,尤其是第361窟窟頂出現(xiàn)了明顯變化。一是窟頂井心不僅繪蓮花十字交杵,而且在藻井凹進(jìn)的四壁上每壁各繪一天王二菩薩(第7窟四壁有殘損)。二是第361窟頂東、南、西、北四披說(shuō)法圖繪有象、馬、孔雀、金翅鳥的生靈座。
第361窟四披中央四佛生靈座明顯是密教方位佛的標(biāo)記,進(jìn)一步表明了密教四方佛形象。井心十字交杵與四披四方佛形成的五方佛構(gòu)圖,應(yīng)是對(duì)前段第370窟井心十字交杵與第158窟密教四方佛相結(jié)合的表現(xiàn),具有金剛界五方佛的雛形。此窟是吐蕃時(shí)期開鑿的密教洞窟,據(jù)研究井心十字交杵與藻井凹進(jìn)四壁的四大天王和八位菩薩應(yīng)是一密教壇城,整個(gè)窟頂“開啟了敦煌五方佛曼荼羅的先河”[30,31]。
晚唐敦煌張氏歸義軍時(shí)期,與中原交往頻繁,密教圖像的數(shù)量、種類亦不斷增加。這一時(shí)期莫高窟第14窟密教圖像極為豐富,但仍沿襲了傳統(tǒng)的四方佛圖像,窟頂五方佛的構(gòu)成形式則更趨明確,不僅四披千佛中央繪說(shuō)法圖,在井心交杵四方也繪有四方佛說(shuō)法,形成兩重五方佛圖像{1}。從法門寺地宮出土咸通十二年(871)比丘智英造銀寶函來(lái)看,中原金剛界五方佛曼陀羅圖像晚唐時(shí)期已相當(dāng)成熟[32]。但是,敦煌至晚唐時(shí)期,除了可能隱喻大日如來(lái)的井心十字交杵與四方佛組合的五方佛形式外,并無(wú)成熟的密教五方佛圖像,即本尊明確的五方佛圖像出現(xiàn)。
五代宋初敦煌屬曹氏歸義軍統(tǒng)治時(shí)期,與中原關(guān)系較張氏時(shí)期更為密切,瓜沙曹氏既奉中原正朔,又貢北方遼國(guó),相互聯(lián)系頻繁,其密教藝術(shù)亦更趨繁盛。敦煌開始出現(xiàn)中尊(大日如來(lái))明確的金剛界五方佛圖像:
1. 洞窟中的五佛曼陀羅
榆林窟第35窟東壁北側(cè)五代繪五智如來(lái)曼陀羅,應(yīng)是敦煌石窟現(xiàn)存較早的金剛界五佛曼陀羅。此窟開鑿于唐代,五代、宋重修,甬道南壁宋畫曹延祿供養(yǎng)像。圖中央為大日如來(lái),坐五獅座,雙手置于胸前,手印不清(智拳印?)。四角為四方如來(lái)。左下方為東方阿閦如來(lái),坐五象座。右下方為南方寶生如來(lái),坐五馬座。右上方西方阿彌陀如來(lái),坐五孔雀座。右上方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lái),坐金翅鳥座。五方佛俱戴寶冠,人物造型則與五代顯教如來(lái)形象無(wú)異,圖兩側(cè)及上方畫千佛。也表現(xiàn)了法身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十方三世佛的思想。
又如莫高窟“天王堂”土塔頂部五方佛。天王堂為曹延祿及其夫人于闐公主修建,門上保存有曹延祿發(fā)愿文,時(shí)間大體在太平興國(guó)九年(984)前后,堂內(nèi)繪塑內(nèi)容以密教為主{2}。天王堂頂部為穹隆頂,中央繪大日如來(lái),頭向東,戴寶冠,菩薩裝,雙手重疊于臍下。大日如來(lái)東、西、南、北方各繪五尊佛,應(yīng)是代表東方阿閦、南方寶生、西方無(wú)量壽、北方不空成就。在每一方佛外,分別繪代表四方佛的三昧耶形,即三股金剛杵(東方)、寶石(南方)、蓮花(西方)、羯摩杵(北方),與中央大日如來(lái),形成金剛、寶、蓮花、羯摩五部,代表金剛界五智。天王堂頂部繪制的應(yīng)是金剛界五佛曼陀羅。另外,南、北壁及東壁門兩側(cè)上方則繪有十方佛赴會(huì),以表現(xiàn)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十方三世佛的思想。
2. 金剛界五佛曼陀羅絹畫
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收藏于法國(guó)集美博物館(Guimet Museum)的金剛界五佛(MG.17780),是歸義軍時(shí)期(9世紀(jì)后半—10世紀(jì)后半)的作品,高101.5厘米,寬61厘米(圖9)。五趺坐佛,雙手均平置于腹上。中央金色的大日如來(lái),手持法輪,坐獅座;右下方白色的東方阿閦佛,手持金剛杵,坐象座;右上方青色的南方寶生佛,手持寶珠,坐馬座;左上方赤色的無(wú)量壽佛,手持蓮花,坐孔雀座;左下方暗綠色的不空成就佛,手持羯磨杵,坐金翅鳥座。各佛旁配以兩身菩薩(八供養(yǎng)),下部繪有八吉祥文、三昧耶形和供養(yǎng)人等[33]。
3. 金剛界五方佛彩繪紙本
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收藏于法國(guó)集美博物館(P.4518-7),是9—10世紀(jì)的作品。高23.6厘米,長(zhǎng)58.5厘米(圖10)。以五佛冠或五智寶冠代表五佛。彩繪一排五尊佛像,中尊高,兩側(cè)四尊等高。每佛位于連珠火焰紋龕中,俱頭光和身光,均戴五佛冠,趺坐蓮座上,雙手平置于腹前持寶物。中間手持法輪者,為大日如來(lái)。右側(cè)第一身手持金剛杵,為東方阿閦如來(lái);第二身手持寶珠者,為南方寶生如來(lái);左側(cè)第一身手持蓮花,為西方無(wú)量壽如來(lái);第二身手持羯磨杵,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lái)。
由上來(lái)看,至五代、宋時(shí)期敦煌形成了尊格明確的以大日如來(lái)為中尊的金剛界五方佛圖像,其五方佛圖像的方位、生靈坐、三昧耶形及身色等與密教經(jīng)軌基本相符。西夏至蒙元時(shí)期藏傳密教異軍突起,成為敦煌的主流,漢傳密教日漸衰落,但五代、宋時(shí)期的五方佛圖像,不論在洞窟中的布局、構(gòu)圖,還是圖像內(nèi)容,都對(duì)藏傳密教五方佛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四 結(jié) 語(yǔ)
綜上所述,通過(guò)對(duì)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分析,我們有以下認(rèn)識(shí):
1. 法門寺地宮出土唐咸通十二年(871)比丘智英造銀寶函上的金剛界曼陀羅五方佛已相當(dāng)成熟。但從敦煌石窟五方佛的發(fā)展軌跡來(lái)看,成熟的五方佛圖像至五代、宋時(shí)期才形成,并非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敦煌密教五方佛在中唐初期就已出現(xiàn)[24]248-249。
2. 敦煌金剛界五方佛圖像是在大乘三世十方思想上發(fā)展和形成的,在敦煌石窟中,既可以看到顯密五方佛的形成,也可以看到其發(fā)展、變化的過(guò)程。在北朝禪觀思潮影響下表現(xiàn)十方三世思想的四方佛圖像,隨著唐、五代覆斗形洞窟的出現(xiàn)和四方佛護(hù)法佑世、禮懺法會(huì)的流行,成為窟頂四披的主要構(gòu)圖;其間華嚴(yán)思想的流布和法身盧舍那法界像的繪制,出現(xiàn)了在“十方三世”中引入法身“盧舍那佛”,以表現(xiàn)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的法身思想的形式,即盧舍那佛與四方佛代表的三世十方佛的組合圖像。隨著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shí)期密教的盛興,密教大日如來(lái)與華嚴(yán)毗盧遮那佛在信仰主體和宇宙觀上的一致性,為法身如來(lái)從華嚴(yán)盧舍那佛向密教大日如來(lái)尊格及圖像的轉(zhuǎn)變提供了義理基礎(chǔ),開始在四披四方佛與交杵(大日如來(lái))井心組合的形式中,引入了密教四方佛,出現(xiàn)了密教五方佛的雛形,至五代、宋時(shí)期形成了主尊身份明確的金剛界五方佛圖像,完成了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zhuǎn)變。
3. 從敦煌五方佛圖像來(lái)看,既有表現(xiàn)華嚴(yán)盧舍那佛化現(xiàn)“十方三世諸如來(lái)”法身思想的顯教五方佛——盧舍那佛與顯教四方佛的組合;又有表現(xiàn)大日如來(lái)化現(xiàn)四方佛密教宇宙觀的金剛界五方佛——大日如來(lái)(摩訶毗盧遮那)與密教四方佛的組合,還可以看到在漢傳佛教影響下二者互相交融、轉(zhuǎn)變的軌跡。敦煌佛教一直以漢傳體系的佛教為主流,隨著唐密的興起,不少密教經(jīng)典將顯教的神祇及其功能移植到密教經(jīng)典中,開始吸收或利用顯教的圖像內(nèi)容和構(gòu)圖形式,說(shuō)明顯密結(jié)合,顯體密用是敦煌密教發(fā)展的主流,而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zhuǎn)變就是顯體密用的一個(gè)典型例證。
參考文獻(xiàn):
[1]松長(zhǎng)有慶.兩部マンダラの(曼陀羅)的系譜[C]//日本種智院大學(xué)密教學(xué)會(huì),編.世界佛學(xué)名著譯叢編委會(huì),譯.世界佛學(xué)名著譯叢75:西藏密教研究.臺(tái)北:華宇出版社,1988:186-187.
[2]佐和隆研.密教美術(shù)論:第1卷[M].東京:法藏館,2000:81-86.
[3]呂建福.中國(guó)密教史[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5:63.
[4]章巽.法顯傳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1-62,103.
[5]甘肅文物考古研所.河西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huì),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史系.須彌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7]松原三郎.中國(guó)佛教雕刻史論[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220.
[8]陳清香.神通寺四門塔探源[J].中華佛學(xué)學(xué)報(bào):第17期,2004:149-172.
[9]瑞方.陶齋藏石記:卷7[M].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1冊(cè).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13.
[10]大村西崖.中國(guó)美術(shù)史·雕塑篇[M].東京:國(guó)書刊行會(huì),1980:253.
[11]李崇峰.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C]//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73.
[12]閻文儒.中國(guó)石窟藝術(shù)總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83-84.
[13]劉慧達(dá).北魏石窟與禪[J].考古學(xué)報(bào),1978(3).
[14]賀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與禪觀[C]//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15]樊錦詩(shī),趙青蘭.吐蕃占領(lǐng)時(shí)期莫高窟的分期[C]//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16]賀世哲.莫高窟第192窟《發(fā)愿功德贊文》重錄及有關(guān)問(wèn)題[J].敦煌研究,1993(2).
[17]大正藏:第16冊(cè)[M].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404,423.
[18]大正藏:第15冊(cè)[M].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688.
[19]李淞.陜西古代佛教美術(shù)[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9-41.
[20]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guó)北朝卷[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132,166.
[21]大正藏:第9冊(cè)[M].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403-405.
[22]松原三郞.增訂中國(guó)佛教雕刻史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151-155.
[23]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M].臺(tái)北:覺風(fēng)佛教藝術(shù)文化基金會(huì),2000:112-126.
[24]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53-156,171-172.
[25]殷光明.敦煌華嚴(yán)法華經(jīng)變的配置與判教思想[C]//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壁畫藝術(shù)繼承與創(chuàng)新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26]大正藏:第18冊(cè)[M].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94.
[27]大正藏:第36冊(cè)[M].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698.
[28]殷光明.敦煌盧舍那法界圖像研究之一[J].敦煌研究,2001(4).
[29]劉永增.敦煌石窟藝術(shù)·莫高窟第158窟[J].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8.
[30]郭祐孟.敦煌吐蕃時(shí)期洞窟的圖像結(jié)構(gòu)——以莫高窟360和361窟為題[C]//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
[31]趙曉星.莫高窟第361窟待定名圖像之考證——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一[C]//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
[32]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M].香港:中國(guó)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134-173.
[33]田中公明.敦煌密教と美術(shù)[M].東京:法藏館,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