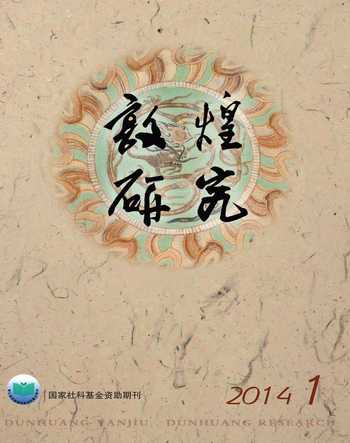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綴合與研究
陳麗萍
內容摘要:本文以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回顧了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其次將較早刊布的五件姓望譜按抄寫格式分為三類,指出其中S.5861兼具兩類抄寫格式的特征,并借助S.5861與其他各卷抄寫格式、物質形態與內容等方面的對比分析,確定了該卷與P.3191、BD10613、BD10076、S.9951、羽59R間存在著綴合關系,并再次將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按抄寫體系劃分為三類,確定了以S.5861為中心的綴合本定名應為《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而與綴合本相似的BD08679當是以此為底本的偽作,其定名應與《貞觀氏族志》無關。
關鍵詞:敦煌;姓望譜;格式;物質形態;綴合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1-0078-09
長期以來,學界周知的敦煌本天下姓望譜①(下行文多簡稱“姓望譜”)共有五件,即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1]、BD08679(北位79號)《唐貞觀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條舉氏族奏》[2]、P.319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3]、S.5861《姓氏書(?)》[4]與P.342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5]。其中,只有S.2052有原題,其他四件皆由后人擬定名。
隨著各國所藏敦煌文書的不斷整理,又有S.9951《姓氏書(?)》[6]、BD10076《姓望氏族譜》[7]、BD10613《郡望姓望》[8]與羽59R《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9]四件姓望譜陸續刊發,其中也只有羽59R有原題,其他三件皆由后人擬定名。
九件姓望譜中,有關前五件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②,后四件卻尚未引起學界全面關注。筆者從抄寫格式、內容銜接與物質形態等各方面入手,對九件姓望譜進行了綜合比對,發現以S.5861為中心,該卷與羽59R、P.3191、S.9951、BD10613、BD10076間存在著銜接或綴合關系(圖1),進而對敦煌本姓望譜的抄寫體系與定名等問題有了一點新思考,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大家。
探討文書間的內在聯系乃至綴合關系,書寫格式無疑是首要直觀的判斷標準,借助已有成果及筆者的分析,可先將前五件姓望譜按抄寫格式大致分為三類:
P.3421為一類。該卷首尾皆殘,存四郡的郡姓與姓源共20行,以郡→姓氏數→州→姓氏→姓源為序抄寫各姓望所出,因與其他四件的格式和內容都大不相同,該卷一般被當作姓源類譜牒文書單獨介紹研究,本文對該卷也不做過多探討。
BD08679為一類。該卷首殘尾全,存66郡的郡姓35行,以郡→姓氏數→州→姓氏為序(雙行)抄寫各姓望所出,再加署名高士廉的奏抄11行與悟真的題記2行(單行抄寫),共計48行。因高士廉和悟真的雙重知名度,使該卷一直備受學界關注,但關于其創作時期、真偽與定名等問題卻又一直存在爭議{1}。
S.2052、P.3191為一類。S.2052首尾俱全,由題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1行、序言3行和十道九十郡的郡姓共106行組成;P.3191首尾俱殘,存第五、六、七道十九郡的郡姓共22行。相較P.3191,S.2052內郡望數大增,與P.3191在道州次序的安排上也有所差異,但兩卷皆以十道為序,按道→州→郡→姓氏數→姓氏次序抄寫,內容也有大致相合處,說明它們是相近底本不同時期的抄本,唯S.2052時代更晚、內容有所增改而已{2}。
所余S.5861的書寫格式較為特殊。該卷由四塊殘片組成,按《英藏敦煌文獻》刊布的圖版,可依次標識為A、B、C、D片,分別殘存6、9、10、6行內容。王仲犖、唐耕耦(將B片標為(一)、能與該卷綴合的S.3191標為(二)、D片標為(三)、C片標為(四)、A片標為(五))、鄭炳林等皆認為B片是另件文書。因筆者求助劉波先生聯系IDP項目負責人能否將S.5861圖版提前在網站公布時,由劉波先生轉告,該卷因早年托裱在一張背襯上而無法拍攝背面,也就無法依據背面的內容再次確定它們之間的關聯。不過,B片的抄寫格式顯然與其他三片不同,部分內容在P.3191中能找到相同記載,而P.3191又能與D片綴合,故B片的歸屬有兩種可能:一是與其他三片為同卷抄寫的兩種姓望譜,屬同卷不同件;二是與其他三片不同卷,只因外形性質相似而被整理者誤歸為一卷。無論何種情況,B片與本文的討論確無關聯,故凡提到S.5861而不做說明時,皆特指A、C、D三片的組合,而據前賢的研究及殘片間的內在邏輯,應以D→C→A為序排列。其中D與C(1-8行)片按道→州→郡→姓氏數→姓氏為序抄寫了第六、七、八、九道十一郡的郡姓共14行,這與S.2052、P.3191的格式完全一致;C(9-10行)與A片所抄內容(李錦繡認為是敕旨)卻與BD08679奏抄極為近似,即S.5861兼具兩類書寫格式的特征,其歸屬一時很難確定。為方便下文對比敘述,先參照諸家錄文將BD08679奏抄內容過錄如下:
(前略)
36 以前太史因堯置九州,今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
37 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
38 后,明加禁約,前件郡姓出處,許其通婚媾。結
39 婚之始,非舊委怠,必須精加研究,知其囊譜相承
40 不虛,然可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雜
41 姓,非史籍所戴(載),雖預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
42 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
43 雖有譜,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祿大夫兼
44 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等奉
45 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別條舉,恐無所
46 憑,準令詳事訖,件錄如前。敕旨:“依奏。”
(后略)
也先將S.5861敕旨的相關內容引列如下:
(前略)
9 太史因堯置九州,今分■
10 ■ 月十日 ■
(以上C片)
1 定偶。其三百九十八姓,■
2 非史籍所載,或■ ■
3 戶,商價(賈)之類。上柱 ■ ■
4 甫等 奏,敕令■
5 各別為條舉,□■
6 聽 進。
(以上A片)
如此,要判斷S.5861的確切歸屬,還得進一步分析卷中蘊含的深層信息,而在此之前,筆者以為有兩點需要略作回顧,再就S.5861的歸屬及本文的主題進行探討。
首先,關于姓望譜的主要研究方法。姓望譜屬譜牒類作品,史籍中也多有相關記載或作品傳世,前賢因此多據兩《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廣韻》、《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辯證》、《通志·氏族略》等傳世史地或譜牒作品與之相較,逐一核實某一姓氏及所在州郡是否史籍有載,以及與史籍所載之別,由此判定寫卷的時期、性質、真偽等問題。進一步講,對爭議較多的BD08679是否與貞觀《氏族志》有關,前賢也多從相關史籍中尋找各種蛛絲馬跡支持各自論點。利用傳世史籍比對敦煌寫卷,固然是研究姓望譜的主要方法,但前賢的很多探討有時不免拘泥于此,過分強調了姓望譜與史籍間的對應點,并將一些對應關系任意引申所用,相應的解釋難免會流于牽強。
其次,關于姓望譜的定名依據。除了參考史籍中各類天下姓望譜的題名作為敦煌寫卷定名的依據外,S.2052是五件姓望譜中既有原題且首尾俱全者,也是其他寫卷定名和校錄的主要參考。實際上,雖然P.3421、P.3191、BD08679、S.5861等的部分定名確以該卷為準,但因BD08679與著名的貞觀《氏族志》有所牽連而成為另一個主導其他寫卷定名的因素,更因BD08679本身定名的不確定,也深刻影響并導致了其他寫卷定名的混亂,如原本出自一卷的S.5861、P.3191、S.9951、BD10076、BD10613等號卻各有定名(詳下),這也為初識敦煌本姓望譜的學者造成了不少困惑。
筆者以為,學界長期以來偏重將敦煌本姓望譜與傳世史籍的比對研究,相對忽視了寫卷間的一些共性或特征;也為貞觀《氏族志》的盛名所惑,將過多的關注集中在了BD08679號上并盡力將二者等同{1}。如果暫時拋開以上兩種傳統的影響,將無法歸屬的S.5861與其他寫卷的抄寫格式、內容、物質形態等聯系起來考慮,就會發現S.5861(綴合狀態)不僅可以解決其本身的歸屬問題,或許對解決諸如BD08679的真偽、缺名姓望譜的定名等爭論也有所啟發,或許能為姓望譜的研究多提供一種方法參考。
S.5861,首尾下部殘,高約15—16厘米,D、C、A片分別長約14.5、21.5、13厘米,依次抄寫第六至九道,即河南、淮南、江南、劍南道的郡姓所出及敕旨。因下部也有殘缺,該卷所存多止于州→郡→姓氏數部分,各片間也不能完全銜接;卷末敕旨若與BD08679號奏抄相較,也似未抄寫完整。總之,S.5861若為全卷,首尾與下部尚缺很多內容。
S.5861的定名主要有《天下姓望氏族譜》(仁井田陞)、《姓氏書》(王重民)、《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唐耕耦)等,《英藏敦煌文獻》編者為其擇名《姓氏書?》(似沿用王重民定名又不甚確定),此外,編者還提示該卷可參S.9951、P.3191{1}。
先說P.3191。該卷抄寫了第五至七道,即河北、河南、淮南道的郡姓所出,除第1、20—22行上部有所殘缺外,第2—19行的內容相對完整。P.3191定名主要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王重民)、《郡望姓望》(黃永武)、《殘姓氏書》(王仲犖)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者為其擇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池田溫最早提出可將該卷置于S.5861D前綴合,唐耕耦認同并作了示意圖;鄭炳林認為兩卷字體不一而分別校注;李錦繡認為該卷即使不是S.5861的一部分,也是同一書卷的不同抄本。
盡管抄寫格式相同,但P.3191與S.5861既無同一定名,能否綴合也有爭議,就是因為無法對比原卷(或彩色圖版)以及無法得知寫卷物質形態等客觀條件所限,前賢的相關判斷因此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干擾{2}。所幸以上限制已有所解除,我們也可借助新的信息重新判斷寫卷間的關聯。
據IDP網站上的物質形態描述,可知P.3191長、高分別為46.9、29厘米。盡管網站公布的彩色圖版(該卷似乎也被托裱在一張硬襯上)依然略有變形,一些字跡,如第3—5、7行的郡姓數、第6行“江南道”三字的墨跡已淡化不清,但從筆跡(具體如“弟”、“郡”等字在各卷內的字形)、州郡的間距、每郡“幾姓”的字號略小且墨跡較淡等方面比對,該卷與具有同樣書寫特征的S.5861確為同卷。正如唐耕耦所示,P.3191第20—22行正好能置于S.5861D第1—3行的下部,綴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為S.5861D):
海州東莞郡 〔四〕■ 盛 關 何 公孫
第七淮■ ■一郡
揚州廣陵郡囗〔姓〕 ■ 高 盛■
除了文字上的銜接,筆者將兩卷圖版的缺口按比例處理,完全綴合是無疑的。再關注綴合部分的高度,也依然保持在29厘米左右。這也提示S.5861原卷的高度、該卷與S.9951、BD10076、BD10613綴合后的高度以及羽59R的高度也皆應在29厘米左右。
再說S.9951。該卷首尾上部殘缺,僅存4行,因前人尚無錄文,先過錄如下:
(前缺)
1 ■ □ 鄔 戚
2 ■ 紀 甘 左 許
3 ■ ■ 黃 賴 豐
4 ■ 陶 翟 騫
(后殘)
該卷所存為姓氏部分,應為姓望譜的下部,最早關注該卷的榮新江將其定名為《唐天下姓望氏族譜》并有詳細描述:
首尾上均殘,存4行。第三行上部殘存“姓”字下半,所余4行字分記十二姓,對比位字79號,知分別為杭州二姓、潤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審其字體,當與S.5861+P.3191同卷,按順序,當是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一,91頁所錄(三)、(四)二片中間一殘片。
〔11×17厘米〕[10]
榮書的定名參照了S.2052,有關描述及復原位置也已相當準確,但仍有三點可略作補充:
第一,榮書提供該卷長11厘米、高17厘米,但IDP網站公布為長11.4、高17.2厘米。兩個測量間的誤差盡管很小,但后一尺寸似應更為精確。
第二,盡管榮書已有定名并指出其與S.5861為同卷,《英藏敦煌文獻》的編者或許為了保持兩件文書本為一卷及定名的一致性,仍將其定名為《姓氏書(?)》。
第三,榮書認可S.5861與P.3191的綴合關系(但應P.3191在前S.5861在后),接著指出該卷能置于S.5861(三)(D)、(四)(C)片間,并指出殘片的內容應為杭州二姓、潤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之姓氏部分。筆者進一步參照BD08679的相關內容,如杭州鹽官郡出三姓:“岑、鄔、戚”;潤州丹陽郡出四姓:“紀、甘、許、左”;括州松陽郡出四姓中有“黃、瀨、曲”;江州潯陽郡出二姓:“陶、翟”。再參照S.2052中第八江南道下也有相近內容,如:“杭州鹽官郡出五姓”,其中有“戚”姓;“潤州丹陽郡出八姓”,其中有“甘、紀、左”姓;“處州松陽郡出五姓”,其中有“賴”姓;“江州潯陽郡出六姓”,其中有“陶、翟、騫”姓。綜上可知,S.9951本應屬第八江南道中的內容,具體所抄為杭州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括州松陽郡三姓、江州潯陽郡三姓的姓氏部分,若補足原卷或當為:
1 〔杭州 鹽官郡 三姓〕 ■ 鄔 戚
2 〔潤州 丹陽郡 四姓〕 紀 甘 左 許
3 〔括州 松陽郡 三〕 ■ 黃
賴 豐
4 〔江州 潯陽郡 三姓〕 陶 翟 騫
不過,S.5861D最后一行為“湖州二郡 長城郡”,若將S.9951直接置于其后,再參考BD08679,其首部至少還應有“(湖州)吳興郡”的內容才能實現與D片的完全綴合;其尾部卻可與C片的部分直接綴合(S.9951第4行之“陶”字與S.5861C第1行之“能”字部分可完全拼合),即S.9951與S.5861D間仍略有缺失。
筆者注意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書中的BD10076與BD10613兩塊殘片與S.5861等應有關聯。
BD10076(L0205)號,首尾下部殘,存3行,長6.3厘米,高14.4厘米,編者判定為9—10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定名《姓望氏族譜》。BD10613(L0742),首尾下部殘,存3行,長5.9厘米,高13.2厘米,編者判定為7—8世紀寫本,定名《姓望郡望》,還提示該卷與P.3191、S.5861為同一文獻。筆者也先將兩件文書分別過錄如下:
BD10076號:
(前缺)
1 錢唐郡 三姓 ■
2 鹽官郡 三姓 ■
3 丹陽郡 四姓 ■
(后殘)
BD10613號:
(前缺)
1 ■ ■ ■ ■
2 蘇州 吳郡 四■ ■
3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后殘)
編者雖注意到了兩塊殘片與其他姓望譜間的關聯,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于是出現了兩種定名和判定了兩個抄寫時期,這有些令人不解。當然,相較而言,有關BD10613的判斷描述更接近其本來面目。
這兩塊殘片與S.9951不同,殘存了錢唐郡、鹽官郡、丹陽郡(BD10076);囗興郡、蘇州吳郡、杭州余杭郡(BD10613號)的州郡名與姓氏數,應為某姓望譜的上部。參考BD08679中有:湖州“長城郡一姓”、“吳興郡七姓”,蘇州“吳郡四姓”,杭州“余杭郡三姓”、“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再參考S.2052,其第八江南道下有:“湖州吳興郡”,“蘇州吳郡”,“杭州余杭郡”、“杭州錢唐郡”、“杭州鹽官郡”,“潤州丹陽郡”。那么,由“杭州三郡”分別為“余杭、錢唐、鹽官”郡,首先能確定兩塊殘片間存在綴合關系,且應是BD10613在前BD10076在后。
上文所示,如S.9951與S.5861D要完全綴合,至少尚缺“(湖州)吳興郡”之內容;S.9951上部缺失,第1、2行分別缺少“杭州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的州、郡與郡姓數等內容,而BD10076第2、3行的“鹽官郡 三姓”、“丹陽郡 四姓”正好能與之銜接。如此,BD10613與BD10076成為置于S.5861D尾部與S.9951上部完全銜接的兩塊關鍵殘片,各卷綴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為S.9951):
(前略)
湖州二郡 長城郡 ■
(以上S.5861D)
〔吳〕■ ■ ■
蘇州 吳郡 四■ ■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以上BD10613)
錢唐郡 三姓 ■
鹽官郡 三姓 ■ 鄔 戚
〔潤州〕 丹陽郡 四姓 紀 甘 左 許
〔括州 松陽郡 三〕■ 黃 賴 豐
〔江州 潯陽郡 三姓〕 陶 翟 騫
(以上BD10076+S.9951)
洪州 豫章郡 五姓 能(熊) ■
(以上S.5861C,后略)
在梳理已知敦煌本姓望譜的學術史之余,筆者利用比對抄寫格式、內容與參照物質形態等方法,認可和進一步確定了P.3191與S.5861間的綴合關系,還由此確定了其他三件姓望譜殘片間的綴合,即以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
S.9951+S.5861C?+S.5861A?為序綴合后(對比BD08679號奏抄內容與S.5861殘存敕旨內容,以及S.5861原卷29厘米高度內所能容納字數的上限,其C、A兩片間應還有部分缺失,暫以“?”示待定),文本較前賢的研究已有所推進,但有一個關鍵問題仍尚待解決:S.5861的抄寫格式和內容與S.2052及BD08679皆有交叉,但其所屬與定名究竟為何,從目前完成的綴合中仍無法確定。最后,唯期望第九件姓望譜即羽59R號能為解決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羽59號,長4.2厘米,高28.9厘米,正背面皆有文字。羽59R號存2行,錄文如下:
1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 □
2大唐天寶八載正月十日京(晉){1}國公隴西郡臣李林甫
羽59V號存1行(其前端還粘貼一塊僅存1行半的碎片,為某書信殘句,與本文無關而不予關注),錄文如下:
天下五姓族譜望(望譜)一卷
羽59為李盛鐸舊藏之一,王重民編為散0248,并轉抄底本目錄中(對該卷正面即59R)的定名并描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李林甫撰 止有書名而書佚)”[11];《敦煌秘笈》的編者卻將其改名為《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或許為了強調寫卷作者是著名人物)。筆者以為,遵循敦煌寫本定名時有原題者一般照錄的原則,羽59R應還原本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此外,這2行文字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問題:
李林甫是否撰寫過“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其題名是否如該卷首題,成書時間是否與該卷所載一致,是否有傳世本以及該卷是否與其他敦煌本姓望譜有關?
史籍中確有李林甫撰寫姓望譜的記載,這在仁井田陞、姜伯勤、李錦繡的論述中早已關注并注明了三個主要出處,筆者也轉引相關內容如下:
《新唐書》卷58《藝文志二》:
唐新定諸家譜錄一卷李林甫等。[12]
《直齋書錄解題》卷8《譜牒類》“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條注:
唐李林甫等天寶八載所纂,并附五音于后。[13]
《玉海》卷50《藝文·譜牒》“唐新定諸家譜錄”條:
《書目》:天下郡望姓氏族譜一卷,李林甫等撰。記郡望出處,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寶中頒下,非譜裔相承者,不許昏姻。[14]
綜上記載,有幾點可以明確:
第一,李林甫確曾撰寫過姓望譜一卷,但署名中皆隨“等”字,說明這是一部集體作品,李林甫是領銜者而已,這就如同高士廉領銜《氏族志》一樣,據《唐會要》卷36《氏族》所載,參修者還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15],但習慣上也以受命兼主修者高士廉為《氏族志》的作者。因此,羽59R號中的李林甫單署名與史籍所載不算沖突。
第二,李林甫所撰姓望譜的具體題名,各家所載皆不同,分別為“唐新定諸家譜錄”、“天下郡望氏族譜”、“天下郡望姓氏族譜”,究竟孰是原題名,或許已無法核實了,不過這或許與各類姓望譜多有別稱的現象有關。如高士廉等奉修氏族志事見載于多處,唯所成書名不確,有《氏族志》、《貞觀氏族志》、《大唐氏族志》{2}等名;還如李義府等所撰天下姓望譜,也有《姓氏錄》、《姓氏譜》、《姓錄》{3}等名。尤其高士廉作品因成書于貞觀年間,故以《貞觀氏族志》之別名流傳最廣,至于其本名與其他別名,世人反而知之甚少。那么,羽59R號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與史籍所載各題名不完全統一,似也在情理之中,且李林甫原作已無法得見,本文只能暫定以羽59R號的題名為該作品的題名。
第三,李林甫所撰姓望譜的頒行時間,《新唐書》闕載,《直齋書錄解題》記為天寶八載,《玉海》記為天寶中,而羽59R號確載為“天寶八載正月十日”,提供了這部作品頒行的具體時間,可補史籍所闕。
第四,李林甫所撰姓望譜已佚,故后世學者僅在譜牒著述目錄中提及,這或許也能作為解釋第二個問題的旁證,因原書已佚且譜牒類作品皆多有別稱等因素影響,故至后人轉抄及南宋時人記載這部作品時,其題名也變得難以統一,唯能確定李林甫修撰過此書而已。
在確定了李林甫等所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確于天寶八載正月十日頒行后,再結合以上所舉姓望譜殘片的物質形態與史籍所載,羽59R號與其他敦煌本姓望譜間的關聯也就顯而易見了:
首先,本文提出判定各寫卷間的關聯,除了關注抄寫格式外,還應關注內容和物質形態等因素。就物質形態而言,已知P.3191原卷與S.5861等綴合高度皆大致為29厘米左右,而羽59R的高度為28.9厘米,二者之間的差距可謂微乎其微,這是說明它們本為一卷的一個基本前提。
其次,結合羽59R、S.5861與史籍的雙重比對,它們之間重合的字眼如“天寶八載”、“月十日”、“李林甫”、“三百九十八姓”、“甫 等”(尤其羽59R號中之“甫”字,與S.5861A中之“甫”字,除了字形相像,皆少了“一”,顯然出自一人之手),皆說明羽59R、S.5861等寫本就是李林甫等所撰、頒行于天寶八載正月十日的《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抄本:羽59R號為開頭部分,保存了題名、作者和頒行時間,其后缺失第一至四及第五道的部分郡姓內容;P.3191為中間部分,所存第五至六道的部分郡姓內容;S.5861、BD10613、BD10076與S.9951等號為后段部分,保存了第六至九道的部分郡姓內容和敕旨。羽59R號與上綴合本當屬同卷,S.5861等號的定名問題也因此迎刃而解了,也可確定綴合本和時代更晚的S.2052當屬同類姓望譜。
S.5861的定名與歸屬問題雖得以解決,但關于S.5861敕旨與BD08679奏抄的相似問題仍需贅述幾句。
如上所引,牟潤孫等先生已判定BD08679是有意“攀附”于貞觀《氏族志》的偽作,李錦繡進一步確定BD08679是以S.5861為底本的偽作,筆者也贊同李先生的判斷并有幾點小發現:第一,作偽者略去十道次序,僅以各州郡為序抄寫,還有意調換打亂各州郡間的原屬位置,如在“徐州沛郡”和“徐州蘭陵郡”中間隔了“沂州瑯琊郡”,在“湖州長城郡”和“湖州吳興郡”中間隔了“越州會稽郡”、“蘇州吳郡”等,以顯該卷與底本的不同;第二,作偽者不僅篡改了姓望譜頒行的時間和作者,甚至將原敕旨的內容也有所擴充改動,以顯官方刊定本的權威。但作偽者忽視或并不清楚《氏族志》成書于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入譜二百九十三姓的基本前提{1},不僅照抄了底本上的三百九十八姓,還將成書時間提前為“貞觀八年五月十日”,甚至犯了五月“十日”當為“庚辰”而非“壬辰”{2}的錯誤。如此,雖有底本原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在先,但作偽者是否沿用確難以肯定,筆者猜測BD08679號還是很可能仍被作偽者冠以貞觀《氏族志》或其他相關別名,而我們若要為該卷再擬定名,或許凡貞觀《氏族志》無關者皆可,如上注文所舉各種其他定名似皆能適用。
當然,作為確定綴合本定名、時代和性質的羽59,其中也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抄寫者的字跡雖相對工整,但從其將李林甫之爵“晉國公”誤作“京國公”,再結合先賢對綴合本中各種錯漏的校錄,可知抄寫者的水平并不高,可能只是粗通文墨的書手。
第二,該卷背面即羽59V還有“天下五姓族望譜一卷”之題名,因目前皆無P.3191等背面的信息,一時無法判斷這是雜寫還是別件姓望譜的題名。山東、關中、江南、代北等地區皆有世胄大姓,其中“崔盧李鄭王”為山東大姓,時人推為諸姓之首,亦簡稱“五姓”[15]773。唐中書令薛元超,本出身關中大姓,又為太宗侄女婿,卻有“不得娶五姓女”之恨[16],由此可知“五姓”在唐人心中的分量。如羽59V中的這行字確為別件姓望譜題名,就說明當時有專為山東五姓所作之姓望譜,為專載或推崇“五姓”郡望的一類作品。
第三,羽59R中(原卷開頭)李林甫的結銜為“晉國公隴西郡臣”,但S.5861A中(原卷末尾)又有“上柱國……甫等”字眼。據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上呈《唐六典》時的結銜為“集賢殿學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臣李林甫”[17],其中確有“上柱國”,那么羽59R與S.5861A中的李林甫官職結銜為何不符,筆者暫時也找不到答案或依據。
第四,據上引史料,李林甫所撰姓望譜題名中有兩處出現了“郡望”,而羽59R則為“郡姓”氏族譜。盡管本文已注意到歷史上知名的姓望譜多有別名,但同一作品名在史料與出土文書間存在著“郡望”與“郡姓”之別,這究竟是傳抄中無意識的筆誤,還是抄寫者的有意改動,由此反映了從“郡望”轉向“姓望”的時人觀念,這點也頗令人思量。因為這種觀念的變化,在其他敦煌姓望譜中確已有體現,如時代晚于綴合本的S.2052,該卷題名不僅已變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連序文都以“夫人身立世,姓望為先”起首,顯然“姓望”已完全代替了“郡望”。
本文對現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在先賢已經判定P.3191、S.5861、S.9951間存在綴合關系的基礎上,將BD10613、BD10076與羽59R加入其中,形成羽59R+……+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S.9951+
S.5861C?+S.5861A?的綴合本,也由此以抄寫格式為標準,將九件姓望譜區分為三個體系:P.3421為一類;BD08679為一類;綴合本與S.2052為一類。其中以S.5861為中心的綴合本是李林甫等撰、天寶八載正月十日頒行《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民間抄本,BD08679是以此為底本的偽作,而S.2052很可能是以此為底本的、時代更晚的擴充本。盡管綴合本依然殘損甚多,但其題名、作者和時間的明確性,使其成為敦煌本姓望譜中的一個重要坐標,尤其對BD08679的定名、性質等問題的解決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3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10-212.
[2]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03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385-388,44.
[3]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2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1.
[4]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9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181.
[5]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4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5.
[6]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95.
[7]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07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113、30.
[8]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08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55、17.
[9]吉川忠夫.敦煌秘籍影片冊一[M].大阪:杏雨書屋,2009:374-378.
[10]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891—13624)[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145.
[11]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318.
[1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3:1500.
[1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29.
[14]王應麟.玉海[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953.
[15]王溥.唐會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74.
[16]劉餗.隋唐嘉話[M].北京:中華書局,1997:28.
[17]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