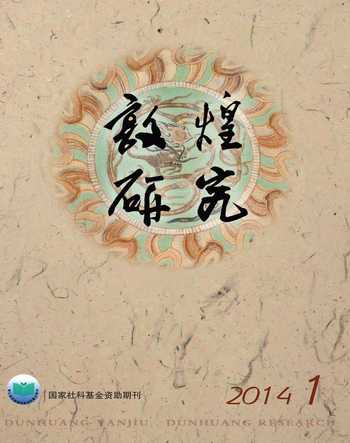燉煌的詞源再探討
譚世寶
內容摘要:有關燉(焞、敦)煌的詞源問題,是伴隨著敦煌學產生而一直吸引眾多中外學者關注研究的跨世紀難題,迄今已經成為聚訟不決的百年歷史懸案。有關燉煌等地名的族源及意義成為難以理解的歷史問題,乃因時過境遷,使得原來完整的漢朝歷史檔案資料在兩千多年來不斷遞減的過程中變成碎片流傳于今世,而導致當代片面的歷史研究者的困惑不斷增加。特別是由于有關問題實際是由原來對中國歷史文化及《史記》、《漢書》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理解的現代歐洲漢學家提出的偽問題,然后由他們及同樣一知半解的日本漢學家對偽問題作出的種種錯答案,形成了先入為主的一些誤論的影響,而導致了所謂燉煌為胡語的音譯詞之說在中國普遍流行,弄清這個百年懸案,必須源流都要厘清,既要把百多年來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史基本研究清楚,同時還要把《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的源流弄清楚。本文通過對有關傳世文獻源流的分析研究,再一次強調“燉煌”為漢語非胡語音譯。
關鍵詞:月氏;匈奴語;土著居民;名從主人
中圖分類號:K92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1-0121-10
有關燉(焞、敦)煌的詞源問題,是伴隨著敦煌學產生而一直吸引眾多中外學者關注研究的跨世紀難題,迄今已經成為聚訟不決的百年歷史懸案。在此再作一些新探討,就教于方家。拙文所論難免涉及一些前輩及時賢乃至新晉博士之論,均力求作出客觀的評論,唯愿能獲得同仁理解,以促進對有關問題的研討深入展開,盡快了結這個懸案。
一 以往的研究略述
筆者在二十年前發表的《燉(焞、敦)煌考釋 》一文①,首先在其中的《燉煌、焞煌與敦煌的正俗源流質疑》至《“燉煌”與“敦煌”之正俗辨》等四節文章中,針對以往流行以敦為正字,燉為俗字之說,較為全面系統地收集了歷代各種文獻數據的有關記載和解釋,從字的形音義的綜合研究分析來證明燉(焞、敦)煌的各種寫法中,應以“燉”為正體字,“焞”為其異體字,“敦” 為其俗體字②。其次,在第五節《燉煌之本義及族源》中,對前輩學者德國的李希吐芬與日本的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法國的伯希和以及中國的岑仲勉、馮承鈞等人之說,還有當時所見時賢齊陳駿、劉光華、王宗維、施萍亭等人的各種說法提出商榷、著重否定了所謂燉煌為胡語音譯之各說,力證被上述大多數中外學者所否定的東漢應劭“燉,大也;煌,盛也”的解釋,其實是現存漢朝人最早也是唯一的“燉煌”正確釋義,以后歷代之史地及文字書籍多沿用此說。及至近現代學者,因不明“燉”與“敦”的正俗關系,又以應劭的解釋不合燉煌當年實際既不大又不盛的規模,而又無法找到燉煌有其他含義,遂紛紛提出燉煌為胡語音譯說。至于是何種胡語,則眾說紛紜。其義是什么,就更無人能道。由此進一步證明“燉煌”完全是按照其漢文的兩個字的本義組合而成的專有名詞,絕非胡語音譯。
如上所述,拙文發表于1993年的《文史》,而且后來又被收入了陳國燦、陸慶夫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歷史卷(2),其應為有關研究者看到是理所當然的。加上在本世紀初,筆者在接受上海李偉國先生組織的“名家與名編”的對話中又進一步指出:
……“燉(敦)煌”在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已經是中國的一個軍事屯田地區名……可見其出處年代早于前述任何一個胡語詞,故充其量只能說那些胡語是燉煌的譯音,而不能反過來說燉煌是它們的譯音。伯希和修正胡語譯音說而提出的土名說,也是主觀的臆測。
應劭的解釋既合乎中國乃至國際通行的傳統命名原則,又合情理和實際。理由如下:
1. 因為孔子提倡“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見《春秋谷梁傳》桓二年)。尊孔崇儒的漢武帝是不會違背這個原則的……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屬和意義皆不知的“一種土名”的譯音作為一個新開疆而設立的重要的軍事行政地區的名稱……
2. 雖然漢朝人在新開的政區地名上普遍實行了名從主人的原則,但是個別的小地名或山水等自然地理名稱也有沿用異族舊名的譯音……相反,漢代的文獻從來沒有說燉煌是來自胡語,已經可以反證其為純粹的漢語地名。
3. ……燉煌之取義大盛,并非實指其時郡治之城市規模的大盛,而是用以象征漢朝的文明道德猶如日月之光輝一樣大盛。故其首字應以從火的燉或焞為正,無火字旁的敦為俗寫假借……故劉光華等對燉煌的大盛之質疑,也是不能成立的誤解。[1]
可見拙見具有不容忽視的一定影響。但是,迄今不少有關論著在研究史的論述或介紹似乎都無視其存在,只是重復筆者提出過商榷的一些陳言舊論。例如,從1997年李正宇的《敦煌歷史地理導論》[2],到2002年劉進寶的《敦煌學通論》都是如此[3]。影響所及,迄今仍然有同類問題存在。2010年郝春文的《敦煌學概論》雖然已經有比前兩本書較為進步之點,但同時又有守舊之處[4]。這反映了當代燉煌學的某些專題研究中,一直存在對研究史的總結記述不夠客觀全面的缺陷,從而造成一些獨到之新見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故此筆者拙見所收之功效,就只是鮮有人再以否定應劭的解釋作為胡語說立論的基點了。因此在下文的工作,就是繼續質疑與否定胡語說的其余兩點主據。
二 “燉(焞、敦)煌”為胡語說之理據再商榷
目前主張胡語說之主據如下:其一,是“燉煌”一詞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張騫自西域歸來后給漢武帝的報告;其二,是常與“燉煌”連稱的“祁連”就是匈奴語的音譯[4]。由于此說濫觴于劉光華,故就以劉光華之論為主,其他學者之論為副,再加探討商榷。
1. 張騫有關月氏的報告涉及的“敦煌”年代與族源等問題
劉光華認為:“據《史記》、《漢書》的記載,‘敦煌一名在漢武帝于河西設置郡縣以前很早就出現了。”其所引述有關月氏與“敦煌”的四條資料如下: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史記·大宛列傳》)
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漢書·張騫傳》)
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 (《漢書·西域傳》)
接著,他就下結論說:“這四條資料都和張騫有直接關系……因為它反映的事實發生在戰國末至秦漢之際。這說明在漢朝建置敦煌縣、敦煌郡以前,就已經有了‘敦煌一名。”[5]如此把“敦煌”一名的出現推定“在戰國末至秦漢之際”,是相當主觀片面的。因為即使是張騫的報告原話,距離“戰國末至秦漢之際”也有很多年,更何況《史記》、《漢書》原稿出于司馬遷、班固,其所記并非張騫原話實錄,而且還有后來傳抄、加工、刻印者再添加之手筆,他們都有可能用后出之郡縣地名,插入其所間接轉述之前人報告。故此,不可以根據這“四條資料”就判定在張騫報告之時或以前就已經有“敦煌”一名。例如,《史記·大宛列傳》有關于元朔六年(前123)至元狩二年(前121)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的結果說:“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6]《漢書·張騫傳》所載基本相同{1}。但是,“金城郡”乃“昭帝始元六年(前81)置。”{2}故不能認為在公元前121年或之前已經有“金城”了。正如《資治通鑒》胡注稱此為“史追書也”[7]。且據當今專家考證,司馬遷編寫《史記》在公元前91年就基本完成了,并且是在“大概過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 {3}。由此可見,有關“金城”的“追書”乃其死后他人所作。據此還可推斷,現存《史記》有關張騫所述西域諸國之事,不可都信為太史公親筆實錄。再看《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漢擊匈奴之結果如下:
……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6]
上文沒有提及“金城”,原因就是金城郡之設立是在司馬遷死后。值得注意的是,史、漢兩書的匈奴傳在元封六年(前105)的記載之下才提及“單于益西北,左方兵值云中,右方兵(案:《漢書》無“兵”字)值酒泉、燉煌郡(案:《漢書》“燉煌郡”作“敦煌”)。”{4}由此可見,史、漢兩書的匈奴傳所載燉煌的地名與年代較《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漢書·西域傳》等為準確。但是,《史記·大宛列傳》又于李廣利伐大宛之后記載:“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這固然如劉光華指出:“此乃李廣利伐大宛后的天漢二、三年間事……證明天漢二、三年間敦煌尚未設郡。”[5]12對此有必要補充說明:這條資料至少還可以證明天漢二、三年間(前99、前98) 燉煌已經設縣,因而可以作為重要的地理坐標之地名加載于軍事行政的官僚組織系統的名稱中。因此,《史記》此條的“燉煌郡”雖然也可能是后人之“追書”,但是更可能是后人傳寫誤加了“郡” 字。筆者認為,刪除了這誤加的“郡” 字,則此“燉(敦)煌”就是指酒泉郡屬下的“燉(敦)煌縣”之簡稱,這樣就不會與前述天漢二、三年間“敦煌置酒泉都尉”的記載抵牾。所以,筆者認為前引《史記》匈奴傳所載之文應該刪“郡”字及頓號為“右方兵值酒泉燉煌”,《漢書》標點本之文也應刪頓號為“右方值酒泉敦煌”[8]。表明“燉煌”并非與酒泉平列的郡名,而是酒泉郡下的“燉煌”縣。而李正宇曾據“東漢史學家李斐說:屯田犯人暴利長元鼎四年秋在渥洼水捉住‘天馬,并說暴利長當時‘屯田敦煌界。元鼎六年才建立敦煌郡,那么元鼎四年的‘敦煌界只能是指敦煌縣界,表明渥洼水屬敦煌縣地。”[2]36而其最近的論文則改為:“《漢書·武帝紀》……注引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筆者案:此指敦煌縣界)……”[9]這雖然較前書嚴謹,但是其引《漢書》之唐顏師古注文而不引較早的《史記·樂書》的南朝宋裴骃《集解》,則是因為誤信《漢書·武帝紀》本文將“秋,馬生渥洼水中”之事列入元鼎四年。而本人二十年前之文已經據《漢書·禮樂志》及《史記·樂書》的南朝宋裴骃《集解》的記載,將此事考定在元狩三年(前120)[10]。這里再補充說明,《資治通鑒》將此事記入元狩三年,胡注也將李斐所述暴利長捕捉天馬的故事注于其下[7]636。故可以肯定在元狩三年(前120)或其之前,已經有燉煌縣了。而李正宇之所以誤信《漢書·武帝紀》有關此事之紀年,乃在于其在1990年之文已經對有關資料做了錯誤的取舍。認為元狩三年時“漢朝初有酒泉,駐軍設政尚不能遽達酒泉以西千里之遙的渥洼水附近……看來,元狩三年之說當屬誤記”[11]。其實,如前所引《史記·大宛列傳》已經明確記載元狩一至二年(前122—前121)“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域〕數萬人,至祁連山……而金城、西河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須知,這里提到的“鹽澤”就是當今的羅布泊(lob Nur、Lopp或Lop Nur)[12,13]。因此,其時有隨軍西征之罪人留駐燉煌是完全必要而可行的。雖然,“金城”為后人“追書”,但是其地在當時與“西河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的情況,應是由于有人留駐燉煌一帶已設的邊鎮據點作了原始的觀察記錄,曾被寫進《史記》原稿,后來之傳抄者才有可能在舊稿的基礎上“追書”一些新名。值得注意的是,《資治通鑒》在元狩三年記載武帝為慶賀獲得渥洼水天馬與司馬相如等文臣作歌配樂,即受到汲黯之直諫反對而“默然不悅”。而汲黯于次年就被免官。故獲馬作歌之事肯定不在元鼎四年而應在元狩三年。李正宇由于據不同的記載做了錯誤的選擇和誤解,就把敦煌縣的設置年代推后至接近元鼎四年(前113)了。
其實,據前述筆者考訂,《史記·匈奴列傳》在元封六年(前105)的記載下提及“右方兵值酒泉燉煌”,《資治通鑒》也將此條記入本年[7]697。這就可以確定起碼其時已經有酒泉郡屬下的燉煌縣了。
因此,確定酒泉郡開設的年代,有助于確定其下的燉煌縣開設年代上限。李正宇又據《漢書·武帝紀》的記載,認為酒泉郡建于元狩二年冬[2]36,93,即公元前121年末至前120年初。而吳礽驤、余堯1982年之文則認為“酒泉郡應建于元鼎六年(前111)”[14]。雖然,最近賈文麗取用了2001年王宗維之說,主張“酒泉郡設于元封四年(前107)”,而其所引用《史記》、《漢書》之文多錯亂誤解[13]51,故難以取用。綜合比較《史記》、《漢書》及《資治通鑒》的不同記載,以及當今學者的各種看法,筆者認為李正宇提出的元狩二年冬之說較為可信,可以據此推定其時已經有隸屬酒泉郡的燉煌縣。
現在再看前述《史記·大宛列傳》等有關月氏與“敦煌”的四條資料,就清楚其為司馬遷等人以“追書”之法將燉煌之名插入對張騫報告的轉述中。同類之例除了前文提及有關金城的“追書”之外,還有《史記·大宛列傳》開頭轉述匈奴降者所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之事,并無提及月氏之居處。至后文轉述張騫有關匈奴與月氏等國的報告時,提及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之后,才加插倒敘補述“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而《漢書·張騫傳》則在轉述元狩四年(前119)之后,“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但是,《漢書》這段文字所據《史記·大宛列傳》并沒有提及“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其原文說:“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由此可見,《漢書》有關文字乃隨意增改《史記》的文字,不足為據。至于《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本居敦煌、祁連間”,“烏孫國……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8],這兩條資料有矛盾異詞,其實也是將《史記·大宛列傳》的有關文字增改而成。而且,《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載:“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而同書下文的《烏孫國》則載:“后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可見,《漢書》有關記載多加入后出的異聞,不足為據。而《史記·匈奴列傳》所載冒頓單于于漢文帝四年(前177)“遺漢書”已經提及其派右賢王“西求月氏擊之……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又文帝于六年(前175)的回信亦對此事加以確認[6]。而《漢書·匈奴傳》所載冒頓單于的“遺漢書”與《史記》基本相同,但是卻將漢文帝回信有關確認匈奴夷滅月氏的內容刪略了[8]。由此可見《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較為原始準確,而《漢書》的兩條記載都對《史記》的記載做了增刪篡改,不足為據。近年已經有學者戴春陽指出這兩條記載“得不到相關史料的支持和印證,同時與新疆地區及原蘇聯中亞地區考古發掘及研究所證實的烏孫活動的時限、區域不符,因而有理由認為班固上述記載是錯誤的”[15]。所以值得研究分析的,就只剩下《史記·大宛列傳》倒敘記述的“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這一條。而此傳既有前文所揭露的“追書”金城之例,故這一條的“敦煌”也可能是后人“追書”的結果。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前人完全信用四條資料,以此作為燉煌來源于所謂“土著居民”的胡語說之主證,是不能成立的。
2. “燉煌”與“祁連”連稱不足為胡語說之據
如前所述,劉光華較早以“敦煌”與“祁連”連稱作胡語說的第二主據。后來諸家之說,與其根據大同,而結論大異[3]。因此,必須再作商榷。現引其有關論證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四條資料中的三條都將敦煌與“祁連”連用。祁連就是祁連山,顏師古《漢書》注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這說明唐人認為“祁連”為少數民族語,并非漢語命名……它和“祁連”一樣,應是當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漢音寫名。[5]
這顯然是對顏師古之注過度的解讀。而且,劉先生最后還確定“原來烏孫是敦煌地區的主人”。但是,又說“烏孫是敦煌地區的土著居民,還是由他地遷去的客民,由于古文獻資料缺乏,無法肯定回答”[5]8-9。如此片面而自相矛盾之論,有必要重新探討。
首先,僅據顏注“匈奴呼天為祁連”這一點,既不能證“祁連”為匈奴語,更難證其為“少數民族語”,乃至希臘或東伊朗等異國之語。據《史記·匈奴列傳》開頭所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因而夏商周秦以來就有華夏漢族與匈奴等北方各少數族裔混居和對立交往的情況,故有關官名及物名等名詞在兩族或多族之間互相借來借去的情況甚多。但是,因為匈奴等少數族裔是沒有本族文字的游牧民族或土著民族,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都比漢族低很多,故其語言中的漢語借詞顯然遠多于漢語中的匈奴語或其他少數族裔語的借詞。例如,《史記》下文載漢初時期的匈奴國官制情況為“其世傳國官號”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8]顯而易見,這些王侯將尉等名稱多數是匈奴譯取自漢語,而漢人再雜用意譯與音譯的方法將其回譯為漢文。故筆者認為,“天”與“祁連”就是一個漢語名詞的變音被匈奴借用之后又回寫為漢文的典型之例。這是因為漢字的單音節詞自上古就有緩讀而變成帶有反切性的雙音節詞的情況。正如顧炎武指出:“……又遲則一字而為二字:茨為蒺藜,椎為終葵,是也。”“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鄭樵謂慢聲為二,急聲為一。慢聲為者焉,急聲為旃;慢聲為者與,急聲為諸……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詩》:‘墻有茨。《傳》:‘蒺藜也。 蒺藜正切茨字……《禮記·檀弓》:‘銘,明旌也。 明旌正切銘字。《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為終葵。 終葵正切椎字。《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謂之筆。 不律正切筆字。”[16]其例之多,不勝枚舉。而“天”古時又音“乾”,且乾與天又有同義之點。例如,《易經》的《說卦傳》第十章說:“乾,天也。”{1}因此,《史記》“身毒國”的《集解》引“徐廣曰:‘身,或作乾。”《索隱》:“身音乾……”[6]顏師古注《漢書·西域傳上·無雷國》的“捐毒”說:“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雖然王先謙的補注認為“捐毒即身毒、天篤”之說誤{2}。但是,從古音來看,應該認同捐毒與身毒、天篤只是“語有輕重”的細微差別。因此,“天竺”又作“乾竺”{3}。而“祁連”正是“乾”的正切音。故此可以斷定“祁連”為古時“天”及其又音“乾”的某種方言的緩讀在匈奴等族的借用再回流給漢人通語的寫音。而匈奴語的“天”字的另一漢人回譯寫音詞為“撐犁”(譚案:《史記·匈奴列傳》的《索隱》作“■黎”),實際就是“祁連”的同源詞之異譯,只是越往后之人就越不知其源最早為漢語的“天”。即使是博學的岑仲勉,也只證明“祁連”與“撐犁”或“■黎”及后世突厥語的“騰格里(t?覿ngri)”的源流關系:“大約漢人初譯其全名曰‘天祁連山(今《史記》作祁連天山,乃其誤倒)后知其義訓天,又將天字截去,相沿省稱為祁連山……故天祁連山之讀法為t?覿n—grin。撐犁之讀法為t?覿ng—ri。不過讀法緩急略殊,祁連與撐犁實語原同一。”[12]525-526筆者認為,此說甚有理據,然尚有未達一間之憾。有關詞的先后實在先有“祁連(grin)”,后有“祁連天山”,最后才有“撐犁”或“■黎”及后世突厥語的“騰格里(t?覿ngri)”。
以上的判定,是因為《史記·匈奴列傳》本文不載“撐犁”或“■黎”此號,是今本《漢書·匈奴傳上》的本文率先將匈奴語的“天子”稱號寫音為“撐犁孤涂單于”,并指出“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涂;‘單于者,廣大貌也。”{4}這表明“撐犁孤涂單于”的稱號是在司馬遷之后至班固之前才為匈奴譯取自漢語。眾所周知,將自然界的“天”宗教政治道德倫理化為神圣的“天”,且因此而用同一個具有“天人合一”的象形和取義的“天”字來表示,這在商代的甲骨文字已經有確證。而以“天子”作為世上最高的宗教政治道德倫理化身的王者之尊稱,可以說是華夏族的祖先創立而歷經商周秦漢承傳確立的獨特語言文字概念。匈奴原有的低級游牧文化,并沒有產生出“天人合一”的“天”及“天子”的概念,其借用自然意義的“天”字的音譯是較早進入匈奴的語言,故首先有匈奴語回譯的祁連(天)山。至文帝時匈奴才開始學用神化的“天”,故在致文帝的兩封信中先后自稱為“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大匈奴單于”,可見其時尚未采用“天子”之稱,但是它們已很接近“天子”了。匈奴是在司馬遷之后譯入“天子”之稱,其方法是將以往漢語“天”的匈奴語音譯,與其本民族的“子”字結合為一個匈奴語的新詞。而這個新詞中神化的“天”就是后來被《漢書》用漢字音譯的“撐犁”或“■黎”。故也可推斷“祁連”的辭源應非匈奴語或其他胡語。不然,何以史、漢多次記載“祁連”一詞,但是其本文卻從來沒有對它的族屬及音義加以解釋。這應是由于其時人對此類單音節詞緩讀而產生的雙音節詞,是不言而喻的,故毋庸再加解說。
另外,德國歷史學家弗里茨·霍梅爾(Fritz Hommel)則認為該詞源自蘇美爾人的“Dingir”一詞,意為“神”或者“明亮的”{5}。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因為蘇美爾人的“Dingir”一詞與漢語的上古“天”之音義皆有較大差異,且東西種族語言之源流關系更欠充足論證。
其次,退一步說,即使“祁連”是匈奴語,也不能因為有三個“燉煌”與“祁連”連用之例,而實際只有《史記》一個是較為原始的,就證明“燉煌”也是“胡語”詞。因為在《史記》、《漢書》中燉煌與酒泉、武威、張掖等純漢語地名詞連用之例更多,豈非也可用做其為漢語詞之證?
更為重要的失誤,是劉先生將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說成是燉煌的“土著居民”。其實,最早在《史記·西南夷列傳》已區分“土著”與“移徙”兩類民族說:“自筰以東北……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6]其后,《史記·大宛列傳》明確記載大月氏、烏孫、匈奴等皆非土著的城郭之國,而是“隨畜移徙”之“行國”,正如南朝劉宋裴骃《集解》釋“行國”說:“徐廣曰:‘不土著。”[6]《漢書·西域傳上》對“土著”與“不土著”的居民也有明確區分說:“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其中夾有顏師古對“土著”一詞的注釋說:“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而徙也。”{1}由此可見,由于大月氏等“行國”沒有固定的城郭或鄉鎮之類的居民點,故不可能有相應的地名留下。假如在大月氏、烏孫、匈奴控制時期中,河西地區曾有零星而短暫的土著居民點,應該就是漢武開邊驅逐匈奴以前的華夏族農耕之民流亡于該地區所建立。在缺乏強大的中原王朝的軍事力量保護下,它們不可能有幾年時間在游牧民族對土著居民的殘酷打擊搶掠下生存。因此,在漢武開邊驅逐匈奴以后,才開始陸續在原來基本沒有土著居民的河西走廊尤其是在燉煌地區,建立起以漢族兵農為主的一系列鄉村城鎮縣郡等定居點,并開始有相應的地名。
三 再論“燉煌”為漢語詞之理據
如前所述,《史記》明確記載大月氏、烏孫、匈奴等皆非土著的城郭之國。因此,他們不可能有由其建立和命名的城郭等,為后來的其他民族作為地標性名詞所沿用,這本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既然有不少學者皆誤以他們為敦煌地區的土著居民,而且“燉煌”這一名詞是由他們傳給漢人,所以還要補論糾正。
1. 略論匈奴等“行國”無本族地名可作區域標界
由于匈奴既無文字,又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所以其“各有分地”的區域劃分的地標名稱,歷來都是借用漢族與匈奴交界處的漢人所建城郭名稱。而用這種方法記述匈奴等少數族裔居處區域變化范圍的,乃濫觴自商周。《史記·匈奴列傳》載:“(周)武王伐紂而營洛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暴中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胊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這種以漢族地名標示胡族區域之古法,至秦漢不替。例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述秦漢時期匈奴主要官名及其控制的區域劃分如下:
……諸左方王將居東方,值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值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值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再看,唐司馬貞《索引》對其中的“單于之庭”加按語說:“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產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可見,一則由于匈奴的單于并無固定的駐地,二則其語言中原本就沒有類似漢語城郭、宮殿之類的名詞。故只能由漢人以漢語的“庭”譯稱之。既然其單于都無固定的駐地及其語名稱之音譯傳世,那么其下的王侯官員皆無此類名稱之音譯傳世,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雙方都是沒有固定的地標的游牧民族,就無法用漢族的地標名稱為其劃界了。例如,《史記·匈奴列傳》載冒頓單于時匈奴與東胡兩大國族間“中有棄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此文的“甌脫”,《集解》注引韋昭曰:“界上屯守處。”而《索隱》引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正義》案:“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可見匈奴等族邊界只有統稱“甌脫”的細小的臨時哨所,根本沒有特別名稱的固定邊防城鎮可資記載。《史記·匈奴列傳》及《漢書·匈奴傳》所記匈奴控制區內的城鎮,只有一處,這就是漢降匈奴的將領趙信于闐顏山所筑的“趙信城”。就連目前所知這唯一的匈奴區內之城,也是以漢化胡人之漢名“趙信”命名。其后《史記》所記有關匈奴邊界的地標性地名,都是沿用前文的方式,采用漢族地名或漢族對其他民族的漢語名稱,而無源于匈奴語的地名音譯。例如,《史記·大宛列傳》載:“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南……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又載:“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故此,如果要運用類推法來分析有關《史記》所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既可以推定其“敦煌”也可能是后人之追書,而且可以推定其與“祁連”皆為漢人命名的地標性名詞,絕對不是匈奴、烏孫、月氏之類的“行國”民族的胡語名詞。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史記》記載是寫給中國皇帝及有關官員看的,有關國族區域和分界的地標名詞不可能用一個古今人皆沒有說明,其意義及族源皆無法考究的所謂“少數民族”的名詞。
2. 從周秦漢對新設邊鎮關塞郡縣之命名看燉(焞、敦)煌的族源
如前文所述,筆者二十年前之文已經認為,“因為孔子提倡‘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見《春秋谷梁傳》桓二年)。尊孔崇儒的漢武帝是不會違背這個原則的,所以漢朝既不會沿用最近被其驅逐的敵國匈奴的地名,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屬和意義皆不知的“一種土名”的譯音,來作為一個新開疆而設立的重要的軍事行政地區的名稱。武威、酒泉、張掖、燉煌等四郡的命名,充分體現了對‘名從主人的原則的實行。”現在再補述《史記》所載周秦漢時期中原王朝對匈奴等少數民族戰爭后的新設邊鎮關塞郡縣等的一系列命名,就可以更加清楚“燉煌”絕對是出于漢人的漢語名詞。
(一)周秦的新設邊鎮關塞的命名
(1)《史記·匈奴列傳》載周代“詩人歌之詩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對此唐張守節《正義》的注解說:“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筑城守之。”
(2)其后文“義渠”的《索隱》引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大荔”的“《索隱》案:‘《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更名臨晉。”而本傳下文更明確記載:“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
(3)其后文又載:“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云中、雁門、代郡。”
(4)其后文又載:“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6]
(5)其后文又載:“后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壍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余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以上表明周朝至戰國乃至秦朝的漢族諸國在占據胡族之地后皆以漢語詞為新設之城鎮及郡縣命名。
(二)漢朝的新設邊鎮關塞郡縣的命名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2)《史記·匈奴列傳》載:“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3)其后文又載:“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盧朐。”(譚按:此句“五原塞”的《正義》引《地理志》云:“五原郡茩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軓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案:即筑城鄣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
有關例子不勝枚舉,可以看出,漢朝對新設邊鎮關塞郡縣的命名基本沿用周秦的慣例,絕大部分用具有明確意義的漢語名詞來命名。正如筆者的舊作已經指出,《水經注》卷2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可見,就連“郡”字本身都與中國的君主有關。又據《漢書·張騫傳》載:“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此古圖書,應指《爾雅·釋丘》說:“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昆崘丘。”[17]可見,漢以前古籍之“昆崘(昆侖、昆侖)山(丘)”應為漢語詞。有認其為外來語者,乃誤以為“‘昆侖二字作何解,《(水)經》、《注》均未提及,僅言是山而已。”[18]其實,在“敦丘”、“陶丘”、“融丘”、“昆崘丘”等有關山丘的名詞中,“敦”、“陶”、“融”、“昆崘”等都是沒有獨立詞義的語素,它們都只是在與“丘(山、墟)組成的名詞中才有“一成”至“三成”等意義。故《爾雅》以及《(水)經》及其《注》均不會離開有關山丘的名詞或山丘的詞義單獨解釋其敦”、“陶”、“融”、“昆崘”之義。例如,《水經注》卷一“昆侖(昆崘)墟在西北”句之《注》首引就是“三成為昆崘丘”之說。其后又引《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三級……”{1}從漢武帝“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可見其對新拓展的西部疆域之地理及地名的高度重視,即使是自然的山川之名,也要由他親自研究中國“古圖書”的有關記載和定義來命名。再根據東漢應劭等古人的注解說明,可以知道漢代的一系列郡、縣、亭、鄣等城鎮命名取義的原因。諸如金城,因在城下得金,或指是用金來形容該城的堅固。酒泉,因為有泉水甘味如酒。張掖,其寓意為“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武威,其宣示漢朝強大的武裝力量之意不言而喻,所以應劭及前人對此名不加注解。對于燉煌,應劭特別解釋為“燉大也;煌,盛也;”其寓意漢朝的文德大盛。至于“縣曰冥安,蓋因冥水得名”。效谷,“本漁澤鄣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漁澤校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為縣名”;淵泉,“師古曰:闞骃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 廣至,其名見詞明義,不用解釋。原注只說:“宜禾都尉治昆侖鄣。”龍勒,其名也見詞明義,不用解釋。而李正宇認為,“‘龍謂駿馬,‘勒即馬籠頭頭……‘龍勒合言,若曰‘天馬收勒之地。”[9]23當然,另有個別顯然是出于其他原因的考慮而保留對被征服民族的個別詞義不明的音譯名詞來命名一些地方,即使不能注明其義,也要注明其族源。例如盧朐,就只注明其族源為匈奴。至于“頭曼城”是前述新設邊鎮關塞郡縣名字中,唯一以匈奴單于名字的漢語音譯“頭曼”來命名而又不加注的特例,應是有當時人不言而喻的特別用意和原因。筆者認為,正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載:當時漢朝所擊破并要消滅的匈奴王國,乃是由冒頓單于才開始將它擴張至“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譚按:其時的“中國”就是漢朝)為敵國。”而冒頓則是靠搞陰謀射殺其親生父親頭曼單于而奪取單于之位。漢朝特別將燉煌的一個城鎮以“頭曼”命名,這與清朝為被明朝子民造反逼得自殺的崇禎皇帝禮葬建陵相比,乃異曲同工,而且具有更加重大的政治道德文化的意義。其核心的意義,就是完成由漢文帝時派使節向匈奴發起的文明道德攻勢,證明倡行儒家的家庭倫理道德的漢朝文明遠遠高于匈奴的“賤老”、“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等野蠻落后的習俗。通過“燉煌縣”及“頭曼城”的命名,宣示漢朝戰勝匈奴,不是單純的武力勝利,更重要的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借此讓匈奴的主動歸降者或被動投降者永遠記住,漢朝將靠弒父起家的冒頓單于王國消滅是正義合理的,漢朝將會在新設立的郡縣繼續推行文明道德以取代其野蠻習俗。冒頓弒父起家之事在當時的漢、匈兩族是人所共知之事,故漢朝最早歷史檔案記錄者無需對“燉煌縣”及“頭曼城”的名稱意義預作解釋說明。
四 結 語
自從東漢應劭等人略作解釋之后,至清代兩千年多間,從來沒有學者注家對有關燉煌等地名的漢語意義產生過懷疑或提出過不同的看法。
有關燉煌等地名的族源及意義成為難以理解的歷史問題,乃因時過境遷,使得原來完整的漢朝歷史檔案數據在兩千多年來不斷遞減的過程中變成碎片流傳于今世,而導致當代片面的歷史研究者的困惑不斷增加。特別是由于有關問題實際是由原來對中國歷史文化及《史記》、《漢書》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理解的現代歐洲漢學家提出的偽問題,然后由他們及同樣一知半解的日本漢學家對偽問題作出的種種錯答案,形成了先入為主的一些誤論的影響,而導致了所謂燉煌為胡語的音譯詞之說在中國普遍流行。甚至還有學者僅據唐以后一度占領過河西走廊的藏族留下的“莊浪”一詞在“今藏語義為野牛溝{1},因而得晤(譚按:晤應為悟之誤)張掖的原意是野牛之鄉”從而認定“張掖”與“敦煌”等都是羌語詞:“敦煌之為羌語譯音,蓋與莊浪、張掖、刪丹等相同。”“最終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對音來,這在現代的藏語中是‘頌經地或‘誦經處的含義。”[19]如此胡亂找來比“張掖”后出一千多年的“莊浪”,以及比“敦煌”后出兩千多年的“朵航”作為“張掖”與“敦煌”的辭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欲要弄清這個百年懸案,必須源流都要厘清,既要把百多年來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史基本研究清楚,同時還要把《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的源流弄清楚。做好這兩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分清是非真偽與正誤,了結此案。
(本文原為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現作了一些刪節修訂)
參考文獻:
[1]李偉國.敦煌話語(插圖本)——名家與名編·世紀初的對話[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李正宇.敦煌歷史地理導論[M].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32.
[3]劉進寶.敦煌學通論[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3-8.
[4]郝春文.敦煌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3.
[5]陳國燦,陸慶夫.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歷史卷(2)[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1-2.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司馬光.資治通鑒[M].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634.
[8]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9]李正宇.敦煌郡各縣建立的特殊過程[J].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11(6):23-29.
[10]譚世保(寶).燉(焞、敦)煌考釋 [J].文史:第37輯,中華書局,1993:55-64.
[11]李正宇.渥洼水天馬史事綜理[M].敦煌研究,1990(3):16-23.
[12]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1:53,583.
[13]賈文麗.漢代河西軍事地理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47.
[14]吳礽驤,余堯.漢代的敦煌郡[M].西北師院學報,1982(2):27.
[15]戴春陽.烏孫故地及相關問題考略[M].敦煌研究,2009(1):38-47.
[16]顧炎武.音學五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2:41,50-51.
[17]李學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爾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01-201.
[18]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14.
[19]李得賢.敦煌與莫高窟釋名及其杝[M].青海社會科學,1988(5):8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