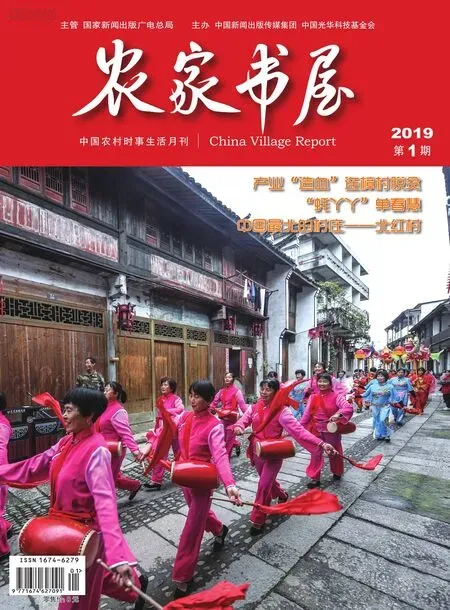鄉村書緣
趙金萍
小時候,每逢我拿著書本在院子里埋頭寫作業,奶奶就要坐在我旁邊念叨她的小曲兒:“從小讀書不用功,不知書中有黃金。不知書中黃金貴,夜點明燈用苦心。”
一般情況下聽到這個,我總是很煩躁,“誰讀書不用功啦?凈干擾人家寫作業!”于是忿忿地起身離去,“您老人家還不是大字不識一籮筐!”
確實,奶奶認得的字沒幾個。如果非要說準確些,除了“一”、“二”、“三”,她這輩子看見了認識并且能寫出來的字只有三個,那就是她的名字。
在農村,像奶奶這樣七八十歲的老人,大多沒入過學堂,認得的字自然也不多。我一直在想,一個不識字的舊社會老太太為啥老念叨讀書的好處,后來想到她是一位極其虔誠的基督徒,想必是從教友那兒學來的腔調,另外她居然還有一本厚厚的硬皮《新舊約全書》,據說價格不菲,我只有在她去教堂時才看到過幾回,雖然紙張已經變黃甚至發霉,但她還是寶貝一樣用布包了一層又一層。
當我自認為想通了事情的來由,不禁感慨起神靈的偉大:居然讓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村老太太明白了讀書的重要性!
然而,在我小的時候,農村還流行著一種觀念:女娃讀書不中用。這個“不中用”不是說女娃念不好書,而是長期受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父母普遍覺得送女娃讀書是讓整個家庭“虧了本”。
我的父母都念過書,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到小學就止步了,因為在他們即將升入初中時迎來了十年文革,此后便再也沒有踏入學堂。對于沒能一直上學這件事,母親現在看得很淡,只有在她的老同學聊天時奉承道:“你這學當初要是念得高了,現在當個省干部都不成問題!”本來口若懸河的母親會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一句話也不說,給人種“當不成就不當”的含蓄氣概,這時父親就要出來打趣:“她要是能成省干部,我就是國家級干部了!”然而私下里“對質”時,父親也不得不齜著牙偷笑默認母親的書念得確實比他好。
書念得好的母親沒能一直把書念下去,一方面是由于文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家里的孩子太多。母親小的時候,家里一共有六個孩子,她排行老四,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雖然母親家的生計在全村還說得過去,但讓這幾個孩子輪流都去上學顯然是吃不消的,恰巧又逢上個“把知識分子踩到腳底”的時代,母親便隨大流放棄學業,和她的姐姐們一起到黃土地上掙起了工分。
當母親向我談起她上學讀書的往事時,我總覺得除了文革和家庭經濟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重男輕女的思想在作怪。因為母親的兄弟姐妹們,也就是我的大姨、二姨,都沒有讀到小學畢業,小姨也只是初中畢業,而大舅卻一直念到了高中。母親和我的姨媽們似乎都默認,家里只要出一個能光耀門楣的男孩子就足夠了,她們都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自己上學的權利,甚至連書都不再去碰,因為大舅才是那個寄托眾望的人。
直到現在,我還很慶幸自己在懵懵懂懂的小時候就知道了讀書的重要性。
母親雖然被夸小時書念得好,但源于農村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她最初沒有打算讓我把書念深,直到后來對哥哥的學習成績極度失望,而我一直穩居學校第一名,這才改變主意沒有讓我在初中畢業后外出打工,還拉父親一起保證“砸鍋賣鐵”也要供我上大學。
聽母親說,我還不認字時就喜歡看書,在書攤前一蹲就是半天,看各種各樣的圖畫書。有時跟著父母去縣城辦事,看到書攤就死活不走,哭著拉著自行車不讓他們辦正事。
那時的我對整個世界充滿了好奇,急切地想要去了解所有未知的東西,但對一個孩子來說,在四歲多的時候似乎還想不到合理的方法。隨著時間的累積,我接觸到的奇奇怪怪的東西越來越多,疑問也越來越多,這居然給我了很大的精神壓力。當別的小孩蹦蹦跳跳去撒歡兒時,我正愁眉苦臉地坐在家里自問十萬個為什么。
直到小學一年級學會了漢語拼音,我感到一個全新的世界正向我敞開大門。我開始尋找所有帶字的紙張去閱讀,家里找不出一本課外書,我就翻看哥哥用過的教科書。那時的我小學還沒畢業,而哥哥的教科書都是初中版本。我把他所有的語文書翻出來,沒事的時候就拿過來反反復復地看,雖然將近一半的字都不認識,但我還是理解了其中大意。《包身工》中底層勞動人民生存的艱難,《白毛女》中農民對地主惡霸的仇恨,《灌園叟晚逢仙女》里除惡扶善的百花仙子,《楊修之死》里因才華致死的楊修,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都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豐富著我的童年生活。
當然,讀書的過程中我也遭遇過尷尬。初中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好不容易從同學那兒搞到一張借書證,歡天喜地地去縣城一家私人書店借來一本《簡·愛》。夏季雨后的一個下午,我慵懶地躺在床上,面對大開的窗戶,呼吸著雨后清新的空氣,正貪婪地閱讀著小說中主人公的故事時,父親進來了。他拿走我手中的書,翻看了沒幾頁,臉色就不對了。看慣了《英雄兒女》的父親大聲呵斥我:“小小年紀就看不健康的書,像不像話?!”我一聽急了:“這哪兒不健康了?上面不是寫著外國名著嗎?”“我不管是啥名著,這么多情啊愛啊是你小孩兒該看的嗎?”頗具革命精神的父親不由分說,拿著書就要撕,我急得一下子從床上跳了起來:“別撕啊!這是借同學的,壞了要賠的!”父親這才住了手,臉色卻依然很難看:“下不為例!”說完丟下書便走了,搞得我也哭笑不得。這件事給我敲了警鐘——原來不是所有書都能隨便看的,從此我再也不敢帶所謂的“情愛書”回家,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父親未免有些不通人情,但當時農村人教育孩子的思想水平就停留在那個地方。
在我的印象中,最富足的讀書時光不是在課堂,也不是在圖書館,而是在一家造紙廠。小學時有一個要好的小伙伴,她的母親在村子附近的一家造紙廠上班,有一次偶爾和她一起去找她母親,當看到那堆成山的書時,我一下子被震住了。“這些都是不要的廢書嗎?”我在書山腳下拾起一本小人書,感覺自己的兩只眼睛都在放光,“實在太可惜了,這么多好書就要被毀了”。從那以后,我就纏著那個小伙伴,要和她一起去造紙廠“找媽媽”,等過了守門老漢這關,我就一口氣沖上書山的“頂峰”,俯瞰整個書海,然后再選一處滿意的凹地藏身,之后大半天的時間,我不吃不喝躺在書堆里不停地看書,這本看煩了丟掉,再從另一處刨出一本,實在累了就枕著書小憩一會兒,身上還蓋滿了五顏六色的書。那時我心花怒放地以為,再沒有比我更高級的待遇了,這么多書,想看啥就看啥,多奢侈呀。然而好景不長,小伙伴的媽媽換了工作,自那以后,守門老漢也把我擋在了門外,我那極度享受的讀書光陰不得不告一段落。
小時候對讀書有那么熱切的愿望,現在長大讀了大學,身邊有數不盡的圖書資源,我卻發現自己不再熱衷看書了。
有一次回家,我和奶奶坐在客廳里看電視,那時她八十了,意識開始不清楚,有時連自己的女兒都認不出來,她看著電視上小孩兒讀書的鏡頭,突然轉過頭來問我:“你不看書了?”她微張著嘴,眼睛深深地陷進去。我震了一下,不知怎么回答。
我開始反思讀書二十多年對我的影響。確實,讀書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不是小時書讀得好,現在的我恐怕正在南方一家小加工廠干著機械重復的體力勞動;讀書讓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五彩繽紛,解答了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又一個疑問;此外讀書還讓我變得更加細膩,讓我從書中了解世俗人情,窺探不為常人所知的真實的人性。
懷著一種悼念式的情懷,我買來幾本文學書看了起來,卻怎么也找不回小時候心滿意足的感覺。這時我明白:放棄了讀書思考,知識和樂趣也轉身離我而去,就算后來又被拾起,但卻像感情破裂的情人,即便復合,也找不回原來純粹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