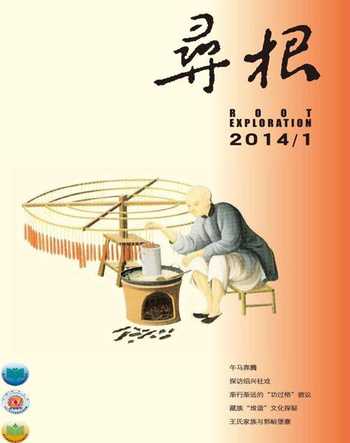普希金中文藝名考
平保興


對我國讀者來說,“普希金”已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別林斯基說過:“只有從普希金起,才開始有了俄羅斯文學。”我國對普希金的接受肇始于他的小說的漢譯。1903年,戢翼翚譯的《俄國情史》是我國正式接受普希金小說的開端。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他的《別爾金小說集》中的大多數小說譯成中文。長期以來,普希金的小說廣為人知,而他的中文譯名卻鮮為人曉,也一直未有專論。
普希金的中文譯名得從晚清談起。那是西學東漸的一個特殊時期,洋務派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譯介西學蔚然成風,國內報刊如雨后春筍,紛紛創立。普希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傳人我國的。從筆者掌握的史料看,晚清時期普希金的中文譯名主要有伯是今、普世金、勃蕭堅、普希罄、布希根、波喜金、普式庚、蒲軒根。
伯是今。日本古城貞吉譯。古城貞吉(1866 1949),號坦堂,又名古城坦堂,為日本明治時期中國文學史家,歷任東洋大學教授、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評議員,以著有日本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成名。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古城貞吉在中國出版的《農學報》《時務報》《昌言報》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1897年6月6日,他為《時務報》翻譯《論俄人性質》,文中說道:“夫俄人之好憑空論事,而少忍耐之力。詩人伯是今所夙稱也。其言云,昔有稱埃務劇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為大言,聳動人耳目,崇論閎議,沖口而出,然未嘗實行其萬一,居常蠢爾無為了此一生,是為俄人之情狀。”該文譯自日本5月26日出版的《東京日報》,這是目前我們所知的詩人的第一個中文譯名。
普世金。上海廣學會翻譯。廣學會是由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外交人員、商人等在上海創辦的一家著名的出版機構。1900年,該會出版《俄國政俗通考》,內有格利老夫(即克雷洛夫)、都斯篤依(即托爾斯泰)和普世金的名字。“有名普世金者,尤為名震一時。”此為普希金的第二個中文譯名。
勃蕭堅。麥鼎華譯。麥鼎華為康有為的學生,《時務報》主要撰述者之一。早年留學日本,譯有《社會進化論》《倫理學》《埃及近世史》《西洋史綱》《歐洲十九世紀史》等著作,享譽譯界。1903年7月9日,廣智書局出版他譯日本山本利喜雄的《俄羅斯史》。該書下卷第三十五章如是寫道:“今舉其文學界中之首屈一指者,則有勃蕭堅(Pushkin)、里門德輔(Lermontof)、克爾疎輔(Klotsof)、格利波輔(Gnboiedof)、格格爾(Gogol)、的伽涅輔(Turgenief)、孔查魯輔(Gontcharof)、卑謔士奇(Pisemski)、阿士魯威士奇(Ostrovski)等。至言文章之妙處,則有雄健,有典雅,有逸趣,有幽玄高妙之逸品,有透辟玲瓏之大作,諧謔百出,以描寫官吏社會、地主社會等之實況。”文中所述的作家,分別為我們今天所說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柯里佐夫、格里鮑耶陀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皮謝姆斯基和奧斯特洛夫斯基。顯然,勃蕭堅之譯名系從日文轉譯而來。
普希罄。戢翼翚譯。1896年,戢翼翚作為首批赴日留學生被派往日本。留學期間,他創立譯書匯編社,為晚清著名的文學翻譯家。他譯的《俄國情史》為普希金第一部漢譯小說,1903年上海大宣書局出版。這是《上尉的女兒》最早的一個漢譯本。此書全名《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又題《花心蝶夢錄》。據日本高須治助的譯本轉譯。高須治助的譯本轉譯自英譯本《The CaptainsDaughter》,譯成日文時,小說改名為《花心蝶思錄》。該書在明治十六年(1883年)出版,明治十九年(1886年)再版,注名為《斯密士瑪利傳》。1905年,小說以《斯密士瑪利傳》之名出版。關于此書,阿英在《翻譯史話》中說:“譯本封面,題作《俄國情史》,正文前才刻上全稱:《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一題《花心蝶夢錄》,原著者的名字寫作‘普希罄。大宣書局發行。重版時把書名改題為《花心蝶夢》。譯者姓戢,字無丞,湖北人,留日甚久。全書意譯,十三章,約二萬言。”
布希根。吳持譯,浙江錢塘人,晚清著名外國文學翻譯家。1907年,他譯的溪霍夫(即契訶夫)的小說《黑衣教士》,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根據日本薄田斬譯述重譯,后收入“袖珍小說叢書”。這是契訶夫第一篇中譯小說。全書共九章。在此篇小說中,契訶夫運用了普希金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詩句。如“吾雖至于狂癇兮,不能禁愛憐戀人之思”是《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詩句。這是我國最早譯出的普希金的詩句。
波喜金。朱陶、陳無我譯。1907年10月24日,《中外日報》刊登《大暴雪》,署名作者是俄國大詩人波喜金。法國小說家仲馬原譯,英國愛靈生重譯,中國朱陶、陳無我同譯,標“奇情小說”,登于“新譯小說”欄,共五章,1907年11月2日登完。這是普希金小說《暴風雪》最早的譯本。
普式庚。魯迅、周作人等譯。1908年,魯迅以“令飛”之筆名,發表《摩羅詩力說》,刊于《河南》第二、三號。這是我國介紹西歐進步文藝思想的一篇著名論文,內有俄羅斯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的文字。“當十九世紀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先覺諸邦之概,令西歐人士,無不驚其美偉矣。顧夷考權輿,實本三士:日普式庚,日來爾孟多夫,日鄂戈理。前二者以詩名世,均受影響于裴倫;惟鄂戈理以描繪社會人生之黑暗著名,與二人異趣,不屬于此焉。”“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獨立。”此外,該文還提及普希金的《阿內庚》,即《葉甫蓋尼·奧涅金》。是年,周作人以署名“獨應”,在《河南》第九期發表的《哀弦篇》,稱果戈理的《田園之夜》“為普式庚、如珂夫斯奇所賞,爾后戈郭理名遂盛傳”。之后,這一譯名被廣泛傳播和使用,林薇、徐中玉、黎烈文、戈寶權、曹靖華等為其主要譯介者。
蒲軒根。冷、毋我、周瘦鵑譯。“冷”為陳景韓(1878-1965)之筆名,此外還有冷血、不冷、華生、無名等筆名。陳景韓,松江縣人,善寫小說,擅長翻譯,譯作頗豐。胡適對他譯文評價是:“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譯的普希金的小說《俄帝彼得》,發表于1909年10月《小說時報》第一期“名著雜譯”欄。他與毋我合譯的小說《神槍手》,刊于1911年10月《小說時報》第十三期。1912年,毋我譯的小說《棺材匠》,發表于《小說時報》第十七期。1926年,外國文學翻譯家周瘦鵑翻譯的小說《游俠兒》,刊于《紫羅蘭》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周瘦鵑將作者譯為“蒲軒根”。
民國時期,普希金的中文譯名有別于以往,主要有蒲希根、普希金、樸思硁、布雪金、普斯金、樸士金、普式金、普希庚。
蒲希根。陳小蝶譯。陳小蝶,浙江杭州人,為陳蝶仙長子,多才多藝,擅長小說詩文,繪畫理論造詣也頗深。1916年,他譯的《賭靈》,發表于《小說大觀》第八集,小說今譯《黑桃皇后》。
普希金。瞿秋白、沈穎、安壽頤、耿濟之等譯,他們為北京俄專的學生,五四時期致力于俄羅斯文學的譯介,成就卓著。1920年7月,瞿秋白的《論普希金的〈弁爾金小說集〉》和《〈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收錄在北京新中國雜志社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安壽頤譯的《甲必丹之女》。這是《上尉的女兒》的另一個譯本,書中有耿濟之、鄭振鐸寫的序文,耿濟之寫的《普希金傳略》。之后,茅盾、宏徒、馮和法、孫衣我、徐聲濤等皆用過此名。
樸思硁。西曼譯。西曼,原名張西曼,為五四時期俄羅斯文學的傳播者之一。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九期發表他的《俄國詩豪樸思硁傳》。該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晉希金的生半和作品情況,其中這樣寫道:“樸氏作了《告毀謗俄羅斯的人》和《波洛紀諾紀念日》兩篇詩,以喚起同群的愛國心。此等詩篇,雖不免對于祖國多所曲護,但出之百年前人的眼光,自然是不能責備的。一八三三年,樸氏被推為‘俄羅斯學會的會員。他作《甲必丹的女兒》一篇小說之先,曾親自到了加章和莪熱布耳格兩省,采訪關于這篇著詩的材料。其中事實,是在蒲加覺夫叛亂時發生的。一八三四年樸氏因為發刊《蒲加覺夫叛亂史》的單行本,得了政府二萬盧布的補助金。他的詩名,雖然成就了,卻是一般鬼蜮社會對于他極盡構陷的能事。”
布雪金。胡愈之、胡仲持譯。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社會活動家和翻譯家。他翻譯的小說《喪事承辦人》(今譯《棺材匠》),署名原作者“布雪金”,發表于1920年《東方雜志》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胡愈之在“序”中說道:“布雪金的思想,起先是受法國十八世紀文學的影響。”此篇小說是從1831年出版的小說集《Talesof Byelkin》里選譯的。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1900 1968),從上述英文譯本翻譯了《莊主的女兒》。此篇小說發表于《東方雜志》第十八卷第八至九號。在小說下旁注“俄國布雪金原著”字樣。
普斯金。鄭振鐸譯。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祖籍福建長樂,為文學史家、著名學者和翻譯家。1921年9月,他翻譯的《莫薩特與沙萊里》,署名“普斯金”,刊登于《小說月報》第十二卷“俄羅斯文學研究號外”。
樸士金。孫照譯。他翻譯的《回鄉》,刊于1921年7月16日《晨報副刊》。此篇實為《戈硫辛諾村源流考》的節譯,其中開頭這樣寫道:“急切想著重見故鄉——就是年輕的時候,在那里嬉游過的——的念頭,很不耐煩地把我的自身充分的占領了,我便時時刻刻的催促那個驛車夫,又允許給他些兒酒錢。”
普式金。艾昂甫、李文望、木子譯。1937年2月《新詩》第五期刊登他們譯的《普式金詩抄》。
普希庚。依然、季明、碧泉、立達、陳秀文等譯。1937年2月,《蘇俄評論》第十一卷第二期分別發表《普希庚百年祭紀念特輯》,內有《蘇聯為什么紀念普希庚》《普希庚與俄國文學》《普希庚的決斗》《關于普希庚》《普希庚的生平》《全世界紀念普希庚》《普希庚百年祭在蘇聯》《普希庚百年祭》。此外,黃源的《普希庚的一生》一文,1937年2月15日刊于《月報》第一卷第二期。
在20世紀50年代前的我國翻譯界,同一外國人名擁有五花八門的中譯名,這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正如許地山先生所言:“所譯的書所用的字也是犯這個毛病。Toistoi有托爾思泰、杜思臺、托爾思臺、多爾思梯的寫法;Darwin有達爾文、多爾溫、達威的寫法;Euclid有歐克烈、歐幾里德、優克里德、游幾烈的寫法;這些人的名字差不多天天要接近我們的眼簾的,你看那么平常的譯名還有如許變化,那不常見的人名,可不教人摸不著頭腦嗎?”譯者“要在本國文字里找一個和外國音相近的字,是很不容易的”(《我對于譯名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
那么,為什么普希金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那么多的中文名字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轉譯。普希金早期的中文譯名大都是從日文轉譯的,如古城貞吉的“伯是今”、麥鼎華的“勃蕭堅”、魯迅的“普式庚”、戢翼翚的“普希罄”,上海廣學會的“普世金”,陳景韓的“蒲軒根”,胡愈之、胡仲持的“布雪金”,均從英文“Pushkin'的發音譯出。二是譯者隨主流的譯法使用譯名。魯迅采用“普式庚”一名,因此30、40年代的譯壇使用這一譯名較多,這與魯迅的文學聲望和地位不無關聯。另外,如陳伯吹既用“普式庚”[《小金公雞的故事》(蘇俄·普式庚),《文藝春秋》,1947年,第四卷第一期],又用“普希金”(《普希金與兒童文學》,《文藝春秋》,1947年,第四卷第二期),在同一份刊物上,僅一期之差,用了兩個不同的譯名,這說明當時的譯介者隨意性很大,刊物對外國人名的翻譯標準沒有嚴格的規定。三是缺乏統一的翻譯標準。普希金的俄文原名為Александр СегевичПушкин。如果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辛華編的《俄語姓名譯名手冊》“俄漢音譯表”,“Пушкин”的中文譯名應為“普什金”,而不是上述譯名,然而當時我國尚無統一的俄漢音譯標準。如今通用的“普希金”之名,已經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象征符號。從翻譯方法來看,上述譯名的譯法主要是音譯法,如布雪金;音、義并用譯法,如普世金,不僅與原名音相同,而且蘊含著基督教普世思想和價值觀,如金子一般閃亮。而“普希金”之譯名,與他在俄羅斯文學上的歷史地位一樣。這兩個譯名音義皆備,為相當不錯的名字。
由上可見,普希金的中文譯名經歷了一個從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翻譯的譯名,到約定俗成多種中文譯名并存,最后回歸統一譯名的過程。翻譯是溝通不同國家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也是產生新的獨特文化現象的媒介方式,上述“Пушкин”的16個中文譯名,已經為我們作了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