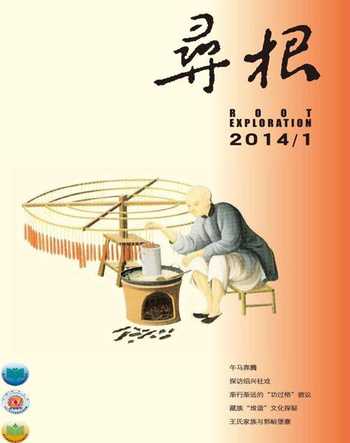泰順曾氏族產的發展與家族組織
吳洋飛
一
浙江省泰順縣交陽曾氏是清朝嘉慶二十年(1815年)由同安新橋頭遷徙而來的。
交陽曾氏一世祖為肇作公。肇作公的胞弟肇力公,于嘉慶己卯年(1819年)亦由同安新橋頭遷徙泰順大丘頭,為大丘頭曾氏之一世始祖。大丘頭曾氏與交陽曾氏雖并非同一個始遷祖,但其血緣和地緣是最為接近的兩個兄弟之族。由于本文以交陽曾氏的發展為主線,因此對大丘頭曾氏則略而述之。
二
曾氏剛遷至泰順縣交陽時,無任何產業,到1950年重修的宗譜里就明確記載曾氏宗族共擁有9處祭田,年收租545貫;8處眾管宅宇基地,包括祠堂、牌樓、倉庫、道路、水塘等產業;12處眾管山場。這里還不包括曾氏析產分家之后,變為個人私產的屋基、田地、山場等。短暫的一百多年問,交陽曾氏從白手起家,到擁有大量的族產,充分證明曾氏一族對于族產的重視和珍惜。到1982年,該支已繁衍了九代,五百多口人,形成一個頗具規模和影響的宗族。
據曾氏宗譜記載,肇作公未正式舉家遷入泰順交陽時,其子拱辰公已在交陽置辦產業,為全家遷徙做準備:“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初三日,買的徐允成(志即光)祖山一片,約有五里闊,坐落四都交陽小洋尾……去紋銀二十兩正,又三月十八日立契去紋銀四兩正。”這些產業足以支持全家來泰順最初生產與消費所需。
嘉慶二十年,肇作公攜全家到泰順交陽定居,曾氏一家開始在交陽大量購置產業。
從嘉慶二十年到成豐六年(1856年)的40余年間,交陽曾氏子弟繁衍至第5世。按照中國傳統宗法制觀念,曾氏初具一族之規模。除卻世系、人口,曾氏經過多年置辦的各類產業也足以支撐整個宗族構架的形成。據統計,在此期間,曾氏通過各種方式置辦產業交易達147宗,平均每年置辦4宗左右,其中包括購買、典當以及交換的方式進行,而產業涉及田畝、山場、房屋、基地等。
購買是交陽曾氏置辦家族產業的主要方式,在147宗交易中,采用購買達成交易的占139宗。例如:“嘉慶二十年七月初九日,買得一都陳世文(子肇賢)水田一號,坐落交洋后洋(即厝后及厝右),種六貫,租一百五十貫,計民畝四畝,正東至買主田,南至買主田,并周沈二姓田,北至董、繆二姓田,西至繆家田及墳。去紋銀七十兩正,七月十九日立截契去紋銀二十兩正。”“成豐四年十二月廿九日,買得韋忠安仝弟侄等荒田四號,計種二貫半,計冬租五十貫。坐落四都交洋后洋小洋尾缸窯壟,安著。底三號,上左右俱至山,下至曾宅。田外一號,上左右俱至山,下至周家田,并荒熟子在內。此田原系時荒時熟,遵例不報升科,亦不另立截。立契約去價錢二十二千文正。”
典當也是交陽曾氏積累家庭財產的方式之一。隨著曾氏在泰順交陽定居日久,整個家族的經濟實力得以增強,族際之間的交往也日益增多。無論是姻親還是鄰近友族,在特殊情況下,都會將本族的產業典當于曾氏一族,請其暫時保管,以便日后取回。如:“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當得齊長興水田一號,坐落四都南山山底,土名外項安著,計種五貫,計租一百貫,計民畝一畝正。東西南北四至俱山,其糧餉齊旁,白行完納。如遇十六年以外不能備贖,任聽曾邊稅契,權畝過戶,永為己業,永無回贖找貼。當去價錢三十千文正,又廿六年三月初六日立找契,去錢三千文正。”
盡管契約上寫明典當人有贖回的可能,但是這些典當的產業到最后往往成為曾氏的私有財產。
除了上述兩種方式取得各種產業之外,因為某種需求,曾氏還會通過交換的方式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產業:“道光四年二月十一日便得鶴巢宮山場三峰,坐落四都交洋亭對面,北畔安著,其山上至峰頂,分水為界,下至田為界,左右二至龍虎峰,直落分水為界便去水田二號,一在交洋亭底,彭監丘田三丘,種一貫半,租四十五貫,又一號在鶴巢宮下安著。田一丘,種半貫,租二十貫,共計種二貫,計冬租六十五貫,計民畝一畝一分一厘正,文起公戶推出。”
交陽曾氏以上述三種方式在40余年問,置辦了大量的財產,為整個家族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在這40余年間,其家族也由幾口人繁衍到五代數十口,家族建設也初具規模。肇作公在剛徙居到泰順交陽時,就開始“建正室為正寢,四時享祀”,隨著整個家族財富的增加,“后遂為祠廟之宇,旁筑夾室,及周圍水城數十間一以護祠風水,規模宏大,誠足鞏固之美觀”。祠堂一向被認為是一個家族正式形成的標志,在曾氏一族由最初設立正室實行祭祀之聚,到后來修建規模宏大的祠堂,證明曾氏真正成為交陽的一個大家族。無論是墳場的設置還是祠堂的建立充分證明曾氏一族組織的擴大,而這一切和其漸趨強大的家族經濟不無關系。
三
人口的不斷繁衍,必然要求足夠的生活、生產資料供應整個家族維持生活和發展。因此,交陽曾氏欲持續發展,并進一步擴大家族組織,必須繼續購置和積累族產,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定經濟基礎。
嘉慶二十年到咸豐六年的40余年問,交陽曾氏在嚴格意義上來說只能稱其為一個家庭,是由四代人共同組成的一個大家庭,而并非一個家族。一個家族起碼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家庭才能稱之為家族。
遍覽交陽曾氏族譜,雖然并沒有直接記載曾氏一族是在什么時候分房立派的,但是在泰順縣交陽曾氏族人手中珍藏的一份契約中,我們發現在咸豐六年契約之前明確記載有“分家后二房白置”的字樣,且成豐四年最后的一份購契是在十二月廿九日,咸豐六年最早的一份契約是在二月初八日,并未發現有咸豐五年的契約出現。至此可推之,曾氏分房應該是在咸豐五年,由于需要對原來的財產進行合理的分配,所以此年并無任何購置的行為。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咸豐初年,由于第五代人丁的繁盛,曾氏作為一個大家庭已經無法維系,只能實行分房,減輕個體家庭之壓力,同時壯大整個家族。
自從咸豐五年分家之后,各房便開始自置產業。從咸豐六年至宣統二年(1910年)的54年間,曾氏各房共出現27宗購置交易,與之前42年的147宗交易相比大大縮水。在這27宗交易中,交換田產1宗,典當交易4宗,其余為購買交易。如仁房自置:“同治十二年十月廿九日買得保之仝云慶水田一號,坐落四都交洋,土名牛羊坪洋心安著,計種五貫,計冬租一百七十貫,及民畝三畝正,其田東至買主田,南至曾劉二姓田,西南二至潘高二姓田,北至曾胡二姓田。其畝向奎象戶推權過戶,立契去錢八十千文,又十二月立截契去錢六十四千五百文正。”
此時期,雖然各房獨自置辦產業,且購置族產的數量并不能與其前期相比,但是其置辦產業的增加,也就意味著共有族產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成為支撐一族持續發展和其組織擴大的基礎。光緒壬寅年(1902年),泰順交陽曾氏與大丘頭曾氏首次聯合修譜,以源支脈、辨昭穆。聯合修譜的費用大部分由共有族產支付,其余在族內按照人口數進行分派。而聯合修譜這種行為的出現恰恰表明曾氏一族之組織在原有的基礎上得以進一步擴張。
從清嘉慶甲戌年(1814年)到宣統二年(1910年),在這近百年間,泰順交陽曾氏從福建徙居泰順,以白手起家之姿,不停購置族之產業,發展各項家族事業,不斷完善家族組織,并成長為泰順一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家族。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毋庸置疑,族產的增長為整個家族組織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