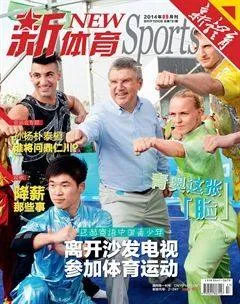蘇之渤,夢里仍在舉槍
若不是穿著一件印有國旗的運動T恤衫,在住滿高校老師的北京育新花園小區,一般人很難看出蘇之渤原本是運動員,更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國第一枚亞運金牌獲得者。不過,小區文化活動站的人們熟悉這個矮壯的老者,因為他愛運動,幾乎每天都來這里打乒乓球。
其實,蘇之渤一直最為喜愛的運動項目在這里找不到,如今也只有在心里,甚至在夢里去找。多少次他夢見自己走向靶場,右手舉起手槍,屏息靜氣地瞄準,靶子清晰可見,可訓練還是比賽卻搞不清……
這是他從1962年起千錘百煉形成的職業習慣和動作定型。憑借著它們,40年前,蘇之渤圓了自己“為祖國爭光”的一個夢。
1974年9月,中國第一次組團參加在伊朗德黑蘭舉行的第七屆亞運會。大賽第一天,26歲的蘇之渤和三位隊友站在手槍慢射的比賽場,心情難免有些緊張,但他很快就平靜下來。比賽為兩個半小時,自己把控時間。蘇之渤試射十幾發之后,就要了計分射。打到第二組時,出現88環。蘇之渤反復思索,有時舉槍起落5次,直到感覺有把握時才扣動扳機。之后他越打越順,最后兩組連續取得94環的好成績。60發全部打完后,時間還余下十多分鐘。此時,他的成績是全場最高的,但一名日本選手還沒打完。如果他發揮正常,成績應與蘇之渤不相上下,而且總成績需裁判最后核準公布。
直到回亞運村吃完午飯后,比賽的最終結果才從電話里傳過來,蘇之渤以522環獲得個人冠軍。下午3點鐘,蘇之渤站到最高領獎臺上,但他全然不知胸前那塊金牌居然創造了歷史,那是中國在亞運會上的第一金,也是第七屆亞運會的第一金。
盡管如此,蘇之渤沒有得到一分錢獎金,連禮服、運動服、背包和手提箱都是從國家體委借來的,賽后如數奉還。那時正值“文革”年代,反對金錢掛帥和錦標主義,蘇之渤得到的只有一紙“表現優異,予以鼓勵”的獎狀。在新聞報道上,這位冠軍名前的“頭銜”還是開封聯合收割機廠工人。這個名頭濃縮了蘇之渤此前三年的工廠經歷,也體現了當年突出“工農兵”形象的特點。
以后,蘇之渤又參加了第八屆和第九屆亞運會。在第八屆亞運會上他蟬聯冠軍,還打破亞洲紀錄,可謂一帆風順。但到了中國第一次組團參加奧運會之前,蘇之渤卻經受了重大挫折。備戰集訓時,他的右臂拉傷,醫生和他自己都沒太在意,只是貼副止痛膏。訓練時,蘇之渤仍有痛感,長久舉槍時出現晃動,成績隨之起伏不定。選拔賽后,一向成績居前的他排在王義夫和后起之秀許海峰之后。面對三個人兩個名額的選擇,隊里爭執不下。最終,還是王義夫和許海峰出征了1984年奧運會。
射擊人喜怒不形于色,蘇之渤外表平靜,卻心潮難平。
先去靶場,已成多年工作習慣
命運在1984年轉了彎。蘇之渤離開國家隊,經過綜合考試,進入了鄭州大學政治系干部培訓班,一學就是兩年。
畢業之后,他擔任了河南省陸上運動學校的副校長,以后又當了書記,學校下屬的運動項目中就有他的本行——射擊。
雖然不能再舉槍了,但蘇之渤離不開射擊。每天早飯后,他先去靶場轉轉,10點多鐘才回辦公室開會看文件。下午,他也是先去運動隊,4點多鐘再回辦公室。晚上他就住在隊里,只有周六才回家。那時,學校只有一部車子,蘇之渤總是騎上自行車,從鄭州的南郊騎到北郊的家,路上要花費一個多小時。冬天到家時,天都黑了。
就這樣過去了十多年,因為愛人調到北京一所大學工作,蘇之渤重回北京,在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射擊競賽處當了副處長。兩年之后,他又擔任了國家射擊隊領隊。
于是,故態重萌。早飯后,他還是先去靶場,與在河南陸校10點才回辦公室的習性有所不同的是時間又向后延了一小時。下午,他還要跟運動員一起上體育課。其實,他在靶場也不能打槍。運動員的槍都是個人專用的,一些部件是根據自己手型定做的。蘇之渤大多是在旁邊看,在心中尋找問題,適時幫助解決。許多問題雖出在練槍之中,卻屬訓練之外和射手內心的,處理起來往往比自己打槍還需細心和耐心。
有時隊員訓練情緒不高,他要去找教練交流;同一項目、同一宿舍的隊員之間出現矛盾,往往暗中較勁,他要及時發現,再分別進行“話療”。“射擊運動員的準星實際在心里,需要幫他們校正。他們打的不光是精度,還有心境”。為此,蘇之渤總是利用各種機會為隊員們注入正能量。一次全隊會上,大家讓他講幾句。他講起了毛澤東的《實踐論》,那些恍如隔世的抽象“大道理”被他拉近到具體可感的當前,拉到射擊場上,竟然講得全場凝神專注,鴉雀無聲。最后,他真誠地對大家說:“世界上沒有神仙,要是有,也是你們自己。只有自己不斷實踐、認識、再實踐,才能提高自己,拯救自己。在運動隊,社會上那種拉關系套近乎的做法是不頂用的……”他剛講完,隊員們就鼓起掌來。其實,蘇之渤的講話不是即興為之,多年的射擊經歷讓他深感毛澤東實踐思想的偉大,他上街特意買來《毛澤東選集》,細細研讀,認真準備之后,才做出此番發言。
曾經有幾年,蘇之渤擔任科研部主任,他仍然不斷地跑靶場。為了提高訓練的精確性,他為每個教練配備了激光測試儀。這種儀器安裝在隊員的槍頭,靶子上設有感應器,槍的穩定性被顯示在一個筆記本電腦上。一槍射出,任何偏差一清二楚,問題迎刃而解。蘇之渤不露聲色,內心卻比誰都高興。

退休在家,仍然渴望舉舉槍
2009年,蘇之渤退休。有運動隊邀他去做教練,他婉言謝絕:“我有高血壓、糖尿病,耳朵還不好。過去射擊時沒有耳罩,長期槍震讓我的耳神經受損,嚴重時連69分貝的聲音都聽不清,還是別給人家添累贅了!”
在大學當教授的老伴每日里教學科研,工作繁多。留學回國,在大學當副教授的女兒也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家中只有蘇之渤賦閑,但他的生活很充實。上午,他去小區活動站打乒乓球,還從直板改成了橫板,一面反膠,一面長膠。比賽發揮好時,他能在小區拿個名次。下午,他在家讀書,練書法,看電視。晚上,他去小區文化中心圖書室讀書閱報。他讀的書很雜,從傳記、史書到武打小說,看的報則主要是《環球時報》和《參考消息》。學校放假時,他和老伴去旅游,從三峽、三亞到臺灣,再到國外。在國外,他最喜歡的地方是瑞士。當年和運動隊坐大巴從米蘭到慕尼黑,途經瑞士,他被那里的藍天白云牧場深深吸引,因為那與靶場的環境很相似,可惜那次純屬走馬觀花。于是,去年他重去瑞士來了個深度游,一呆就是9天。
不過,無論怎樣,他的心里還是割舍不下老本行。媒體上只要有射擊的報道和轉播,他必看無疑。隊員比賽時,他跟著緊張出汗。隊員取得好成績時,他跟著興奮喜悅,忙不迭地發短信給隊里表示祝賀。至今,他還在為中國飛碟隊多年來苦苦努力卻只有一塊奧運金牌而百思不得其解,盡管嘴上說“我退休了,這事讓后人考慮吧”。
當然,他還是渴望親手舉舉槍,畢竟從小就與槍為伴。記得第七屆亞運會前,他被下放到工廠做鈑金工,用鐵棍焊了把“槍”,安上準星和照門,在宿舍墻上貼一個紙黑點,晚飯后樂此不疲地舉起“槍”練上半小時到一小時,只可惜那“槍”沒有擊發裝置。上世紀80年代初,他花了當時堪稱不菲的700多元,買來一支雙筒獵槍,可惜只試了兩發子彈,一次出獵都沒成行。隨著政府槍支管理法規的出臺,涂上黃油的嶄新寶貝也讓他上交了國家。如今退休了,有的是時間,可惜無處化解技癢。
某日,他看報發現國外有一種俱樂部,專門飼養大小動物,供人狩獵,內心不禁一動:國內要有這樣的場所該多好呀,哪怕多花點錢呢!可再一想,這可能有違國家法規,唉,又是一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