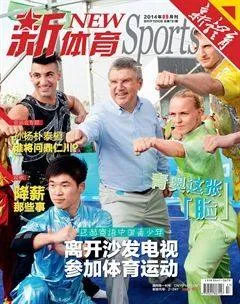中國人的麻將,與體育無關
今年夏天,麻將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在第五屆歐洲麻將錦標賽上,中國麻將國家隊遭遇滑鐵盧,僅僅拿到團隊第三十七名,個人最好名次三十名,團體冠軍被歐日聯隊奪走,個人冠軍亦被日本人納入囊中。
考慮到麻將在國人心中的地位,這結果堪比世界杯半決賽巴西隊的1比7。有人警示當年“十億人民九億麻,還有一億在觀察”,但隨著大媽們轉戰廣場舞,中國麻將有斷層的風險。有人聯想“單獨二胎”生育政策的推行,正是為了“拯救麻將”,“三缺一”的當代中國家庭模式嚴重消弱了麻將這一四人運動的群眾基礎……
更直接的救市之舉是在國家麻將隊慘敗后不到半個月,首屆溶洞麻將大賽和首屆“喜盈門”杯麻將大賽同時在四川火線開牌,以期從廣場舞界吸引大媽回流,重塑中國麻將的威權時代。
目前,麻將有三種存在形式:競技麻將、休閑麻將、賭博麻將。后兩者我們從來天下無敵,在歐洲輸掉的其實是前一個。但競技麻將的國標也是中國人設定的。早在1998年,國家體育總局就出臺過《中國競技麻將比賽規則》,其中要求“對”、“吃”、“和”等行為,都要用漢語說出來,說錯了還要扣分。全世界很多體育項目的比賽語言都是英語,惟有麻將要說中文。在推廣漢語方面,麻將立了功。
然而,近20年來,競技麻將開展得最好的卻是日本,光職業聯賽就有九級,完善度不遜于J聯賽。而吾國的麻將基本上還停留在休閑與賭博的階段,國家體育總局倡導多年的改革終究無語,競技麻將推廣最不力的地區恰是四川。
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國人打的是麻將,談的是人情,講究的是坑蒙拐騙煙霧裊繞說學逗唱,競技麻將非要跟斯諾克臺球一樣西裝領結一本正經不準喧嘩,中國選手未戰便已先輸了氣場。如此看來,國麻今夏輸于歐洲,倒也不算冷門。中國麻將如果想要如廣場舞一樣雄霸全球,非如NBA一樣設立獨立的競賽體系不可。
胡適曾說過英國的國戲是板球,美國的國戲是棒球,日本的國戲是相撲,中國的國戲是麻將。但對中國人來說,麻將永遠不是體育,而是文化。有中國人的地方,從來都少不了麻將聲。在中國風格的電影里,麻將一直都是中國人的永恒文化符號。
《色戒》中的麻將戲貫穿始終,太太間的虛榮攀比吃醋較勁,男女間的眉目傳情與暗戰,都在牌桌上暗自流動。《圍城》中張太太以麻將選女婿,方鴻漸贏錢失嬌娘的橋段更是將中國人對麻將的感知刻畫得入木三分。臺灣的楊德昌導演有部代表作就叫《麻將》。
毛澤東也曾說過,不要看輕了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系。”哲學也是文化的范疇。近年來麻將申遺的推手從來不斷,非遺的全稱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可惜直到現在,麻將申遺還是未能成功。當然,在4歲初涉麻壇14歲金盆洗手的我看來,這恰恰可能是麻將對于中國文化的真正貢獻。對于曾以六藝設定為君子立身之本的中國,麻將縱是文化,也不過是糟粕。有人說中國麻將源遠流長,數百年不倒,自有其內在價值,但我倒以為此論有典型的裝外賓之嫌。麻將風行的背后,說到底還是一個“賭”字,如果不是國人好賭的性格,麻將可能已如鼻煙和小腳一樣,早已滅絕了,談何遺產。
法國漢學家伊麗莎白·巴比諾說過:“麻將破除了命定的東西及人與世俗權力的關系。”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表面一團和氣,私下相互拆臺,信奉的是“我做不成的事,你也別想做成”。就像中國象棋講究一切為了保帥,中國軍棋講究官大一級壓死人,這些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游戲,反映的恰是我們骨子里的小。倒是國際象棋里王亦能沖鋒至前線親自打老虎,小兵堅持到底終將涅磐的規則,更像是“中國夢”的合理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