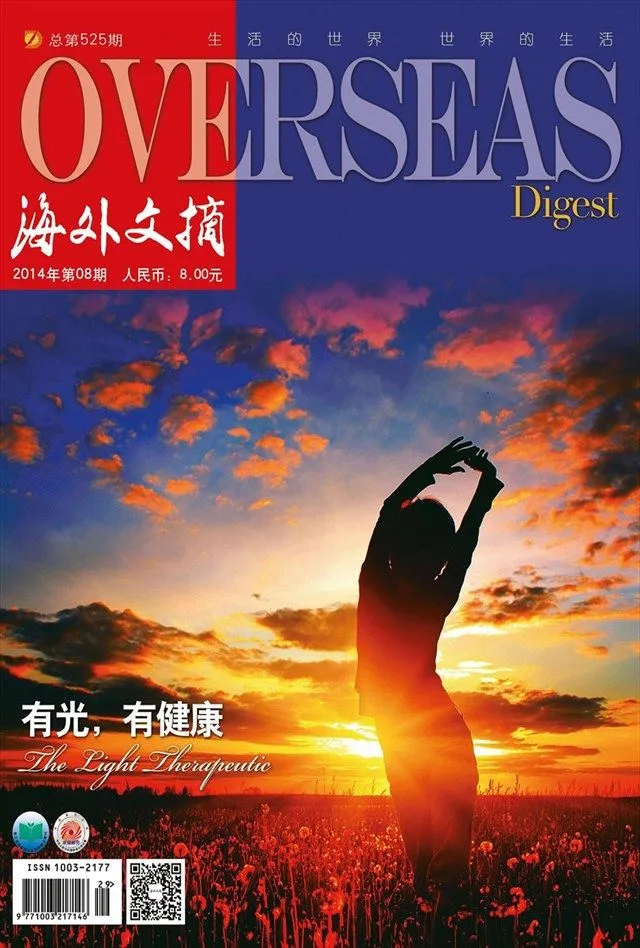樹之學校

德國下薩克森州一個晴朗的秋日,在公交和地鐵難以抵達的森林深處,一群人歡聚在一起,慶祝“不上學節(jié)”,反對國家強制義務教育。
這一節(jié)日持續(xù)了3天,300名參與者傾聽來自法國、英國和加拿大代表的演講。這些國家的父母可以選擇在家教育孩子。克里斯蒂安·路德維希-伍爾夫也做了報告,主題是“德國輟學孩子的法律處境”。她的長子伊曼努爾也是活動的組織者之一,站在門口收取入場費和餐飲費。為此要做出的計算對25歲的他來說有些困難,馬上就有人懷疑,這就是不上學的代價嗎?但是他的弟弟尤里也曾輟學6年,盡管如此,他仍在進入一所中學后很快成為班級的佼佼者。伍爾夫三兄弟的故事讓我們開始重新認識普通義務教育。
在家上課
90年代初,德國巴伐利亞州施瓦本山區(qū)的一個鄉(xiāng)村。每天早上,父親送伊曼努爾去學校時,他都會又哭又喊,怎么都不肯挪動腳步。他的父母對此很是無奈。一位教育專家建議他們,堅持帶伊曼努爾去學校上課6個星期,哭鬧就會漸漸停止。
然而這不符合這對夫妻對孩子的教育觀。他們希望保持孩子的自由天性,于是給孩子請了病假,母親克里斯蒂安開始埋頭苦讀教育學。她還聽了作家奧利弗·凱勒的一個講座。他對瑞士和法國不接受普通義務教育的家庭進行了研究,充滿熱情地向聽眾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她想:“如果其他家庭能夠做到,我們也會做到。”
由于這種教育方式在德國不被承認,克里斯蒂安撒謊說,伊曼努爾目前在奧地利上實踐課。有關部門對這個理由似乎很滿意,至少沒人追問她什么,西蒙輟學時甚至直接照搬了哥哥的理由。
1999年,這家人搬到了薩安州一片有著遼闊土地、牛馬和磚房的地方。他們買了一個帶著大花園的舊農(nóng)舍。這個村莊只有一條主街道,左右整整齊齊排列著一共10棟房子。小兒子尤里也到了上學的年齡,那時克里斯蒂安已經(jīng)確定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天生就有自學能力,其中包括生活技能,也包括閱讀、書寫和算數(shù)等文化技能,而帶有強制意味的學校教育只會阻礙這一學習過程。
在他們家,學習就融匯在日常生活中,外人甚至看不出來,就連學習者自己也意識不到。孩子們在建造汽車模型、玩沙、玩水的過程中學習。他們用積木搭建筑,學習捕魚,玩角色扮演游戲,下棋。家里有個閱讀室,里面陳列著許許多多各種主題的書籍以及數(shù)學、德語、英語和地理等各科的學習資料。
西蒙喜歡BMX越野自行車,玩自制武器;尤里喜歡在叔叔送的舊計算機上編程;伊曼努爾和父親一起制作象棋棋子,喜歡閱讀和遛狗。這三兄弟常常光腳四處亂跑,個個都是爬樹能手,在樹上無憂無慮地度過了一天又一天。克里斯蒂安說:大自然就是孩子們的課堂,樹木、小溪、土地和各種動物都是他們的老師。父親則簡單地總結:直接和自然接觸有益于孩子的教育。
官方反應
在他們的新家鄉(xiāng),男孩們的故事飛速流傳。有人向當?shù)亟逃峙e報了他們。當教育局官員卡爾·莫納爾特一天早上想和這家人聯(lián)系時,有人告訴他,這家的母親和3個孩子一起躺在自家花園中的帳篷里,還在睡覺。這位母親喜歡親近自然,孩子們不用上學,自然也就沒有理由早起。最后,莫納爾特還是決定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接見這家人,兩個世界發(fā)生了無言的碰撞:深秋,母親和孩子們光著腳來了。莫納爾特的同事們難以置信地看著這一幕,不禁向他耳語:“莫納爾特先生,您得做點什么。”
青年福利局也開始介入進來,接著是頻繁的通信往來。克里斯蒂安說:“伊曼努爾、西蒙和尤里強烈抵制上學,我只能使用心理或身體上的暴力行為強迫他們?nèi)W校。孩子們卻有在非暴力的前提下接受教育的權利,我無權對他們施暴。而且,孩子們在他們感到不適的狀態(tài)下,什么也學不進去。”因此對她的孩子們來說,在她能夠提供足夠支持的基礎上,在家學習是最好的選擇。
官方的反應如何呢?最初是令人吃驚的溫和。他們雖然給了這對倔強的父母多張罰單,同時卻也派出了特殊學校的老師馬汀·邁斯納,致力于讓孩子們重新適應學校生活。然而邁斯納很快就達到了他能力的極限。當他想教數(shù)學時,伊曼努爾提出抗議,他現(xiàn)在更想讀讀尼羅河岸邊的古老文化。當邁斯納講述德語第四格時,母親問這些孩子知道這個究竟有啥用。邁斯納很快就明白了,“是母親不想讓孩子上學,她腦里的思想根深蒂固,并不準備改變”。
他是對的。“媽媽對我們說,對邁斯納先生保持友好,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做任何我們喜歡做的事情。”今天的西蒙笑著說。而邁斯納也開始了解那些拒絕上學者的理論,甚至還買了奧利弗·凱勒所著的《因為我的生活就是學習》一書研讀,它被奉為拒絕上學者的圣經(jīng),倡導讓孩子們自主學習。邁斯納無法同意這一觀點:“這樣我們的文明將無法傳承下去。”他擔心這三兄弟將來能做什么,“他們怎能在我們的職場中找到一席之地?”
再入學校
這樣兩年后,法院終于開始對伍爾夫一家施壓:他們“通過保留教育權危害到了孩子的利益”,如果三兄弟繼續(xù)不上學,就剝奪他們的監(jiān)護權。父親萊因哈特·伍爾夫經(jīng)營著一家小小的建筑公司,經(jīng)常出差。那時他已經(jīng)和妻子分居了,住在不萊梅,但他們?nèi)匀还餐瑩碛泻⒆拥谋O(jiān)護權。萊因哈特向法官承諾,盡快讓孩子們?nèi)ド蠈W。
母親仍然不樂意剝奪孩子的自由,但是同意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那時伊曼努爾15歲,西蒙13歲,尤里11歲,他們非常害怕將來可能要在孤兒院生活,于是決定隨父親搬去不萊梅上學。萊因哈特于2003年春為他們在臨近的一所中學辦了入學手續(xù)。尤里上了六年級,西蒙上了八年級,伊曼努爾九年級。
不久就出現(xiàn)了意料之外的問題:他們的同學吸煙、偷竊,吵架時掏刀子。伊曼努爾常常爬上操場的大樹,以逃避認為他不合群的同學的拳頭。而西蒙所在的班級遠足活動被取消了,因為老師不愿意陪同這個非常沒紀律的班級出去。尤里班上有個女生患有憂郁癥,曾試圖自殺。當這一切被人知道后,一些同學嘲笑她是個什么都做不好、甚至連自殺也無法成功的失敗者。在上學的最初幾周里,這三兄弟經(jīng)歷的沮喪之多是他們在以前的人生中從未有過的。他們母親的顧慮“學校對孩子有害而非有利”以一種荒誕的方式得到證實。
而學習本身并沒有給三兄弟帶來困擾。只有在最初入學時,父親和男孩們一起坐在桌前,學習數(shù)學和英語。西蒙做算術仍然要用手指頭,英語也很讓他頭疼。一次,他要做關于美國猶他州的報告。“我不可能做到,只能得到差評。”他抱怨。他的父親幫他把英語報告一個字一個字地用德語發(fā)音的形式寫下來,最后老師給了他一個良好。其他知識漏洞也在幾個星期內(nèi)就填補起來。
紐約教師泰勒·加多幾年前寫過一本引起轟動的書《使我們蠢如一人》(Dumbing Us Down)。他稱每個人都有能力長期自學閱讀、書寫和算數(shù),而學校是讓孩子們對學習倒胃口的地方。這和尤里的經(jīng)歷不謀而合,他很快成為班級的佼佼者。而他的同學大多是為考試而學習的,考后很快又會忘記。尤里常常聽到同學對他說:“你的優(yōu)勢是,你仍然熱愛學習。”
幾周后,在沒有上過一天輔導班的情況下,他和兩個哥哥的成績都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西蒙最初還要努力應付數(shù)學和英語,最后也順利通過了畢業(yè)考試,尤里甚至以優(yōu)異的平均成績結業(yè)。只有伊曼努爾在讀11年級時輟學了。一次自行車旅行之后,他的一只手疼痛不已。醫(yī)生在上面發(fā)現(xiàn)了鏈球菌,并確定其已在全身擴散。只要晚治療一天,他的這只手就保不住了。伊曼努爾認為這次事故是結束學業(yè)的標志,畢竟受感染的是他寫字的手,父親萊因哈特決定尊重長子的決定。
故事繼續(xù)
現(xiàn)在伊曼努爾25歲了,平時售賣自制的手指布偶和皮毛坐墊。對于未來,他毫不擔憂:“我今天生活得很好,為何明天會有所不同?”23歲的西蒙曾在建筑工地打短工,目前開始了木工學徒生涯。21歲的尤里在波茨坦大學上學,同時為柏林藝術研究院和德國歷史博物館開發(fā)軟件。專家的各種負面預測都沒有實現(xiàn),相反,他們都在社會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
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什么?早已退休的莫納爾特說:“我并不想否認,沒有上過學的孩子也能長大,但是教育仍然不可或缺,在他們的故事中,孩子的母親代替學校充當了教育者的角色。然而我更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及時為這些孩子踩剎車,今天的他們會怎樣?如果他們從一開始就上學,今天會不會更加成功?”
這三兄弟中對學校生活最適應的尤里卻反駁,他寧愿沒有在學校學習的經(jīng)歷。“學校讓我崩潰。”一次他對父親說。對他而言,學校是“一個無法逃出的地方”。西蒙對此表示贊同:“職場中也有很多強制規(guī)定,但是一旦我覺得不合適,我永遠有轉行的可能。”
他們的母親克里斯蒂安又回到了施瓦本山區(qū),和她的新伴侶生育了兩個兒子。他們?nèi)缃?歲和11歲了,兩人都從沒去上過學。只有母親在臨近的學校教授手工課時,有時會帶著年長的兒子同行,而他會給學生們示范如何做絨毛球。
[譯自德國《南德意志報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