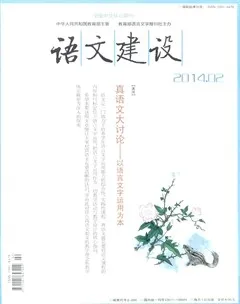確立語用目標(biāo),構(gòu)建語文教育新體系
我國語文教育的種種問題,表面看是教學(xué)問題,其實質(zhì)是課程問題,尤其是其背后所依據(jù)的語言觀和語言學(xué)基礎(chǔ)。有什么樣的語言觀,就有什么樣的語文教育。我國的語文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須從更新語言觀,構(gòu)建語用教育理論體系開始。
一、百年語文的語用目標(biāo)觀
語文是“學(xué)語言”的學(xué)科。百年語文教育的發(fā)展史其實是一個“語言專門化”的歷史。[1]“語言專門化”是語文獨立設(shè)科的唯一理據(jù)。由于語文教育受傳統(tǒng)義理教育影響太深,要認(rèn)識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事實上,我國語文教育的語言目標(biāo)經(jīng)常發(fā)生偏移。
1904年的《奏定學(xué)堂章程》仍具有濃重的經(jīng)義教育色彩。直到1916年頒布《國民學(xué)校令施行細(xì)則》規(guī)定“國文要旨在使兒童學(xué)習(xí)普通語言文字,養(yǎng)成發(fā)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fā)其智德”,第一次明確“語言教育”的主目標(biāo),并為后世語文課程目標(biāo)確立圭臬。1923年吳研因起草的新學(xué)制《小學(xué)國語課程綱要》目的是“練習(xí)運用通常的語言文字,引起讀書趣味,養(yǎng)成發(fā)表能力,并涵養(yǎng)性情,啟發(fā)想象力及思想力”,再次確立“運用語言”的課程宗旨。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曾發(fā)生“技術(shù)訓(xùn)練與精神訓(xùn)練”之爭,葉圣陶等力排眾議堅持“國文教學(xué)自有它獨當(dāng)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的訓(xùn)練。……這種技術(shù)的訓(xùn)練,他科教學(xué)是不負(fù)責(zé)任的,全在國文教學(xué)的肩膀上”[2]。建國初,語文教育一度強調(diào)政治性。1958-1961年的語文“文道關(guān)系”大討論后,語文教育正式確立了其“工具性質(zhì)”。1963年語文教學(xué)大綱中提出“語文教學(xué)的目的,是教學(xué)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這一觀點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后,“培養(yǎng)學(xué)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作為語文教育的邏輯起點與學(xué)科基點,基本成為語文界的共識。
從20世紀(jì)初的“經(jīng)義與語文之爭”,到三四十年代的“技術(shù)訓(xùn)練與精神訓(xùn)練”,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文道之爭”,又到20世紀(jì)末以來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語文教育目標(biāo)總搖擺不定,常常陷入二元矛盾糾纏。2001年《義務(wù)教育語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實驗稿)》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tǒng)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這一說法看似公允,其實是對語文科的“語言教育”本質(zhì)的無視。這直接導(dǎo)致了課改十多年來,語文課程目標(biāo)泛化,教學(xué)內(nèi)容虛化,知識技能淡化,“泛人文、非語文、去語文”盛行。語文放棄了語文教育的本質(zhì),語文課沒有了“語文味”,飽受批評。直到《義務(wù)教育語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2011年版)》明確指出“語文課程是一門學(xué)習(xí)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語文課程致力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等理念,才將“語言文字運用”提高到一個全新高度,語文才算重新回到語言教育軌道上來。
語文課程目標(biāo)的核心是“學(xué)習(xí)語言文字運用”,其他目標(biāo)像“思想、人文、道德、政治、情意、審美、文化等都是語言教育這個主干上的衍生物,是通過語言學(xué)習(xí)和運用語言實現(xiàn)的”,“語文課程區(qū)別于其他所有課程的特質(zhì)在于它以培養(yǎng)學(xué)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為根本宗旨”。[3]語文教育只有立足于“語言文字運用”,才能找回自己,回歸本質(zhì)。
二、語言教育:從語言能力到語用能力
任何時代、任何一種形態(tài)的語文教學(xué),不管是否自覺,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語言學(xué)觀念和理論基礎(chǔ)上。[4]語文要進(jìn)行語言教育就面臨語言觀、語言知識理論來源的問題。傳統(tǒng)語文教育基于索緒爾的“結(jié)構(gòu)語言學(xué)”設(shè)計語言教學(xué),已不能滿足當(dāng)代社會發(fā)展對語言能力的要求。當(dāng)今世界語文教育的語言學(xué)基礎(chǔ)正從傳統(tǒng)語言學(xué)向當(dāng)代語用學(xué)轉(zhuǎn)變。當(dāng)然,這種轉(zhuǎn)變有著時代發(fā)展的要求,也與當(dāng)今語用學(xué)的飛速發(fā)展直接相關(guān)。
1.語用學(xué)及語用能力的提出
語用學(xué)是專門研究具體語境中理解與運用語言的學(xué)科。20世紀(jì)30年代C.W.莫里斯提出語言有“語符、語義、語用”三維。60年代喬姆斯基提出語言能力和語言運用兩個概念。認(rèn)為前者指內(nèi)化了的語言規(guī)則體系,后者指人對語言的使用。后來,D.H.海姆斯提出交際能力的概念,認(rèn)為一個人的語言能力不僅指能說出合乎語法的句子,還包括能否在一定的語言環(huán)境中恰當(dāng)使用語言的能力,即在不同的場合、地點對不同的人進(jìn)行成功的交際的能力。這些觀點對當(dāng)代世界語言教育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語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流。交流能力是語用能力的核心。傳統(tǒng)語文教育是個人的、內(nèi)向型的、封閉的,而現(xiàn)代社會開放交往合作的社會環(huán)境,更需要人的表達(dá)交流與溝通合作能力。歐美語文課程鮮明的“交際取向”與我國的“應(yīng)試取向”形成鮮明對比。社會對人的語用能力與交際能力的要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
2.從語言能力到語用能力的轉(zhuǎn)變
從語言教學(xué)角度看,語文教學(xué)包括語言形式教學(xué)、語言意義教學(xué)、語言功能教學(xué)三個層面。語文教育的重心正經(jīng)歷從語符、語義教學(xué)即語言能力教學(xué),向語用能力教學(xué)的轉(zhuǎn)變。
語言能力與語用能力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從其語言學(xué)基礎(chǔ)看,一個基于傳統(tǒng)語言學(xué),一個基于語用學(xué)和功能語言學(xué);從教學(xué)內(nèi)容看,一個偏于語符、語義教學(xué),一個注重語境、語用教學(xué);從語言哲學(xué)上看,一個屬于客體語言觀,一個屬于交往語言觀。傳統(tǒng)語文教育基于靜態(tài)語言學(xué),以掌握一定數(shù)量通用的語言知識、形成簡單初級的語言技能為主要任務(wù)。它有一個致命缺陷:忽視語言的應(yīng)用和交際本質(zhì),導(dǎo)致學(xué)生交往能力差、語用能力不強。當(dāng)今社會對人的語言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復(fù)雜情境中的語言實際運用能力要求越來越高。過去靠簡單機械的語言能力完成的任務(wù)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當(dāng)代社會、工作、學(xué)習(xí)的實際需要了。今天語言能力的核心是交流,交流要涉及對象、目的、場合、功能等,它們屬于語用能力范疇。
歐美國家主要立足語用能力教語文,對我國是一個啟示。這絕不是一個東西方語言差異的問題,因為全球化時代人類的語言應(yīng)用環(huán)境幾乎是相同的。這是一個教育目標(biāo)新舊取向更迭的問題。
三、構(gòu)建基于語用的語文課程教學(xué)體系
1.語用能力:語文教育目標(biāo)的核心
當(dāng)代語文教育的根本目標(biāo)是什么?應(yīng)該是培養(yǎng)語用能力。雖然語文也有思想政治和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教育的目標(biāo),但那是輔助目標(biāo),不是核心目標(biāo)。雖然語文需要語言知識、語法規(guī)則和篇章知識的學(xué)習(xí),但是學(xué)這些知識的目的是運用。葉圣陶先生說:“語言文字的學(xué)習(xí),出發(fā)點在‘知’,而終極點在‘行’,能夠達(dá)到‘行’的地步,才算具有這種生活的能力。”[5]學(xué)習(xí)語言文字運用是語文課程的本質(zhì)。舉凡日常生活中的言語交流,工作學(xué)習(xí)中的語言運用,以及社會運行、文學(xué)藝術(shù)、文明創(chuàng)造等復(fù)雜高級的人類活動,無一不是語言文字運用的過程和結(jié)果,都屬于語用層面。準(zhǔn)確、得體、高效的語言交際能力是當(dāng)代公民所必需的生存技能,也是語文教育的最終目標(biāo)。義務(wù)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應(yīng)把培養(yǎng)學(xué)生運用祖國語言文字進(jìn)行交流溝通作為語文教育目標(biāo)的核心。
2.語用知識:語文課程主體內(nèi)容
語用學(xué)是語文課程的原理性學(xué)科。雖然語用學(xué)是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由西方學(xué)者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起來的語言學(xué)的一門獨立的新學(xué)科,但語用的概念至今還沒有正式進(jìn)入我國語文課程與教學(xué)領(lǐng)域。由于沒有語用學(xué)理論指導(dǎo),目前我國的語文課程知識體系還缺乏語境、語篇、語用等一系列語言運用知識,由于缺乏語用知識導(dǎo)致所培養(yǎng)的語文能力也是一種虛假的語文能力。
語文課程語用知識的來源首先在于語用學(xué)及其相關(guān)學(xué)科,比如“語用學(xué)”“功能語言學(xué)”“篇章語言學(xué)”“寫作學(xué)”“閱讀學(xué)”“文藝學(xué)”“交際學(xué)”“傳播學(xué)”等。語文學(xué)科亟待引入諸如運用主體、語用規(guī)則、語用形式、語言目的、語用類型、語用效果、語篇交際、語用審美、語用文化等知識,使其成為語文教育核心知識內(nèi)容。課程標(biāo)準(zhǔn)制定、語文教材編寫、語文課堂教學(xué)、豐富多彩的語文實踐活動應(yīng)該以這些語用知識為核心內(nèi)容,從而取代過去的語言、語法、章法知識成為語文課程知識的主體。這種知識更新所帶來的課程內(nèi)容更新以及整個語文教育教學(xué)評價體系的更新,將支撐起未來新語文教育的軀體與靈魂。
3.語用實踐:語文能力培養(yǎng)的途徑
語言能力的形成遵循“言語—語言—語用”的規(guī)律。任何一個人學(xué)習(xí)語言都是從具體言語活動和語言材料開始,在接觸言語作品和言語活動中,慢慢感受語言的規(guī)律,積累語言運用的知識經(jīng)驗,然后將它們遷移到生活世界的語言運用活動中去,形成自己的語用能力和語用素養(yǎng)。傳統(tǒng)的語文教學(xué)培養(yǎng)的是一種僵死、低級、虛假的語言能力,真正的語言能力是語用能力,它是在語用實踐活動中形成的。過去語文能力教學(xué)的假設(shè)是“語言知識—語言能力”,忽視了知能轉(zhuǎn)化的關(guān)鍵,即語言的運用環(huán)節(jié)。就像游泳需要在水中練會一樣,真正語言能力的形成離不開語用實踐。通過語言知識灌輸?shù)姆绞浇陶Z文,效率低、效果差,違背語言學(xué)習(xí)的客觀規(guī)律與科學(xué)原理。語文教育要構(gòu)建“言語—語言—語用”的開放而有活力的永不停息的語用實踐循環(huán)圈。
只有立足語用理論,以語用能力為核心,以語用知識為內(nèi)容,以語用實踐為途徑,以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用能力、提高學(xué)生的語用審美和文化素養(yǎng)為根本目標(biāo),本本分分地教語文,實實在在地學(xué)語文,扎扎實實地用語文,“假語文”“泛人文”以及脫離生活實用的“偽語文”問題才有望解決,我國的語文教育才有望走上科學(xué)健康發(fā)展的道路。
總之,基于語用的語文教育是當(dāng)代中國語文課程改革的正確方向。構(gòu)建基于語用的語文課程教學(xué)體系乃當(dāng)務(wù)之急。目前基于語用的語文教學(xué)理論研究已經(jīng)開始[6],基于語用的語文課程教學(xué)體系建設(shè)還任重而道遠(yuǎn),需要更多有識之士通力合作,建造一座真語文的通天塔,當(dāng)從今日始!
參考文獻(xiàn)
[1]李海林.語言專門化——語文教育的一個岔路口[J].語文教學(xué)通訊,2004(11).
[2][5]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C].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1980:57,3.
[3]王尚文.語文教學(xué)要走在“語文”的路上[J].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參考,2004(10).
[4]李海林.言語教學(xué)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
[6]目前已有王建華的《語用學(xué)與語文教學(xué)》,王元華的《語用學(xué)視野下的語文教學(xué)》,孔凡成的《語境教學(xué)研究》等研究成果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