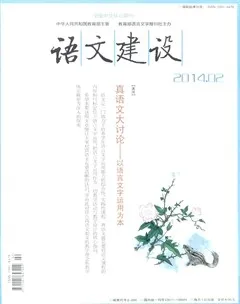對話,讓思維更有深度
小說教學中,我們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要求分析某一人物時,學生給出的答案往往是籠統的抽象概念,許多學生憑直覺能說上一兩點來,但具體的又說不出所以然來,造成結論與文本間的“空檔”;長期架空文本的論述,模式化的結論評價,易使學生產生思維倦怠,分析能力、思維能力難以有效提升。
筆者嘗試在小說閱讀中進行開放式教學,即無預設、無指向,學生在素讀的基礎上獨立思考、分析、鑒賞,之后小組交流,全班討論。所有的解讀全部在課堂即興生成。這種開放式的課堂如果完全交給學生自由討論,極易形成兩種局面:其一,目標散亂,自說自話;其二,分析粗淺,難以深入。因此,課堂教學中教師要適時適當啟發、引導、點撥。引導學生關注作品的言語,沉浸到文字的世界,由對語言的直覺提升到對語言的理解,進一步明晰思路,讓文字變得立體,從而使閱讀走向深入。
下面以《孔乙己》一課的教學為例具體來談。
一、比較分析,思維碰撞
在對話教學中,適時運用比較分析,往往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學生分析一:眾人都哄笑起來,從“笑”中可以看出人們的冷漠。
師:你憑什么認為眾人的“笑”就是冷漠的?
生1:他們笑得不一樣。是“故意高聲的叫道”,說明是有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從孔乙己身上找點樂子,這并不是善意的。
師:注意到了說話時的表現,語氣神情等,還可以從哪里看出他們的笑不是善意的?
生2:他們并非因分享別人快樂的事而笑。他們說的是孔乙己偷東西和考不中秀才,這兩件事對孔乙己來說都是不能說的痛。
師:為什么這么說?
生3:因為他是讀書人,讀書人講斯文,不能偷東西,這關系到他的面子問題,沒考中秀才更是對他能力的否定。你看,人家一說,孔乙己就“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從“不屑置辯的神氣”到“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這兩件事一說出來,可謂擊中了要害,他們從孔乙己的神情變化中獲得了歡樂,他們的歡樂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二、咬文嚼字,深究細品
咬“文”可從嚼“字”始,解讀文本時要讓學生學會關注文字本身,深究細品,點石成金。
學生分析二:孔乙己偷了人家的書,被人譏笑了還不承認,還一定要說“竊書不能算偷”,從中可以看出他死要面子。
師:你覺得“竊”與“偷”本質上有區別嗎?
生1:沒有。
師:那他這么強調是“竊”不是“偷”真的可以要回面子嗎?
生2:不能。在短衣幫的人看來,“竊”就是“偷”。在他們眼里,孔乙己早就沒什么面子了。
師:那么在孔乙己眼里“竊”與“偷”有區別嗎?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個詞到底有什么區別。
生3:一個比較書面化,一個比較口語化。
師:書面化顯得“我”是讀書人,有水平。
生4:孔乙己強調是“竊”不是“偷”,因為他也承認“偷”是不好的行為,是為人所不恥的惡劣品行,但說“竊”的話好像要好一點。這說明他自欺欺人。
師:自欺還是欺人?
生5:應該是自欺。他反復強調這一點,是要讓自己相信“竊”真的不是“偷”,“我”雖然做了這樣的事,但和“你們”說的并不是一回事,“我”品行上并不是惡劣的,這樣就能保全自己的面子了。
師:在強調了形式上的差別后,似乎實質也變得不一樣了。孔乙己的自欺為他換得了心理平衡,卻也為別人增添了更多的笑柄。
三、前后關聯,追問不舍
追問,是對話教學中常用的手法。那么,在什么點追問才適宜?在什么時候追問才最有效?根據實踐,筆者以為,應當在學生自覺“理所當然”處,在學生“自信滿滿”時。“理所當然”包含的是其潛意識下的思維慣性,“自信滿滿”是學生深思熟慮的表現,此時追問最能呈現出邏輯推理的過程與脈絡。
學生分析三:“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站著喝酒”說明他地位低,“穿長衫”是為了顯示他自己的身份。
師:什么身份?
生1:讀書人的身份。
師:顯示這種身份對于他人、對于實際生活來說有意義嗎?(生搖頭)那他為什么還這么放不下這種身份?
生2:他科舉考試失敗,心有不甘,說明他還是不能完全面對現實。他如果放下這種身份,不穿長衫,那就等同于短衣幫了,他作為讀書人的那種優越感就沒有了。
師:這種優越感對他來說很重要嗎?
生3:重要。因為在別人那里他得到的只有嘲笑與不屑,他也根本毫無尊嚴可言,這點優越感可以讓他獲得一點心理平衡。
師:人活著總要面對實實在在的世界。在無力抵抗外界的欺壓與迫害時,他通過穿長衫給自己營造了一個精神堡壘——我是讀書人,我比你們有文化。他用他那僅有的一點優越感來抵擋圍攻他的冷嘲熱諷,而且他還用另一種方式來鞏固他的這種優越感——
生:滿口的“之乎者也”。
四、追根溯源,平中見奇
往往司空見慣的東西,其中蘊藏的“天機”是最大的。布封說:“風格即是本人。”言語主體的說話方式和說話習慣,往往比所說的內容能更真實、更真切地展現一個人的心靈世界、個性精神。教師要善于在無疑處置疑,善于挖掘“平常”中的“奇絕”之處。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而將文本解讀帶向深處。
學生提出疑問:孔乙己在給孩子們茴香豆后已經說了“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為什么之后又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師:一開始是跟孩子們說的,對象很明確,之后的那句是跟誰說的?
生1:“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應該是對自己說的。
師:從他對自己說話的方式中你有什么發現嗎?
生2:也是文言的方式。
師:一般一個人面對自己的時候應該是最放松的,會去講究什么形式嗎?
生3:說明他平時自言自語的時候就是這樣,習以為常了,下意識的。
師:如果說他對別人用文言的方式是想顯示自己讀書人的身份與修養,那他在下意識中對自己的這種說話方式又能說明什么?
生4:說明這種方式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常態,這不僅是他的說話方式,更是他的生活方式。
師:對,他始終沉浸在自己營造的世界中,自說自話,自我麻醉。他始終不肯放下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所謂讀書人的身份,以期在這個世界中保有他殘存的那點可憐的價值。
生5:這讓我想到范進,范進是幸運的,但孔乙己卻落魄到了社會最底層,窮困潦倒,受人欺辱,但他又不能面對自己的真實處境,可見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毒害之深。
語文教學的對話,從課堂角度來說,不僅包括教師與學生間的對話,還有學生與課文、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材編寫者、教師與課文、教師與教材編寫者之間的對話。教師,作為提升學生思維水平的中間媒介或助推器,占據著絕對核心的重要地位。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諸多方法也是共通共融、有機統一的。教學過程中,課堂上呈現出濃濃的探究熱情,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思維火花不時碰撞,許多精彩由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