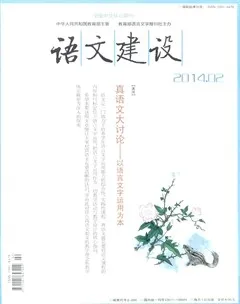語文教學須“祛弊”
20世紀20年代,討論國文教學是一時之風氣,當時一些有影響的雜志如《教育雜志》《新教育》《學生雜志》,甚至《新青年》都刊載有關(guān)國文教學的文章。一些著名的文史專家都參與討論。史學家呂思勉從1905年起開始教小學國文和歷史,1914年到1919年在中華書局、商務(wù)印書館任編輯,編寫過兩套國文教科書,同時也非常關(guān)注國文教學的討論。呂思勉發(fā)表的有關(guān)國文教學的文章有十來篇,最早的是1921年他在沈陽高等師范教書時發(fā)表于《沈陽周刊》的《答程鷺于書》,最重要的是1925年發(fā)表在上海《新教育》雜志上的《國文教學祛弊》,而最長的則是寫于1937年到1938年作者任教于光華大學之時的是未刊稿《論基本國文》,主要內(nèi)容是關(guān)于大學語文的選擇和編排。
呂思勉有深厚學養(yǎng)并有實際教學經(jīng)驗,又編寫過中學和小學的國文教科書,因此,他的意見是非常內(nèi)行的。尤其《答程鷺于書》和《國文教學祛弊》二文,針對當時國文教學中出現(xiàn)的種種不符合教學規(guī)律的現(xiàn)象提出了中肯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是置于今天仍然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本文擬將這兩篇文章略作介紹,并加以簡評。
一、《答程鷺于書》
這篇文章原刊于《沈陽周刊》,后收入《蒿廬論學叢稿》,今見于《呂思勉遺文集》(呂思勉《呂思勉遺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該文原是一封回答學生問學的書信。有兩部分內(nèi)容,前一部分談國文教學,后一部分談經(jīng)學的“今古文”問題。這里談?wù)勱P(guān)于國文教學的那一部分,共涉及如下四個問題。
第一,呂思勉把各年齡段的國文分成三個階段:一是最淺者,就是白話文,也叫語體文,應(yīng)該在小學里教;二是較深者,指普通應(yīng)用的文言,可以在中學里教;三是最深者,是文學的語言,當然這里指的是舊文學。呂思勉認為第三種是專門之事,可以不論。關(guān)于為什么要在小學里學白話文,他說:“文言既非盡人所能通,即斷無人人學之之理。此高等小學以下,所以宜專授白話也。”至于在中學,文言必不容不授,因為將來有一部分人需要深造,另一部分人,雖只需學白話,而通文言對白話也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教學要兼顧這兩部分人。
第二,呂思勉談了如何教學生學習,他說“令其自己讀書”是為“第一義”。他指出,現(xiàn)在學生國文不能通的原因是“今日學校中教授國文,只執(zhí)成文數(shù)十百篇,死講其文法及修詞之法,而不使學生自己讀書”。因此,他同意胡適在《中學國文教授》里提出的讓學生自己讀書并讀小說的主張。但是,他對胡適開出的書目不贊成,認為分量太重程度太高,不是中學生能夠勝任的。而對胡適認為課外讀書、課內(nèi)講解也不太贊同,他說:“鄙意國文一科,講貫簡直有妨教學效果,須將其減至最小限度,教室之時間,盡從事于講貫,尚覺其太多。”按他的設(shè)想:學生所讀之書不必限定何種,聽其自己所好即可,因為只有自己喜歡讀的書然后能多讀,多讀然后能有悟入處;在教室里亦以學生自己讀書為主,有問題了再由學生質(zhì)問,教師回答,再次之是教師就學生習作加以批評,教師的提示須減到最少限。
第三,呂思勉主張學生要學會自己思考:“凡疑義,貴乎自思;一疑即問,亦屬不宜。凡人之學問必一級一級,逐步而進;欲躐一級不得。”因此,教師提問講解都要顧及班級里不同層次學生的需要。總之,呂思勉強調(diào)學生自學:“讀書百遍而自熟,猶之練體操,為某式之運動,至若干處而筋力自強,此筋肉之強斷非由體操教員講明運動之理而即得,學國文亦猶是也,真正之了解斷非有教員講解而得。”對于有人認為應(yīng)該給學生學習“精良的工具”這一種說法,他認為:求學問的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做教師的,只能在他們自造成工具時,略加輔助罷了。
第四,呂思勉主張學生多讀多看多寫,“切勿妄講文法,勉強用心推求”,這個文法是指作文之法。他認為舊時代講文法之書往往只對應(yīng)舉之文有用,對文學沒有什么用。現(xiàn)今一些講文法和修辭的書,學生文理通了以后閱之自然能懂,就像語法一樣,是學會講話以后之事,絕不能靠它來學語言。他還反對教師越俎代庖改文章,“主批評而不主改削”,因為幫助學生改文章會限制他們的思路。只有讓學生自己修改才可能有所領(lǐng)悟,有所進步。
二、《國文教學祛弊》
1924年,上海的《教育雜志》曾組織中學國文課程建設(shè)的討論,當時許多名家參與討論,沈仲九、孟憲承、何仲英、朱經(jīng)農(nóng)、朱自清等都有文章在《教育雜志》上發(fā)表。呂思勉當時在滬江大學,他的文章《國文教學怯弊》發(fā)表在《新教育》第十卷第三期上,時間是1925年。所謂“祛弊”,就是要去除國文教學中存在的許多弊端。國文教學從1904年開始到那時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新舊文化和新舊教學方法的對立經(jīng)常在國文教學中表現(xiàn)出來,主舊的和主新的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一般的中小學教師有時難免不知所從,這就影響了國文教學的效率。中小學國文教學中確實也存在一些弊端。呂思勉針對這些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概而言之,他認為當時國文教學中存在著六種弊端:偏主文言白話之弊;講俗陋文法之弊;并舊文學與國文為一談之弊;誤國文為國故之弊;偏講理論之弊;不重自習之弊。就是這六種弊端影響了國文教師的教學。
關(guān)于第一種弊端,呂思勉認為:文言白話的界限不是非常明確的,自古以來就有古文、白話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普通文”,即日常的應(yīng)用文如公牘書札,普通文是將文言白話合起來用的。他的觀點是文言白話各有優(yōu)點和缺點,兩者不應(yīng)該偏廢,不同的場合、不同文化水準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呂思勉指出偏主文言一派的偏頗在于:要求人人都學文言,認為文言并不難通,是置事實于不顧,當年科舉時代,一些學童讀書十年下筆不能成一字者也不鮮見。相反,偏主白話一派的偏頗在于:認為文言絕不足學,這也是不對的。因為白話中有許多詞類必須取之于文言,多讀文言的人,他們所作的白話文,語言可以精練,文章可以謹嚴,所以他認為學不學文言不能一概而論。
第二個弊端是“講俗陋文法”,這里的“文法”是指作文之法,而非文言語法。20世紀20年代,雖然已經(jīng)實行語文新課程多年了,但是不少學校指導學生作文仍然沿用舊時代寫策論和制藝(八股文)的一套方法,這一點葉圣陶、王伯祥等都有過批評。呂思勉認為作文應(yīng)該有了感想才寫,有題目了再寫就已經(jīng)不自然了。現(xiàn)在社會已經(jīng)不是科舉時代了,教師也不是科舉中人,但是那一套盛行幾百年的東西仍然在影響著教師。社會上流行的“評本”“選本”還在學校里被奉為寫作的范本。他說:“學文者一入此途,百無是處。欲講授國文,須先將此等謬說,一切摧陷而廓清之——舊時俗陋之選本,及近之俗陋選本,如《學生國文成績》等,宜一概屏絕。”所謂《國文成績》是指當時一些作文選本,往往以“國文成績”為名,這些選本大多數(shù)選的是文言文寫的作文,作為范本在中小學流行,教師以此類文章作范本教學生作文方法。呂思勉認為這也是一個弊端。
關(guān)于第三和第四種弊端,其實可以并為一種來講。呂思勉認為,舊文學雖然與國文有關(guān)系,但絕不能并為一談。普通文言是一種較高等之國語,普通文字人人能通,但是舊文學乃美術(shù)之文學,不是人人能通的,也不必人人都學。“高等學問之領(lǐng)悟,自非天才,必待相當之年齡。”如果不顧實際天天給學生講什么“雅馴”“義法”,就一定使學生感到隔膜。國文就是基礎(chǔ)課,不是舊文學鑒賞課。至于把國故和國文混為一談,也是當時一種常見現(xiàn)象。當時整理國故是很時髦的一件事,有人就認為讓學生也去接觸國故就能學好國文。但是,國故本身太籠統(tǒng),究竟是指什么很難確指,此外它與國文又有什么關(guān)系,這些都是超越學生實際水平的。呂思勉此論不是無的放矢,因為當時有些學校把“經(jīng)、子、史、漢”列為課程。造成的結(jié)果是:“經(jīng)書之義,初未通曉,已評論漢宋之短長,爭訟今古文之真?zhèn)我印VT子讀未終篇,已滿口周秦學術(shù)流別;朝代且不省記,已縱談史書體裁得失矣。教者信口開河,學徒之謹愿者,初不知為何事;其浮動者則摭拾牙慧,如塗塗附。”呂思勉認為這種做法只會把“秀才變成學究”。
第五種弊端是“偏講理論”。這是指當時一些學校的文學概論、文學史一類課程。呂思勉批評有些教師不顧學生實際喜歡講一些評論作家作品的理論,對李杜之詩、韓柳之文,學生首先要自己去讀,要有感性認識,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妙處。而當時一些教師的做法是:“于事實概乎未有聞知,而顧以評論此事實之語,強聒不舍,此則千言萬語,悉成‘戲論’而已矣。”對此,呂思勉的觀點是:所有那些文學概論、文學史一類科目應(yīng)該從中等學校的語文課程中刪除。就是到了大學也應(yīng)該讓學生讀書稍多以后才能開設(shè)。
最后一種弊端是“不重自習”。這里的觀點和《答程于鷺書》里的完全一樣。呂思勉說:“凡事必先立基礎(chǔ),基礎(chǔ)穩(wěn)實,其余一切,皆不煩言而解。”因此,學生要從熟讀成誦、多看(擴大閱讀量)兩方面入手。他感嘆當時學生讀書實在太少。這一點和胡適完全一致。胡適在《中學國文教授》一文里曾經(jīng)批評當時“薄薄的教科書”是“為低能兒準備的”。呂思勉說:“茍能多讀,即不語之,自亦能知。迎機語之,尤極容易。若其從未讀過抑或所讀甚少,則雖耳提面命,亦屬茫然。故今日諄諄之講授,及無謂之討論,十分之九,皆可省去也。”然后他還用自己讀書的經(jīng)歷為例說明自學的重要。
本文在批評了六弊以后,還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如“自行讀書之法,吾希望之兩種書”。呂思勉說:“大抵人之讀書須經(jīng)過雜讀及亂讀之一時期,而后趨向乃定,此其一關(guān)系年齡之長幼,一關(guān)系學問之淺深。…….所貴迎機指導,略與輔助者,則正在其雜讀及亂讀之時代耳。”他認為這個時期除了必不可讀之書外,“宜一切勿加禁斷也”。為了做好指導,他認為亟須編寫兩種書,一是有簡明注釋和詳晰符號的古書;二是一種工具書,“先略說六書條例,音韻轉(zhuǎn)變,以為緒論”,要求不必太高,“其本論則舉數(shù)千常用之字,先說明其本義,又說明其所以引伸假借之故焉”。這兩種書,差不多相當于朱自清先生所提倡專家精心編寫的“選本”,以及王力先生后來在《古代漢語》“常用詞”基礎(chǔ)上編撰成的《古代漢語詞典》。什么叫英雄所見略同?真正的專家才能說出同樣明白清楚而且不偏激的話。
三、呂思勉國文教學思想給我們的啟示
呂思勉的這些論述是大約八十多年前寫的,對于我們今天的語文教學還有什么用呢?呂叔湘先生1980年在為《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所作的“序”里這樣說:“按說這本集子里邊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寫的,為什么現(xiàn)在還沒有過時呢?這是因為現(xiàn)在很多問題表面上是新問題,骨子里還是老問題,所以這些文章絕大部分仍然富有現(xiàn)實意義。”(呂叔湘《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對呂思勉先生的文章也可作如是觀。我們重提這些論述絕不是簡單的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從前人那里獲得啟迪,想一想我們當今語文教學有沒有當年呂思勉所提的弊端?依筆者愚見,至少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呂思勉關(guān)于小學生學白話,中學生才學文言,要遵循孩子發(fā)展規(guī)律的看法,非常有道理。雖然他談的是文言和白話,但是他多次強調(diào)反對凌節(jié)和躐等,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多少年來,小學生不扎扎實實學習語文基本功,還沒有積累多少詞匯就要在課堂上分析課文的現(xiàn)象,已成為一大景觀。只要去看一看小學生的考試試題,我們就會明白一切。
其次,呂思勉反對“妄講俗陋文法”,提倡學生自己讀書;而且提出,學生在發(fā)展自己閱讀能力時大抵都經(jīng)歷過一個“雜讀”“亂讀”階段,教師應(yīng)該“迎機指導”,而不要急于禁斷。這和葉圣陶提倡的“相機誘導”“誘導與啟發(fā),講義并示范”是一個意思。這些話有沒有過時?相信我們是不難判斷的。現(xiàn)在“妄講文法”的教師不多,但是在課堂里大講解題技巧、傳授考試秘訣的不在少數(shù),在課堂上深文周納、條分縷析解讀課文,深挖課文“核心價值”,把一篇本來容易理解的文章分析得學生不知云里霧里的也很常見。結(jié)果當然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這兩種表現(xiàn)雖不同,但是“不重學生自習之弊”的結(jié)果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后者還往往打著發(fā)展學生思維、提高學習效率的“科學”旗號,糊弄了不少一線教師。
最后,過去有“整理國故”和將舊文學、國文混為一談之弊,而我們現(xiàn)在也常常有一些陳義過高不合實際的要求,例如提倡中學生讀經(jīng),動不動要開展研究性學習。學生對中國古代詩詞學習吟誦背誦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讓初中生、高中生在中考高考中賞析古詩,顯然是超出學生的能力,屬于凌節(jié)和躐等,結(jié)果導致學生討厭古詩詞。因此,我的結(jié)論是現(xiàn)在的語文教學也要祛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