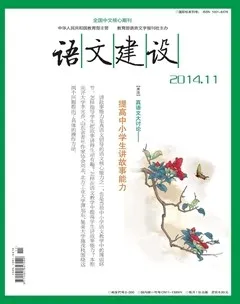貶謫人生風(fēng)景異
從游記乃登山臨水而發(fā)觀感角度而言,蘇軾的《前赤壁賦》與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記》(以下稱“蘇柳二文”)都屬山水游記。將兩文放在一起比較解讀,可以看出不同的山水風(fēng)景和不同的抒情方式所內(nèi)隱的不同的人生參悟。
一、山水文章風(fēng)景異
山水游記的敘寫主體一般應(yīng)是山川風(fēng)景,但恰在這一點(diǎn)上,蘇柳二文卻顯差異。
我們先看蘇軾《前赤壁賦》中的風(fēng)景。通篇觀之,讀者貌似會(huì)覺得自己處于一種月光水色的籠罩之中,聆聽一位哲人闡述人生道理。文中人(蘇子與客),文中物(舟、酒、簫),文中景(浩渺長(zhǎng)江、皎潔明月),中國古代文人能夠抒懷吟誦的一切道具(風(fēng)景)都呈現(xiàn)了出來,為的是讓后世讀者在觀賞風(fēng)景時(shí)能感受到作者的那份曠達(dá)與超然。我們?nèi)魧⑽闹酗L(fēng)景剝離出來,不禁發(fā)現(xiàn)整篇文賦寫景處,僅集中于文章開頭:“清風(fēng)徐來,水波不興”,“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除此之外,幾乎都是作者在明理抒懷,因而,我們能感覺到蘇軾賦中寫景,并不是為了展示赤壁自然山水,或者說并非是為了寫景而寫景,而是將山川風(fēng)景作為觸發(fā)情志的媒介,或議論說理的工具。譬如明月大江,不過是“吹簫客”與蘇子觸發(fā)悲喜之情的工具;文章巧妙借助于江水的奔流無盡、明月的周期盈虛,也是為闡釋天地變亦不變的道理。
再看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記》。游記開篇寫自己貶居永州后漫游山水時(shí),發(fā)現(xiàn)并宴游西山。在寫西山風(fēng)景時(shí),柳宗元以敏銳的觀察力,驅(qū)遣生花妙筆,連用形容和譬喻,從不同角度描繪眼中的西山風(fēng)景。先寫西山縱勢(shì):“岈然”寫山谷的空闊,“洼然”寫溪谷的低下;“若垤若穴”寫其狀如蟻穴,形似窟窿。再寫西山橫勢(shì):“尺寸千里”側(cè)寫山脈連綿橫亙,“攢蹙累積”直言高山巒聚密集,“莫得遁隱”說其精微幽深。而后回首騁目,只見山巔上“縈青繚白,外與天際”,進(jìn)一步寫高峻。最后以“四望如一”收結(jié)有力。
品讀這篇游記,竊以為柳宗元對(duì)西山風(fēng)景的描寫,可稱得上是“形容盡致”,在他的筆下,西山的高峻形勝,可視可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作“漱滌萬物,牢籠百態(tài)”。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就曾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tài)’,固宜。”此論甚確。當(dāng)然,作者也有自我感受的抒發(fā),但就整篇游記而言并不占主要地位,文章只是在描寫完西山風(fēng)景之后,才道出“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
為類”的感嘆。
蘇柳二文,兩相比較,如果說柳宗元要使他的“西山宴游記”成為西山風(fēng)景的鏡子,那蘇軾則是使他的“赤壁賦”成為他自己的鏡子。蘇軾《前赤壁賦》將景物視為一種抒懷媒介或工具,文中對(duì)風(fēng)景的描寫幾乎淡化,相反作者卻大大強(qiáng)化自我感受的抒發(fā),給讀者的感覺是,整篇文賦呈現(xiàn)出略景存情,甚或舍景存情的特點(diǎn)。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卻恰恰相反。在其筆下,西山既有正面落墨,也有側(cè)面烘托;既有仰觀遠(yuǎn)景,也有俯察近物;既有全景鳥瞰,也有特寫鏡頭。這種通過洞察刻畫而出的西山,已然不是一種冷漠的存在,而是柳宗元心中的風(fēng)景。
二、比賦抒懷方式異
從景物描寫的特色而言,柳蘇二人都注重景物描寫的客觀真實(shí)性,但二者不同的是,柳宗元的“西山”用比興去呈現(xiàn),蘇軾的“赤壁”則用賦去表現(xiàn)。
在西山宴游前,柳宗元先是自述:“居是州,恒惴栗。”為何惴栗?而此間所謂游山玩水:“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yuǎn)不到。”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以僇人身份謫居永州之境況,同時(shí)也能看出作者力求以游覽和醉夢(mèng)來解脫苦悶之心情。然而當(dāng)其寫到登西山,“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則表現(xiàn)出作者披荊斬棘,與命運(yùn)抗?fàn)幍纳蓜?dòng)。上得西山,頓然感覺“則凡數(shù)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為類”,由此顯示自己不與奸佞小人為伍、超然物外的心態(tài),同時(shí)也是對(duì)自己特立獨(dú)行人格的欣慰,最后作者“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從苦悶中有所解脫。
我們說,柳宗元游的是西山,悟出的是自己。在他的筆下,西山儼然成了“僇人”的象征物,西山的特點(diǎn)就是人的特點(diǎn),山被遺忘即人被遺忘,山與人成為一種對(duì)應(yīng)的互賞共感的同類。我們能感覺到,柳宗元探訪西山之旅正是其精神痛苦解脫之旅,品味山之被忽視也就是在咀嚼自己被貶謫;或者說,西山宴游之過程即是柳宗元游心之過程,也是其精神超脫之過程。
蘇軾的抒懷方式與柳氏的比興手法不同。也許是“烏臺(tái)詩案”的后怕所及,《前赤壁賦》通篇不著時(shí)政一字,但抒情達(dá)意卻盡得風(fēng)流。文章開始蘇軾以閑淡之筆狀寫閑適之情,借自然之“江水、明月、清風(fēng)”等風(fēng)景,繼承并發(fā)展了“主客對(duì)話,抑客伸主”的賦的傳統(tǒng)手法。“客”托古說今,睹物思人;“主”借江月說理,而主客對(duì)話則代表了作者思想中兩個(gè)不同側(cè)面的矛盾斗爭(zhēng);把政治失意的苦悶通過“客”來反映,把樂觀曠達(dá)的情懷通過“主”來表現(xiàn),最終“客”被“主”說服,認(rèn)識(shí)歸為統(tǒng)一,體現(xiàn)了蘇軾精神由苦悶到解脫的過程。
在《前赤壁賦》中,“江水、明月、清風(fēng)”等風(fēng)景并不是精細(xì)刻畫的對(duì)象,而是蘇軾用來表現(xiàn)主體意識(shí)、自我感受的載體,對(duì)于蘇軾來說,看風(fēng)景的過程既是審美的過程、超脫的過程,更是生活的過程。他是在常態(tài)的生活中品味山水風(fēng)景之美。在蘇軾筆下,赤壁風(fēng)景是平淡無奇的,清風(fēng)明月,何處沒有?作者的興趣似乎并不在于山水之奇之幽之麗,不在于對(duì)江風(fēng)明月本身的精雕細(xì)琢,也不在于江水明月與人的同生共感,而在于江水明月的直接觸發(fā)性,它能觸動(dòng)作者尋求解脫痛苦的心情,成為渴望平和閑適境界的一種媒介,在蘇軾的眼中,江水明月與人的心境是互適相協(xié)的。
三、蘇柳人生參悟異
就上文所述,人們不禁要問,蘇軾、柳宗元同為寫山水勝景的大家,從其人生經(jīng)歷來看,二人同為貶謫逐臣,而這兩篇游記又都是其貶謫時(shí)所作,卻為何呈現(xiàn)出不同特色?我們說,或許貶謫環(huán)境會(huì)改變?nèi)说男睦恚洳煌娜松鷳B(tài)度、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不同的情感體驗(yàn),使得作家對(duì)眼前風(fēng)景的參悟有所不同。
就柳宗元而言,謫居永州后的他不斷在尋求排解苦難,遺憾的是他并不能融于山水,而是將眼前環(huán)境視為陷阱,在游西山之前,他游遍永州山水,卻是“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mèng)。意有所極,夢(mèng)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這短促緊湊的語句,反映了他謫居乏味的生活以及苦悶憂懼的內(nèi)心。在此之前,柳宗元參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團(tuán),因革新失敗貶謫永州,不久王叔文等人被殺,柳宗元內(nèi)心更加憂懼不安,為了排憂遣愁,于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但這種漫無目的、不知所往的游玩,并不能排解其內(nèi)心的苦悶、心靈的孤寂,直至其偶遇西山,恍然如他鄉(xiāng)遇故知,于是便有了“宴游西山”之旅,便有了“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之感。能否因此斷言,柳宗元已悟得西山而釋然呢?乍讀其文,似乎有心曠神怡、輕松愉悅之感,但仔細(xì)品來,尤其是將篇首敘寫聯(lián)系起來,不難發(fā)現(xiàn)所謂“宴游”的背后,仍是一片憂憤情懷;所謂“與萬化冥合”的深處,愁苦依舊難以釋懷。因?yàn)椋挥性诂F(xiàn)實(shí)中屢遭挫折,情無可訴,志無可表,才無可用,甚至命無可保,才會(huì)被迫寄情山水,求個(gè)暫時(shí)的忘卻,其實(shí)為一種自嘲加自慰,無奈且憂憤。
而幾百年后的蘇軾對(duì)待貶謫的態(tài)度則不一樣。雖然蘇軾在一些詩文中也有言及黃州貶地“僻陋多雨”“窮陋”等,但遠(yuǎn)不及其對(duì)黃州山水的欣賞。蘇軾在《與言上人》書中說:“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后,曳杖放腳,不知遠(yuǎn)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yōu)劣也。”此語雖包含幾分無奈,但絕對(duì)發(fā)于內(nèi)心,我們?cè)谄洹肚俺啾谫x》中,就能真切感受到蘇軾與赤壁風(fēng)景的互適相協(xié)。赤壁無奇觀異景,但無限風(fēng)光盡在心中,身旁的江水、耳畔的清風(fēng)、眼中的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當(dāng)然,蘇軾取之所當(dāng)取,舍之所當(dāng)舍,在取舍之間,他“游”于其中,“樂”于其中,且能“悟”在其中,達(dá)到一種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這是一種基于對(duì)世事人生深刻體認(rèn)后的感悟,更是一種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蘇軾正是用性格中的調(diào)和與曠達(dá)造就了超然物外的永恒不盡的精神,在屢屢貶謫之后,依然如常,因而在他的這篇赤壁游記中,我們才能體會(huì)到他那種曠然天真的心境。無疑,這般心境,這樣的參悟,要比柳宗元西山“宴游”深刻得多。